
请记住本站永久中文域名:风水业协会.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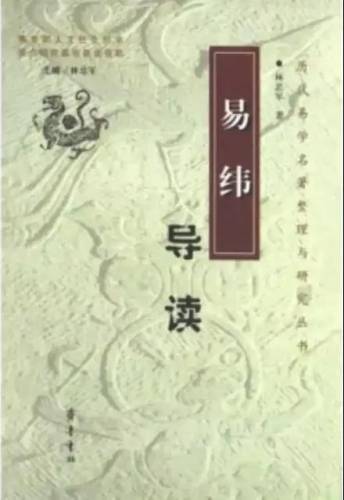
01.《易纬》道家宇宙观
成书于西汉独尊儒术时期、备受当时统治者和儒者重视的《易纬》,是对《易经》的解说和阐发,整体上体现着孔子儒家基本的理念,反映着汉代儒者治《易》的思路和风格。因此,从这个意义说,《易纬》是儒家的作品。然而正是这部出自于儒家之手、整体体现着儒家观念的易学著作融进了道家的思想,从而在儒家占统治地位的西汉表现出儒道合流的倾向。这种倾向集中体现在天道问题上,《易纬》援道入易。
其一,《易纬》在论述宇宙起源时吸收了道家的范畴。为了探讨宇宙演化,《易纬》使用了“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四个哲学范畴。
《易纬·乾凿度》指出:“夫有形生于无形,乾坤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易纬·乾坤凿度》指出:“太易变,教民不倦,太初而后有太始,太始而后有太素。”这里的“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四个范畴皆取自于道家典籍。今人钟肇鹏先生指出:“‘太初’又作‘泰初’,《庄子·天地篇》云:‘泰初有无,无有无名’……《淮南子·诠言篇》说:‘稽古太初,人生于无,形于有。’太素一词也见于《淮南子》。《淮南子·精神篇》说:‘明白太素,无为复朴,体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又曰:‘弃聪明反太素’。《淑真篇》‘偃其聪明而抱其太素’……扬雄《檄灵赋》云‘太始之始,太初之先,冯冯沈沈,奋博无端’(《太平御览》卷一引),在《太玄赋》里又说:‘观大易之损益兮,览老氏之倚伏。’”(钟肇鹏,第147-148页)
不仅如此,《易纬》在讲宇宙本原时还使用“一”、“太极”、“太一”、“无”、“虚无”等观念。《易纬·乾坤凿度》云:
天本于一而立,一为数源。
太易始著,太极成,太极成,乾坤行……乾坤既成,太极大成。
太极有,地极成,人极灵……天有太极,地有太壃。
易起无,从无入有。
《易纬·乾凿度》云:
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气变之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
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
易始于太极,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
故易始于一,分于二,通于三,□于四,盛于五,终于上。
以上所使用的“一”、“太极”、“太一”、“无”、“虚无”等范畴,在道家的典籍中都可以找到。“一”是道家常用的概念。《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三十九章)《庄子·齐物论》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鹖冠子》云:“有一而有气,有气而有意。”《黄老帛书》云:“虚同为一,恒一而止。”《淮南子·诠言训》云:“一也者,万物之本也。”
“太极”源于道家。《庄子·大宗师》云:“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淮南子·览冥训》云:“引类于太极之上。”“太一”也多见于道家典籍。《庄子·列御寇》云:“太一形虚。”《鹖冠子·泰鸿》云:“中央者,太一之位。”
“无”、“虚”或“虚无”是道家专有概念。《老子》四十章云:“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十六章云:“致虚极,守静笃。”《庄子·至乐》云:“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管子·心术》云:“虚无无形谓之道。”
其二,《易纬》在论述宇宙生成时引用或照搬道家的语言。
老子在描述本体的“道”时指出:“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易纬》在描述本体的“易”时指出:“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对比道家和《易纬》的语言,显然,后者出自于前者。
其三,《易纬》继承了道家无生有、气变形变的理论。
以无为本、无生有是道家宇宙观最基本的理论。《老子》明确提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庄子进一步阐述了老子这一观点,认为宇宙从“无”到“有”是气变形变、无形有形的过程。《庄子·至乐》云:“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淮南子》在解释庄子有无之辨的同时,用气探讨了宇宙生成。《淮南子·天文训》指出:“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易纬》在宇宙生成问题上与道家这一理论完全一致。《易纬·乾凿度》云:
易者,以言其德也,通情无门,藏神无内……虚无感动,移物致耀,至诚专密,不烦不挠,淡泊不失,此其易也。
昔者圣人因阴阳定消息立乾坤,以统天地也。夫有形生于无形,乾坤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始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混沦。混沦者,言万物相混成而未相离。
《易纬·乾坤凿度》云:
易起于无,从无入有,有理若形,形及于变而象,象而后数。
太易变教民不倦,太初而后有太始,太始而后有太素,有形始于弗形,有法始于弗法。
从以上引文看,《易纬》将“太易”或“易”视为与道家的“道”或“太一”具有同等的地位。道家的“道”或“太一”具有虚静、寂然、无为的特点,而《易纬》的“太易”或“易”也具有这种特点。在宇宙起源问题上,《易纬》认同了道家的观点,提出“有生于无”、“有形生于无形”的命题。同时,它又似乎看到了“有生于无”、“有形生于无形”过于简单,缺乏必要的论证,进而用道家的概念和语言揭示“有”、“无”之间的逻辑。按照《易纬》的意思,从无到有,经历了太易、太初、太始、太素,这个过程是由“未见气”到“气之始”、“形之始”、“质之始”,“太易”是“未见气”的“无”,“太初”是“气之始”的“有”,“太始”是“形之始”的“有”,“太素”是“质之形”的“有”。因此,从使用的概念、论证方式和阐述内容看,《易纬》在宇宙观问题上与道家是一脉相承的。
另外,在《易纬》中,多次引用黄帝和老子之言。如《易纬·乾坤凿度》四次直引黄帝的话,一次直引老子的话。这些引文虽然未必真的是黄帝和老子的话,但说明了《易纬》在一些问题上接受了汉初黄老思想。
02.《易纬》与黄老道家流行
《易纬》能够吸收道家思想建构自己的宇宙观,与整个易学体系融为一体,这与当时社会政治学术文化的发展分不开。汉初高祖的功臣曹参在任齐相时,“荐盖公言黄老”,“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他做丞相后,实行无为而治。当时老百姓称:“萧何为法,觏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史记·曹相国世家》)陈平曾做过惠帝、吕后、文帝时的丞相,他“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临死后悔自己的行为违背了道家准则。他说:“我多谋,是道家之所禁。”(《史记·陈丞相世家》)汉文帝、景帝和窦太后尊崇黄老之学,《风俗通·正失》引刘向云:“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净无为。”《汉书·外戚传》云:“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由于统治者大力倡导,黄老适应了汉初社会需要而流行,成为当时思想的主流。一些思想家和学者站在新的角度纷纷探讨道家理论,出现了《淮南子》等体现道家思想的著作,对当时政治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自武帝始虽独尊儒术,取代了汉初黄老之学,但是武帝启用许多过去是治黄老之学的官员,他们对于黄老之学有深入的研究和深厚的感情,内心崇尚的仍然是道家,政治上用黄老治理国家,如武帝时名臣汲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净”。(《史记·汲郑列传》)学术上兼顾黄老和儒家者不乏其人,出现许多杂而不纯的儒者。即便是生活在武帝年间的司马父子,“其论学术,则崇黄老薄五经”、“先黄老而后六经”。这是道家在独尊儒术条件下没有完全消亡而且能够发挥作用的外在原因,当然也是《易纬》在儒学极盛时能够接受道家宇宙观的原因。
同时,思想学术发展除了受到社会政治制约外,还有它自身的逻辑规律,即按照自己的需要不断调整、完善、丰富自己的理论。当它受到外来的压抑和冲击时,或以隐蔽的形式自我完善、蓄积力量、等待时机,或通过吸收其它营养改变自己的外在形态,或将自己的学说理论寄托于益于生长的新土壤,拓展生存的空间。汉代的黄老之学就是如此,“黄老学在西汉中期后失去汉王朝宫廷殿堂的支持,并非意味着它作为一种学术文化就从此销声匿迹了。学术文化的生存发展虽然要受当权者的支配,但它却是按其内在的逻辑而演进的。对于黄老学来说,它虽然在西汉中期后,在政治上已无用武之地,但它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文化仍然在活着,并作为两汉儒学正统学术的一种暗流而表现自己”。(丁原明,第303页)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时期有发展的趋势,成书于西汉中叶的道家著作《老子河上公章句》和《老子指归》,说明了道家于汉代失去政治支持后作为暗流完善、丰富、发展自己的理论。而将天道观渗透到儒家思想中,则是道家求生存的另一种方式,这也是道家对包括《易纬》在内的儒家学术产生影响的重要原因。
而从儒家来看,在汉代虽然获得尊贵地位,但重实践、偏人事的儒家理论因缺乏理性思维,面对复杂的汉代社会现实所表现出的局限性日益凸现,也就是说,原来的儒家观念和学说对统治者的政治和社会发生的问题不能完全彻底地作出合理的解释。这就迫使一些儒家学者不得不重新检讨自己的理论,通过吸收其它思想学说来补充完善原有的理论,重塑自身的形象,以求得在社会活动中发挥最大的作用。“所以在汉代,可以看到这样的历史现象:每当社会风俗淫弊、奢华不实、虚伪之风高涨时,儒者们就会自发地倾向于《老子》。每当有神论泛滥弄得社会乌烟瘴气的时候,儒者们也会从黄老思想寻求治疗和抑止的药方。这与其说是一些思想家的个人自觉,毋宁说是由社会倾向所自发形成的趋势。”(金春峰,第645页)这不能不说是《易纬》内涵道家思想的原因。
另外,《易纬》在宇宙观上吸收了道家的思想,还当归结为它对易学传统的继承。大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易学的精神实质,表现了易学固有的摄涵性和开放性。易学正是因为具有了这种摄涵性和开放性,不断吸收外来观念、思想,才实现了自身的扩张发展。出自儒之手、以诠释《周易》为宗旨的《易传》提出了真正反映易学精神的命题,即“生生之谓易”、“化而裁之谓之变”,并通过继承和整合道家的“道”、“太极”、“精气”等观念和“遁世无闷”、“寂然不动”等理论,首先将它所提出的易学精神付诸行动,推动了易学向理性发展。《易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章句笺注之学,但它却是针对《易经》(包括经传)和整个西汉易学而发,而在附会和推阐义理时,受启于《易传》,借用道家观念、思想和理论论证宇宙起源,解说易学象数客观根据,也符合整个易学发展的精神。因此,我们认为,《易纬》在儒学极盛时代接受了道家的宇宙观不是偶然的,这是易学传统。
03. 易道互渗与儒道合流
儒、道两家出身不同,其观念和学说也有很大的差别。班固指出:“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汉书·诸子略》)由于两家观念和理论差别在现实中往往表现出对立撞击,司马迁把这种对立撞击视为互绌:“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同时,因儒道两家观念和治学态度不同或相反,而又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互为表里,互为依存。如老子贵柔,孔子贵刚;老子重天道,孔子重人事;老子偏理性,孔子偏践行。
这两种不同的哲学趋向在学术发展中根据社会需要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就汉代而言,儒道两家一方面势如水火,斗争极为激烈。文景之时,黄老受崇,儒家被贬。《史记·儒林列传》云:“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儒道直接交锋有三次:一次是道家黄生和儒家辕固生汤武是否受命之争,黄生坚持君臣上下的绝对、等级名分,辕固生坚持汤武受命,最后不欢而散。一次是辕固生当着窦太后的面把老子的书说成“家人言耳”,惹怒窦太后,令辕固生与猪搏斗,几乎丧命。一次是武帝元年丞相卫绾奏请罢治申、商、韩非、苏秦等之言,但崇儒的田蚡、王藏等人很快受到窦太后的打击。窦太后死后,田蚡出任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儒家获胜,道家失宠。我们认为儒道两家的斗争不是学术的斗争,而是政治地位之争。
另一方面,儒道两家在汉代一直相互融合。汉初道家《淮南子》承袭了《庄子》、《管子》的传统,多次引《周易》文辞解说之;严君平的《道德经指归》诠释《老子》之作,其论述事理多引《周易》经传之义;严氏弟子扬雄模仿《周易》作《太玄》,融会黄老和《周易》,即扬雄所说的“观大易之损益,览老氏之倚伏”。东汉魏伯阳作《周易参同契》,借用《周易》的概念、理论阐发丹道,反映了汉代儒道会通趋势。若《淮南子》、《道德经指归》、《太玄》、《周易参同契》是援易入道的话,那么,汉初思想家、《易纬》和东汉王充、郑玄、虞翻等人的易学著作则是援道入儒。汉初黄老思想流行,“陆贾、贾谊、韩婴、董仲舒都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引用和发挥着黄老思想。或者用黄老思想补充解释儒家的思想,或者把黄老思想纳入体系,作为一个组成部分,甚至移花接木,用黄老思想为儒家思想作天道观的根据和基础”。(金春峰,第67-68页)成书于西汉末的《易纬》,吸收了道家的观念思想解说宇宙起源和象数产生,东汉王充自觉地引进黄老的自然观念,作为天道观的基石,提出元气自然的理论。大儒马融好老子,撰有《老子注》,其弟子通儒郑玄《礼运注》、《大学注》引老子之言,注《易纬·乾凿度》时,则系统地引进老子的自生、自彰、自通、从无到有、以无为本的思想。
其后汉末虞翻注《周易参同契》和《老子》,并援引老子之言和《周易参同契》中天体纳甲说释《易》,是谓援道入易。自此以后,易老、儒道相互资取、渗透、融合,形成了具有道家特色的易学文化或具有易学特色的道家文化。因此,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易纬》援道入易是易道融合的重要一环,整体上体现着儒道合流的趋势。若没有汉代包括《易纬》在内的易、道融合,就不可能形成魏晋玄学,更不可能形成后世易学特色的道教和以道家为特征的易学。
参考文献
丁原明,1997年:《黄老学论纲》,山东大学出版社。
古籍:《易纬》,《老子》,《庄子》,《冠子》,《黄老帛书》,《管子》,《淮南子》,《太平御览》,《史记》,《风俗通》,《汉书》。
金春峰,1997年:《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钟肇鹏,1985年:见《中国古代佚名哲学名著评述》,齐鲁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