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记住本站永久中文域名:风水业协会.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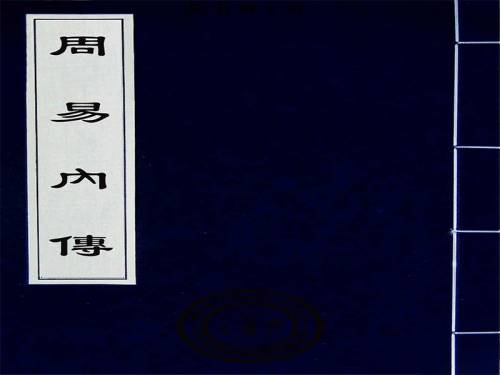
《周易》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摹画天地万物之变,它的符号系统至简,但取义至深,《易》的意义的获得,全靠读《易》者以其知识底蕴对《易》进行解释,解释的路向不同,所得的结果也有异。这就给释《易》者留下了无限广阔的解释空间。《易》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易》的意义的实现,是作《易》者与解《易》视域交汇的产物。《系辞》就说:“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1]认为天下众多、繁赜的事物及其运动变化可归约于卦爻象的变化中,观卦知其理,学《易》者能即卦象卦爻辞之变化而知制《易》者之意,事物的运动变化也可因观象玩辞推论而知。《周易》是一套需要通过解释而获得意义的符号系统。它不会直白地告诉占问者所求之事如何应对,而是告知已经发生的同类事物,要人通过类推而知应对之道。或告诉一些象征性的事物,由占问者通过解释获得正确的义理。解释者有以感性之悟得者,有以理性思考得者,还可由种种象征、比喻、暗示等种种非理性经验而得。所以《系辞》说:“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2]
一、程颐朱熹的义理学解释传统
《周易》的解释学传统至汉代而一大变。就解经说,汉代对《易》的解释最重要的学派有三:一是以孟喜和京房为代表的象数之学,一是以费直为代表的义理学派,一是以严遵为首的黄老学派。孟喜、京房之易以奇偶之数和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解释《周易》经传文,同时讲卦气说,并继承今文经学的传统,利用《周易》讲灾变。费直易学解经多取道德教训之意,用《彖》、《象》、《文言》中所讲的道理发挥《周易》经传文。严遵著《道德经指归》,以《周易》之义解释《老子》。这三家最重要的是孟、京一派的易学。此派易学最重要的是卦气说和纳甲说,将《周易》的卦与二十四节气及七十二物候相配,和干支、五行相配,将《易》坐实为一个定型的框架,这个框架可以装进不同的内容,框架的各个部分也可以由其规则推论而知,削弱了《周易》通过比喻、暗示、象征等进行范围广阔的意义诠释的有效性。汉易的象数传统对后世易学影响极大。
魏晋时代的王弼易学则转一方向,尽扫汉易象数学中滋蔓出来的各种学说,恢复义理学传统。他在解释《周易》经文中引入老庄哲学和东汉古文经学的传统,在解易体例上主取义说、一爻为主说、爻变说、适时说等。这在他介绍注易体例的《周易略例》中有详细说明。王弼非常重视《周易》的解释学传统,如他在《明象》中提出“得意忘象”说,主张通过卦象获取卦义,而获取卦义后就可忘掉卦象。这一说法的核心在通过解释学即象以见义,而一义能表现为不同的物象,故象不可拘泥执定。他说:
夫象,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意可为其征。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惑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蔓,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至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纵复或值,而义无所取。盖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义,义斯见矣。[3]
这里的“象”,可以就卦说指卦爻象,也可以就天地万物说指物象。就易学语言说,这段话是说通过卦象可以获知卦义,通过卦爻辞可以获知卦象,而一卦最重要的是得到其卦义,并由此得到卦义所象征的事物。故得到卦义就可忘掉卦象,得到卦象就可忘掉卦爻辞。既然意义相同的一类事物可以用一种征象来表示,那么要表示健的意义,就不一定非用马(《说卦传》:“乾为马”,“坤为牛”)来代表,要表示顺的意义,就不一定非用牛来代表。而汉易的取象说定马于乾,即乾一定要马来代表,遇到有马无乾的卦爻辞,就用别法穿凿说通,这样好多不正确的说法就产生出来了,如互体、卦变、五行等。这都是由于存象忘意而招致的恶果,故须“得意忘象”。王弼的这段话实际上是预设了一个解释学的前提:一个意义是可以通过多种物象来表示的,不同的物象可以获得同一个意义。而由象到义的获得要通过解释,义与象不是直接等同的,它需要认识者意识的飞跃、灵感的突现来实现意义的类比贯通。解释活动也不是注释、解说、训诂等知识性活动,而是需要调动诸多思想手段来共同完成。解释者在这一活动中不是被动的、呆板的,而是能动的、活泼的、充满了艺术意味的。王弼这一原则的提出,对象数学的框定、演算、坐实等思想方法是一次重创。魏晋玄学思辨的、空灵的、玄想的思想方法和老庄的富于艺术意味的特征结合起来,使中国的经学、史学、文学等经受了一次大的变革,展开为一个新的形态。就易学来说,王弼的解释学一直影响到二程和朱熹。
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是王弼《周易注》之后一部以义理方法解易的名著,在这部书中,解释学的方法得到了更为广阔的运用。程颐关于《周易》的根本解释,表达在他的《易传》序中,此序说:
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至矣。去古虽远,遗经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味,自秦而下,盖无传矣。予生千载之后,悼斯文之凐晦,将俾后人沿流而求源,此传所以作也。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于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会通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其意,则在乎人焉。[4]
在程颐看来,《周易》是对宇宙万物的摹拟,但《周易》所要表达的,不是可用数量摹画的外在相状,而是一种道理。世界是一种道理和法则的宣示,《周易》也是一部道理和法则的宣示。《周易》的六十四卦是这个总的道理在各卦所代表的特殊境遇中的体现。六十四卦虽然代表六十四种境遇,但它经过解释,可以代表天下无尽的境遇。《周易》本卜筮之书,但在程颐这里却成了一部讲道理的书。朱熹对此点见得极精透,他在评论程颐《易传》时说:“《易传》明白,无难看。但伊川以天下许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若作《易》看,即无意味;唯将来作事看,即字字句句有用处。”[5]就是说,《周易程氏传》将《易》来做个载体讲他所见的道理,或者说是借《周易》卦爻发挥他自己的哲学思想。故无一句讲到卜筮,通篇皆在讲事理。朱熹还说:“伊川见得个大道理,却将经来合他这道理,不是解易。……他说求之六经而得,也是于濂溪处见得个大道理,占地位了。”[6]这也是说,程颐先熟读六经,尤其于周敦颐处特有颖悟,以此中义理为基础,然后借《周易》发挥所见。不是伊川解释《周易》,而是《周易》解释伊川。明白朱熹说的这一点,就可以明白程颐解《易》为什么只解六十四卦卦爻辞及《彖传》、《象传》、《文言》而不及系辞以下。因为系辞为《周易》之总论,而伊川通篇皆阐说道理。《说卦》、《序卦》、《杂卦》讲取象说等,伊川皆摒弃不用。这一点也遭到朱熹的批评,说:“《易传》(指《程氏易传》)言理甚备,象数却欠在。”又说:“《易》要分内外卦看,伊川却不甚理会。”“《易传》义理精,字数足,无一毫久缺。亦安得如此自然!只是与本义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书,卦辞爻辞无所不包,看人如何用。程先生只说得一理。”[7]
程颐的这种易学观,对王夫之影响很大。王夫之以《周易》为道德训诫之书,就是在程颐这一基调之上,继续往下延伸。朱熹不同意程颐以《周易》为言理之书,作《周易本义》,欲恢复《周易》本为卜筮之书,后来的易学家从中发挥出道理这一本来面目,强调《周易》的卜筮性质。王夫之吸取了朱熹的看法,不废卜筮而讲道德训诫,所以他的重点放在知得卜筮结果之后君子何以自省,何以接受道德教训而避凶趋吉。王夫之是在吸取了程颐、朱熹的易学观后,在理学观念的支配与影响下产生的易学形态,所以道德意识、人格修养意识在他的《周易》解释中处于压倒一切的地位。另外,程颐本其“天理之学”所讲的道理为天地间事物之阴阳消长、刚柔顺逆等道理,中间亦有人伦道德等道理。这些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道理都是“天理”。天理重在言其本来如此,不可违抗等意思。王夫之所讲的道理则是在圣人观念的支撑下,以道德人格的养成为目的,以境界指引、道德训诫为主要内容。后者具有更多的伦理意味。这些都制约着王夫之的解释趋向。
就解释学本身说,程颐的《易传》序有以下内容:
第一,文本、符号语言不是我们认识本来世界的工具和媒介,而是一种本体性存在。就是说,我们和世界之间并不是一种可以离开符号媒体的本然性存在关系,而是一种通过符号语言与世界本身浑然一体的关系。正是通过使用符号语言的实践,我们参与了世界万物根本道理的展开。进入我们心中最终被我们接受为义理的东西,是经过我们的符号语言直接参与的产物。程颐说的“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可以从两个层面去解释,一是天地万物本身。天地万物是一个不断变化但又与宇宙的总体和谐一致的系统。另一是,《周易》这套符号系统,是随着卦爻时位的变化,因而其顺逆消长、吉凶悔吝也不断变化的系统。程颐是先悟到了天地万物之理,而后宣示于《周易》的符号系统,从而要求学易者、占易者通过这套符号系统认识天地变易以从道这个根本理则。最后的结果是,文本不是直接认识天道的媒介,而是诱发学者将已识得的义理发散出来,并通过细细咀嚼易理使识得的义理更加精细和深入的手段。朱熹曾告诫学《易》者,须先读其他书,待积累了一定的义理基础,然后学《周易》,使其已得磨砻入细。所以朱熹说《周易程氏传》不是启发性的,而是磨砻性的。启发是使没有的东西有,磨砻是使已有的粗粝变得精细。就《周易》的性质说,“随时变易以从道”,这个“道”是经过人的磨砺而由粗变精,由模糊变得清晰,由潜在变得现实的过程。“道”的实现实际是解释者与本然的东西相融合的产物。《周易》之广大悉备,并非它本来即是世界万物,而是它需要学易者、占易者的诠释活动,这个诠释活动对于“知道”、“从道”是本体性的,不是工具性的;是存在论的,不是认识论的。“顺性命之理”、“道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示开物成务之道”,是诠释活动之后达到的境界。“圣人忧患后世”,所以创造《周易》,使人通过诠释活动体会圣人的意思,达到圣人的境界。后世失掉此意,象数之学用先天的象数将世界框定为如此,失去了通过诠释活动以从道这一步骤,圣人之学因此凐晦。
第二,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这一句被程颐视为《周易》的精髓,故其高弟尹和靖认为程颐将这一句写入《易传序》中说破是泄漏天机,程颐称赞尹和靖有此见解“甚是不易”。[8]按朱熹的意思,程颐这句话指“盖自理而言,则即体而用在其中,所谓‘一源’也。自象而言,则即显而微不能外,所谓‘无间’也。”[9]即是说,理是体,象是用,二者同出一源,而在运用中又无间隔。也这是说,《周易》这套符号系统是“因象以明理”,“借象以显义”。这也预设了一个前提:本有的理是先在的,本有的义是有特定内容的,理义因卦爻象这套符号来表现,理义作为本体是需要工具性的东西来阐释的。本体现象中间无有隔阂,诠释者和被诠释者中间也无有隔阂,本体是存在的,它不像实证论者那样是被拒斥的东西;《周易》系统也不是实证性的存在,它是诠释意义的,诠释的过程是通过符号系统来实现的。不但筮人要通过引申、类比、象征等方法把符号系统还原、化约为对义理的显明和照察,求筮者接受筮人讲给自己的义理时还要把它和自己要求筮的具体事项进行类比、引伸等。占筮活动最后在求筮者心中终结并被它说服时,义理已经在占筮者和求筮者中间进行了多重转换。最后的结果是多重视域的融合。朱熹曾这样评论程颐《易传》:“伊川只将一部《易》来作譬喻说了。”所以程颐告诫学《易》者,勿将三百八十四爻只做三百八十四件事看,要依理类推,触类而长,《周易》便可尽包天下之事。这表达的都是同样的意思:《周易》本质上是诠释的、理解的,不是通过客观的、实证的知识达到对真实世界的把握。像象数那样将《周易》坐实为一个可装任何知识的框架而不要求解释,或直接把它作为一个可以分合加减而求合于某种确定内容的东西,都是违背《周易》原意的,都背离了《周易》的诠释性本质。
第三,“观会通以行其典礼”,“由辞以得其义,则在乎人焉。”这二两句是典型的解释学。这是说,易有圣人之道四:辞、变、象、占,《周易》要表达的义理全渗透在辞中,由辞以知变,而象、占在辞中说明。筮者由辞而会通体用、显微而得一卦之义。程颐解释卦象主要用取义说,即据卦爻辞字面的意思说为一事类,就此事类说出道理。但上文已说到,爻辞之间本来没有联系,明显有联系的只是少数,卦名与爻辞也无必然联系。要把本义凐晦的卦辞说为一个事,要把诸多事说成卦名所象征的事类中的具体例证,要把各不同事类所表达的意思说成一个整体,处处需要会通。“会通”者,汇集而贯通,得出一个具有典则性的“一般”,这就是“典礼”。典礼由会通而得,这表示它是一个视域融合的结果。典礼在这里是相对的,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准则,也不是筮者单方面的意向,而是会通的结果。并且程颐要人随视域会通的致思方向走,明确说他只是为卦爻辞作解释,而由这解释以得意义,乃是读《易》者自己的事。这其间存在精粗工拙的不同,也就是说,同一种文本对于不同的解释者具有不同的意义和结果。经过解释活动,经过“会通”,新的结果出现了,这个结果是超越解释者原来的意愿的,因为筮者对赖以传达意义的卦爻辞的解释不是技术性的,目的在使它更清楚明白,而是诠释性的,目的在使它更有意义。它的说服力不来自它对卦爻辞字面上的意思解得符合原意,而是它通过诠释打动筮者的力量。所以说到底,它不是复原而是创造,不是训诂学的而是诠释学的。程颐这种解易方向,或者说他的诠释学方法,对朱熹影响很大。
朱熹较程颐说理的意味减杀。朱熹主张分三圣易:伏羲、文王之易本为卜筮,至孔子作十翼才加入许多道德教训,后世解易又多是借《周易》发挥己意,所以要分别看各人之易。同时朱熹以《周易》为卜筮之书,故不废象数,但究以义理为主。朱熹亦将《周易》系统视作待诠释的系统,主张“活看”,他曾做过一个比喻:“《易》如一个镜相似,看甚物来,都能照得。如所谓‘潜龙’,只是有个潜龙之象,自天子以至庶人,看甚人来,都使得。孔子说作‘龙德而隐,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便是就事上指杀说来。然会看底,虽孔子说也活,也无不通。不会看底,虽文王、周公说的,也死了。须知得他是假托说,是包含说。假托,谓不惹着那事;包含,是说个影象在这里,无所不包。”[10]他对后世注《易》的著作也据其易学观加以总的评论:“《易》最难看,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包含万理,无所不有,其实是古者占卜书,不必只说理,象数皆可说。将去做道家、医家等说亦有,初不曾滞于一偏。某近看《易》,见得圣人本无许多劳攘,自是后世一向乱,妄意增减,硬要作一说以强通其义,所以圣人经旨愈见不明,……说千说万,于《易》原不相干。此书本是难看的物,不可将小巧去说,又不可将大话去说。”[11]朱熹在文本上主张《周易》的各部分有其确定性,如伏羲易是伏羲易,文王易是文王易,孔子易是孔子易,不能混为一谈。他要把后世混在一起的各部分还其本来面目。在文本确定之后,他主张用后出的彖、象来解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但朱熹对《彖传》、《象传》等的兴趣,显然没有对卦爻辞的兴趣大,所以《彖传》、《象传》注得很简略,多一笔带过。《说卦传》、《杂卦传》注寥寥几字,《序卦传》弃而不注。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主张将伏羲易、文王易、孔子易分开。伏羲易无文字,但意义已备于卦画中。文王易、周公易(即六十四卦卦爻辞)最须细读,在此基础上读孔子易。或有不解的,可用孔子易作参考,帮助解释,不可用后者做基础去解前者。他曾说:“读《易》之法,先读正经。不晓,则将彖、象、系辞来解。”又说:“看《易》,且将爻辞看,理会得后,却看象辞,若鹘突地看,便无理会处。”又说:“文王爻辞做得极精严,孔子《传》条畅。要看上面一段,莫便将《传》拘了。”[12]朱熹在为程颐《周易程氏传》写的序言中,集中表达了他对《周易》的根本看法,也表达了他的解释学观点,他认为,《周易》首先是明理之书,所明之理,从根本上说,只有一个,但此根本之理表现为具体事物之理。就《周易》系统说,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所表现的理只是一个,此一理散在卦爻中。这是同他的“理一分殊”说明呼应的。易中根本之理,“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其至大无不包首先体现在卦的丰富性上。本来卦是代表不同境域的(时),境遇无穷,但《周易》只制六十四卦,以此引申、类推至无穷之域。各境遇中的事亦多至无穷,但《周易》只有三百八十四爻,亦引申、类推至无穷多之事。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不知推广,是不知《易》。所以,《周易》需要“得之于精神之运,心术之动”,即在心灵创造、智慧开发中展开阐释活动。最后达到与宇宙同其广大,“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才算知《易》。在朱熹眼中,易是理最切近的体现者。易有卦爻,这是易表现于外的形式;易包含的理,是不能以经验得到的,需要以心灵体会。另外朱熹在这篇序中还强调,易以阴阳二者作为起作用的原因和发生变化的方式。易可用《庄子》的一句话来概括:“易以道阴阳”。所以,易是阴阳之道。卦是阴阳之物,爻是阴阳之动。周易系统六十四卦为体,三百八十四爻为用,大至天地之外,小至一身之中,莫不有阴阳之动,亦莫不有卦爻之象。《周易》作为一个卦爻构成的符号系统,它“顺性命之理,尽变化之道”,故能“先天下而开其物,后天下而成其务”。
二、王夫之的《周易》解释学
程颐、朱熹的易学观对王夫之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从程颐的义理解释学出发,容纳了朱熹易为占卜之书的观点,但他不是把占作为卜问吉凶的活动,而只是作为警醒自己,发现修德上的缺漏,从而更加完善自己的媒介。王夫之的卜问完全是假想的,是处于假想境地的自己对筮得的结果作出的扣问和应对,不是对吉凶休咎的现实预测,它完全是修德之事。他最看重的是导致吉凶的理由从而从善弃恶。相较而言,他对程颐的吸收与取法比朱熹为多,道德训诫的意味也更重。这决定了他对《周易》的处理方式同程颐一样,更多具有解释学的意味。比如王夫之在解释《系辞》“《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一句时说:
《易》统象、占、辞、变而言。“无思无为”,谓于事几未形、物理未著之先,未尝取事物之理,思焉而求其意之精,为焉而营其用之变也;设其象变,系以辞占而已。“寂然不动”,具其理以该四者之道,无适动而为一时一事兆也。“感”者,学《易》者以心遇之,筮者以谋求通焉。“通天下之故”,谓言、动、器、占皆于此而得也,此则至精至变,而括之于一理之浑然,以随感必通,非智计之所能测,唯“天下之至神”乃能与也。天下之至神,诚之至也。健而诚乎健,顺而成乎顺,絪緼而太和,裕于至足之原,精粗、本末、常变皆备于易简之中,故相感者触之,而即与以应得之象数,非待筹量调剂以曲赴乎事物,此则神之所以妙万物而不测也。[13]
这是说,《周易》的卦爻系统本身是不能为的,他只是创设了一些表示变化的象。这些象的卦爻辞下系之以辞,并有关于卜问的吉凶断语。《易》的寂然不动是指这种静态的卦爻辞系统中象、占、辞、变四者之道统括于一理中,此理至静无感,渊默幽深而非表现为一事一时之兆。它要靠感,这个感即学易者以自己心灵的含蕴去扣问这静态的卦爻,然后通过占筮把自己已有的蓄结、理解与占问到的卦爻象会通起来。扣问必涉及到象、占、辞、变。象是卦之阴爻、阳爻、内卦、外卦等,占是吉凶悔吝等相告之断语,辞是卦爻象下所系之辞,它假设了某些情景及在此情景中所做的事,以此提供引申、象征、比喻、类推等等的基础。器是制器者所要效法的底本。此四者皆以叩问《易》体而得。易体“至精至变”,但其究归结为一理。此浑然之理,随叩问者之感而成为其特殊境遇中的独特理解。它是通过象、占、辞、变直接地、直观地实现的,所以只有具备了这种修养境界和直观能力的人才能显示它,不是每个人都能以理性论证而得。这种修养境界是一种识度和相应的直觉能力,故一叩问,即与之以应得的象数,非人力安排而得。这种反应是神妙的,其前提是叩问者具备“天下之至神”的能力,具有静而实、动而灵的品格。
在王夫之这里,《周易》的卦爻系统不是像黑格尔那样以正反合组成的概念层级系统,它不具有以概念的递嬗和升进所带动的思想的流动性,也不具有柏格森式的精神活动的绵延,这些都是认识者对已经有的东西的或理性或直觉的把握,《易》系统给人的是供人联想、引申、类比的一些事项。其中意义的获得完全是通过诠释实现的,最后的结果是《易》系统被叩问者解释出一套完全与《易》提供的事项无关的义理。占筮活动是实践的,不是仅仅被给予的;占筮者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占筮结果是原来的文本和叩问者解释的融合。这种解释活动也不是技术性的、寻求文本“原意”的活动,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诠释。对解释者的知识构成的要求,也不是与文本的技术性因素相关的知识,而是对天地万物的根本理解,即“天下之至神”。解释的过程也不是机械的逻辑推类,而是一种跳跃式的、充满了灵感的活动,故“非智计之所能测”。在王夫之这里,古代创制的易简的筮测工具由于其义理之学的解释性参与而变得神妙无比,占筮活动也更多地具有了本体论的性质而非知识论的活动。就是说,它是一个与对天地万物的觉解有关的活动,而并不仅是以清晰的知性对已有的东西的逻辑推论。所以他把周敦颐的“诚神几”概念引入来表示占筮活动:“诚”是解释者具有的精神境界,“神”是解释者对宇宙万象根本性质的把握,“几”是解释者由其精神境界和知识底蕴对于眼前的具体境遇的闪回切换而有的对象占辞变的具体应用。这里,解释者先在的东西决定了解释的结果。
在对“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一句话的解说中,王夫之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乃其所以极之研之者,无思无为于寂然不动之中,易简而该刚柔摩荡之大用,则问之即应,用之即效,妙用而不测;其功之速成也,则一皆神之为也。非大明于全《易》浑然之体,以得其至变大常之诚,固未足以知此也。要诸其实,则与第一章‘易简而理得’同为一理。唯纯乎健顺,以知太始而作成物,故无深非其深,无几非甚几,以速于应而妙万物。[14]
《易》是用来研究天地间奥秘的工具,它本身无思无为,不具有言告的功能,但他在易简的形式中寓托着深刻的道理。它以阴阳二种爻的上下往来表示万物的冲突、和谐、运动变化,它应答占筮者的任何问题,它的作用神妙莫测。但这些神妙作用的发生实际上靠的是占问者自己的解释,《周易》的神妙实际上是占问者解释的神妙。所以,用《易》者必是知《易》者,知《易》者必是知天地万物之诚者。周易的创制与正确应用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从其制作说,圣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了知万物之情状,故创制卦爻以摹拟天地万物的变化。而对于《周易》的解释又还原为对天地万物的理解。这一来一往之中,人的思维能力和精神境界得到了提高。从自然到人文,从天文地理到易卦系统,这是人的抽象、浓缩、凝聚、象征等思想方式的提高。人不是在自然本身中把握世界,因为人总是被自己所处的时空所拘限,不可能完全跳出经验的圈子。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世界里,人们以此境遇、事项为基础,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积累起来的知识,试图把握整个世界,刻画人类最主要的活动。人通过自己的创设,为更加全面、更加广泛地了解世界,提供了可能。但人对易卦世界中的东西的把握,最终受制于人自己所达到的知识高度、人格高度。“问之即应”,实际的应者是解释者;“用之即效”,这个效果来源于对真实世界的明澈把握。在王夫之的解释学中,人格—包括道德修养、知识积累和境界升华诸方面的实际作为——在解释活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它不是单纯的知识取向所能替代的。所以王夫之在此段解说之后,紧接着就批评了纯知识取向对解释《周易》系统所发生的歧异:“若何晏、夏侯湛之徒,以老庄之浮明,凭其权谋机智,而自谓极深而入神,则足以杀其躯而已。无他,诚与妄之分也。”[15]
解释活动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人们也常常追问解释的有效性。这种追问是人在解释活动发生之后的反思,它伴随着对解释工具是否完善,意义是否有遗漏,解释传递中出现的歧义如何处理等问题的追问而出现。这种追问是人的思想活动处于较高层面的一个标志。《易传》对于《周易》解释学有个方法论的说明,这就是:“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故之舞之以尽神。”[16]这个回答是在“言不尽意”的前提下做出的,它实际上认为,在一般层面上,从不太细致的角度看,《周易》系统可以穷尽天地万物之情状。王夫之对这段话的解说可以说将这一回答推进了一步,在解释学层面,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集中于统会卦爻系统诸要素合而观之,他说:
“书”谓文字;“言”,口所言。言有抑扬轻重之节,在声与气之间,而文字不能别之。言可以著其当然,而不能曲尽其所以然;能传其所知,而不能传其所觉。故设问以示占者、学者,当合卦象鼓舞变通之妙,以征《系辞》之所示,而不但求之于辞也。“象”,阴阳奇偶之画,道之所自出,则《易》之大指不逾于此也。六画配合而成卦,则物情之得失,见于刚柔时位矣。《系辞》则以尽情意之可言者也。利,义之合也。卦象虽具,而变通参伍之,然后所合之义显焉。辞虽有尽,而卦象通变之切于人事者,圣人达其意于辞中,以劝善惩恶,歆动而警戒之,则鼓舞天下之权,于辞而著,是利用出入、便民咸用之神所寓也。如是以玩索于《易》,然后系辞之得失吉凶,皆藏密之实理,而无不可尽之于书矣。夫子示人读《易》之法,于此至为著明。[17]
头两句,以语言与文字在传达意义上功能的一致性,把“书”与“言”作为一个范畴来看待。王夫之的意思是,语言传达的是组成语言的词语的直接意思,但语言有言外之意。语言能传达我们理性所知的东西,但不能传达直觉所显现的东西。而我们所得到的理解往往是直觉的,那么我们如何从语言上得到言外之意?王夫之把这个问题转归到易卦系统时,言主要指卦爻辞,而卦爻辞是理解卦义,进而进行对占筮的解释的主要媒介。他的主张是,要把设卦的意愿、卦象、爻变、卦爻变化的内在动力等要素参合而观,来理解卦爻辞的意思,而不光从卦爻辞求之。卦象由阴阳奇偶即阴爻阳爻构成,是道和理的承载者,道和理皆从象中出。这从他的《周易大象解》中对卦义的解释看得很清楚。一卦之理就是一卦之大旨。此卦的得失,表现于爻之刚柔、时位。卦爻辞是表达一卦的真实情况最基本的依据。还要考虑卦爻辞中吉凶之断语。只有将六爻参合而观,变通而释,然后一卦之义才可见出。王夫之对《文言》中“利者义之和”一句的解释是:“生物各有其义而得其宜,物情各和顺于适然之数,故利也。”[18]即在一卦中,各爻皆有其所代表的具体境遇,但经过变通,和顺于一卦之适然之数,则自然产生利。卦爻只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从表面上看,只说了三百八十四件事,但通过连类比通可以括尽所有的事,卦爻辞中吉凶悔吝的占词,也可以歆动或警戒无数事,由此可以引导人们树立对事件的价值权衡。圣人创制卦爻系统,将无限的解释的可能寄寓在有限的言辞中,以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卜筮者经过咀嚼玩索,将卦爻辞中所包含的理包罗无遗地呈现于胸中。这是作《易》者示人的读《易》正法。
可见,王夫之认为,《周易》中所体现的圣人之道是可以尽见的,但须将《周易》看作一个整体,将易卦的各要素参合观之,然后在这整体中求一卦一爻之义。刚柔、时位皆借象以尽意的工具和媒介。同时还要看出具体境遇中各因素调谐的最佳形态,以得到此境遇中的和义之利。同时在整体背景中观照具体境遇,以此玩索辞意,则言可尽意。在这一段解说中,王夫之对《周易》的解释功能赋予了很多意义。在他这里,一个真正的叩问者、解释者应该从易卦系统得到真、善、用。“真”是卦爻辞中所表示的道和理,“善”是卦爻辞中所表现的价值理想和断占之辞对叩问者的价值趋向的指引,“利”是此境遇中各因素的整体协调从而符合其理想状态所产生的利用之益。这些功能的获得要求叩问者要有诠释的洞见和利用的才能。在这一点上王夫之极似程颐,但又比程颐的解《易》赋予了更多的伦理内容和主体精神。王夫之对《周易》的解释是全方位的,《周易》系统在他这里容纳了一个对天地万物有深刻的觉解的人所具有的全部精神获得。这种获得不是单向度的、孤零的,而是丰富的、各种精神因素互相关联的。其思维方式是投射的、引申的、富有象征意味和超越意义的。这表现了他关于《周易》的一贯主张:《易》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不是卜问吉凶利害的;是人格养成的凭借,不是获得利益的工具。即就获得利益说,也是在和义基础上的自然结果,不是汲汲然唯利是求的。这鲜明地体现出他“《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占学一理”的易学宗旨。
王夫之据此理解对后人解《易》中的单向度特别是其中的知识趋向、利益趋向、排斥运用各种解释手段会通解《易》的趋向提出批评:“自王弼有‘得意忘象’之说,而后之言易者以己意测一端之义,不揆诸象,不以象而征辞,不会通于六爻,不合符于彖象,不上排于阴阳十二位之往来,六十四卦、三十六象之错综,求以见圣人之意,难矣。”[19]而后对他以上所揭橥的主张,反复申言。他在“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一句的注文中说:
此言学《易》者即卦象爻辞变通而尽圣人之意,以利其用也。……六十四卦,天道、人事、物理备矣,可因是以极其赜也。“动”,兴起于善也,玩其辞而劝诫之情自不容已也。“化而载之”者,人之于事业有所太过,则刚以节柔,柔以节刚,于卦之变而得其不滞之理。“推而行之”者,苟其所宜然,则刚益刚而不屈,柔益柔而不违,即已然之志行而进之,于卦之通而得其不穷之用也。如此,则可以尽圣人之意矣。[20]
这是说,六十四卦包天地人之道,天下之繁赜尽于卦爻之中,观象玩辞可知其中之理。此处“动”字,王夫之不以卦中之爻之动静、来去、刚柔、隐显释之,而释之以具有价值意味的“兴起于善”,就是要强调《周易》的劝善惩恶的作用,以免使人将“动”看作状态义而非价值义。“化而载之存乎变”,是说人于卦爻中得变通无滞之理,以此理为标准,对刚柔等行事风格和性格特点注意裁抑使其合于正。“推而行之存乎通”是说如果经过验证己之所持合理、适宜,则坚信不变,推行到底,而得其不穷之用。此数句本来皆是表示卦爻之德的,王夫之的解释将之归置于人事上,强调通过观象玩辞以得到人道教训之意。这一诠释方向的扭转说明,《周易》在王夫之心目中最主要的功能是道德教训,卦中所表现的物理、人事的道理是次要的,从《周易》中吸取人生智慧和人格修养的滋润才是最主要的。这一点是王夫之不同于程颐的地方。程颐是用《周易》卦爻辞去承载他所见得的关于物理人事的道理,王夫之是在这一基础上加强人见此道理后采取行为的自觉性、主动性这一面。
这一面向的强调使王夫之对扣《易》者的个人德性修养有较高要求,他紧接上一段在解释《系辞》中“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一句时说:
承上而推言之,欲见圣人之意以尽《易》之理,又存乎人之德行,而非徒于象、辞求之,或不验于民用,则归咎于书也。易本天道不测之神,神,幽矣,而欲明著之于事业以征其定理,唯君子能之,非小人窃窥阴阳以谋利计功者所知也。若默喻其理,而健顺之德有成象于心,不待《易》言之已及而无不实体其道,唯修德砥行者体仁合一,自与《易》契合,而信《易》言之不诬也。[21]
这里王夫之说出了他的《周易》解释学的重要方面:解释者需要崇高的精神境界和人格修养才能充分体会和理解《周易》的内涵。实际上王夫之表达的是这样的信息:《周易》不是仅仅理智的再现所能把握的,它是道德境界和天地襟怀照察下的产物,它是符号系统和人格映射双重作用的产物,它是作《易》者、解《易》者视域融合的产物,所以“欲见圣人之意以尽《易》之理,又存乎人之德行”。同时它是“实践”的产物,这个实践指解《易》的实践,也指民用这个实践。就解《易》这个实践说,解释者的解释活动是打开《周易》这一矿藏的前提,解释者对于辞、变、象、占的综合眼光,对《易》的全部含蕴的深刻洞察是尽《易》之理的先决条件。《周易》不是独断的诠释所能奏功,它不是在文献中其意义早已清楚明白了,而是在解释者的实践活动中重新被给予意义。被给予意义的深浅多寡端赖解释者的人格和知识底蕴。就民用这个实践说,《周易》中蕴含的治国牧民之理,需要解释者的诠释活动才能把它挖掘出来并推行于民用。从《易》的辞、变、象、占中发现理,发现“天道不测之神”,这需要诠释;将此理推行于事业而证明此理之大用,仍然需要诠释。这就是王夫之的“而欲明著之于事业以得其定理,唯君子能之”的意义。“小人之窥窃阴阳”,指各种形式的象数之学,象数之学是“排甲子死数”,是通过卜筮求取利益,而君子学易,利是义的自然结果。并且君子对《易》的创造性诠释保证了它自然有利益。修德砥行者对理与道的把握,体理于心,则自然与《易》契合。这也说明,《易》是浓缩在卦爻符号中的天理天道,对自然事理的把握与对《易》的符号系统中义理的把握在诠释者心中重合为一。这就是王夫之在此章的总结中所说的“存乎人之德行,则唯君子可以筮而小人不与之理也。”[22]
注释:
[1]见《船山全书》第一册,第570页。
[2]见《船山全书》第一册,第563页。
[3]《周易略例·明彖》,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09页。
[4]《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89页。
[5]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50页。
[6]《朱子语类》第1653页。
[7]《朱子语类》第1651—1652页。
[8]见《二程遗书》卷十八。
[9]《答汪尚书》,《朱子文集》卷三十,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280页。
[10]《朱子语类》第1647页。
[11]《朱子语类》第1661页。
[12]《朱子语类》第1661页。
[13]《船山全书》第一册,第535页。
[14]《船山全书》第一册,第556页。
[15]同上。
[16]《系辞》上传第十二章。按此分章据王夫之《周易内传》。
[17]《船山全书》第一册,第566页。
[18]《船山全书》第一册,第59页。
[19]《船山全书》第一册,第566—567页。
[20]《船山全书》第一册,第570页。
[21]《船山全书》第一册,第570页。
[22]《船山全书》第一册,第5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