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记住本站永久中文域名:风水业协会.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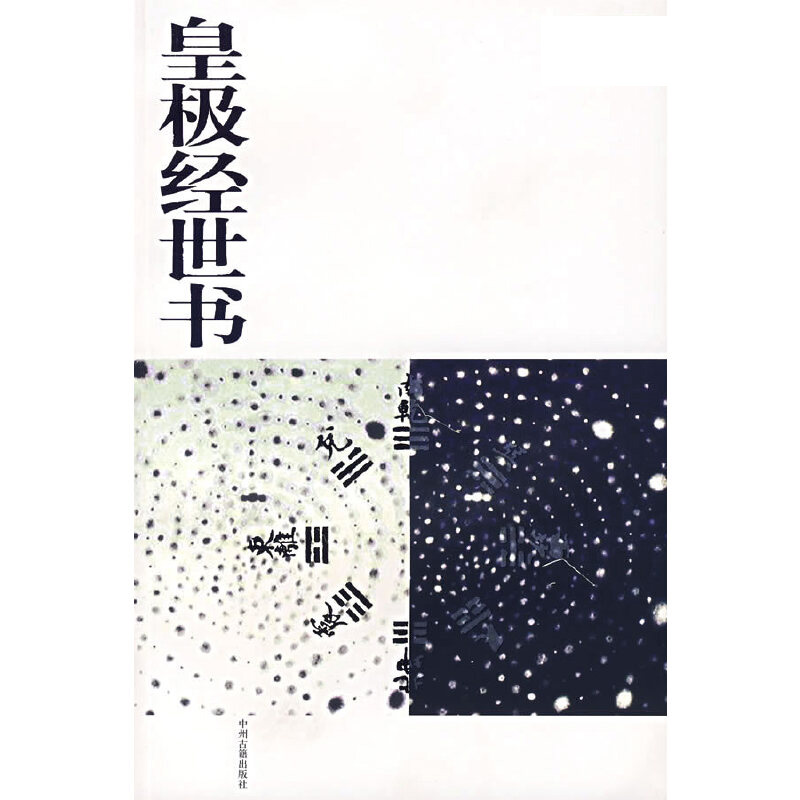
《皇极经世书》十四卷,宋·邵雍撰。邵子数学本于李挺之、穆修,而其源出于陈抟。当李挺之初见邵子于百原,即授以义理性命之学。其作《皇极经世》,盖出于物理之学,所谓《易》外别传者是也。
其书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世,起于帝尧甲辰至后周显德六年己未。而兴亡治乱之迹,皆以卦象推之。
朱子谓“《皇极》是推步之书”,可谓得其要领。朱子又尝谓“自《易》以后,无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齐,包括得尽”;又谓“康节《易》看了,却看别人的不得”。而张岷亦谓此书“本以天道质以人事,辞约而义广,天下之能事毕矣”。
盖自邵子始为此学,其后自张行成、祝泌等数家以外,能明其理者甚鲜,故世人卒莫穷其作用之所以然。其起而议之者则曰,元会运世之分无所依据;十二万九千余年之说近于释氏之劫数;水火土石本于释氏之地水火风,且五行何以去金去木?乾在《易》为天,而《经世》为日,兑在《易》为泽,而《经世》为月,以至离之为星,震之为辰,坤之为水,艮之为火,坎之为土,巽之为石,其取象多不与《易》相同,俱难免于牵强不合。
然邵子在当日用以占验,无不奇中,故历代皆重其书。且其自述大旨亦不专于象数,如云“天下之事,始于重犹卒于轻;始过于厚犹卒于薄”,又云“治生于乱,乱生于治。圣人贵未然之防,是谓《易》之大纲”,又云“天下将治,则人必尚于义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于利也。尚义则谦让之风行焉;尚利则攘夺之风行焉”,类皆立义正大,垂训深切。
是《经世》一书,虽明天道而实责成于人事,洵粹然儒者之言,固非谶纬数家所可同年而语也。
郭彧
今见《道藏·皇极经世》一书有十二卷,总以“观物”名其篇,分《观物篇》五十二篇(一至十二篇为“以元经会”,十三至二十三篇为“以会经运”,二十四至三十四篇为“以运经世”,三十五至四十篇为音律,四十一至五十二篇为杂论)及《观物外篇》上下篇。从《道藏》中辑出之《四库全书·皇极经世书》有十四卷,分《观物篇》六十二篇(一至十二篇为“以元经会”,十三至二十四篇为“以会经运”,二十五至三十四篇为“以运经世”,三十五至五十篇为音律,五十一至六十二篇为杂论)及《观物外篇》上下篇。
我们读两宋间人王湜《易学》及清人王植《皇极经世书解》,即知此十二卷本及十四卷本《皇极经世》皆非邵雍原《皇极经世》之旧。王湜曰:“康节先生遗书,或得于家之草稿,或得于外之传闻。草稿则必欲删而未及,传闻则有讹谬而不实。”又于“皇极经世节要序”中说:“康节先生衍《易》作《经》,曰《皇极经世》。其书浩大,凡十二册,积千三百余板。以元经会二策,以会经运二策,以运经世二策,声音律吕两相唱和四册,准《系辞》而作者二册。”其实,王湜所见十二卷本的《皇极经世》,已是邵伯温于邵雍去世后将《皇极经世》与《观物篇》合在一起,又加入其祖父邵古的声音律吕之学(陈绎《邵古墓铭》:君性简寡,独喜文字,学用声律韵类古今切正,为之解曰正声正字正音者合三十篇。)与张岷听邵雍讲学时所作的笔录(邵伯温定名为《观物外篇》。邵伯温《易学辨惑》:子望平时记录先君议论为多,家人但见其素所宝惜,纳之棺中。其后子坚得其遗稿见授,今《观物外篇》是也。)厘订而成。一至六卷为元会运世,七至十卷为律吕声音,十一卷为“观物内篇”,十二卷为“观物外篇”。对此,清王植已有说明:“《皇极经世》观物一书,邵伯子以为十二卷。一至六则元会运世,七至十则律吕声音,十一二则论以上二数之文也,皆为观物篇。”邵伯温比之《周易》上下经及十翼厘订《皇极经世》为十二卷,前六卷元会运世如上经,中四卷声音律吕如下经,后二卷内外观物则比之上下《系辞》。其后,赵震又分前六卷为三十四篇,中四卷为十六篇。明初《性理大全》则合内篇十二及外篇二,共为六十四篇,至嘉兴徐必达刻《邵子全书》时,分“以元经会”为十二篇、“以会经运”为十二篇、“以运经世”为十篇,前六卷总三十四篇,中四卷仍为十六篇。清王植则总元会运世为三卷、律吕声音为一卷、观物内外篇各二卷,总成八卷。
自邵伯温整理而成十二卷本《皇极经世》之后,其卷数及篇数虽时有不同,然其内容总不外是由其祖父及父亲遗书并张岷听讲笔记而组成。
邵雍《伊川击壤集》有《书皇极经世后》一诗,曰:
朴散人道立,法始乎羲皇。岁月易迁革,书传难考详。
二帝启禅让,三王正纪纲。五伯仗形胜,七国争强梁。
两汉骧龙风,三分走虎狼。西晋擅风流,君凶来北荒。
东晋事清芬,传馨宋齐梁。逮陈不足算,江表成悲伤。
后魏乘晋弊,扫除几小康。迁洛未甚久,旋闻东西将。
北齐举爝火,后周驰星光。隋能一统之,驾福于臣唐。
五代如传舍,天下徒扰攘。不有真主出,何由奠中央?
一万里区宇,四千年兴亡。五百主肇立,七十国开疆。
或混同六合,或控制一方。或创业先后,或垂祚短长。
或奋于将坠,或夺于已昌。或灾兴无妄,或福会不祥。
或患生藩屏,或难起萧墙。或病由唇齿,或疾亟膏肓。
谈笑萌事端,酒食开战场。情欲之一发,利害之相戕。
剧力恣吞噬,无涯罹祸殃。山川才表里,丘垄又荒凉。
荆棘除难尽,芝兰种未芳。龙蛇走平地,玉石碎崑岗。
善设称周孔,能齐是老庄。奈何言已病,安得意都忘。
又《安乐窝中一部书》诗曰:
安乐窝中一部书,号云皇极意如何?春秋礼乐能遗则,父子君臣可废乎?
浩浩羲轩开辟后,巍巍尧舜协和初。炎炎汤武干戈外,汹汹桓文弓剑余。
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铺舒。几千百主出规制,数亿万年成楷模。
治久便忧强跋扈,患深仍念恶驱除。才堪命世有时有,智可济时无世无。
既往尽归闲指点,未来须俟别支梧。不知造化谁为主,生得许多奇丈夫。
又《皇极经世一元吟》诗曰:
天地如盖轸,覆载何高极。日月如磨蚁,往来无休息。
上下之岁年,其数难窥测。且以一元言,其理尚可识。
一十有二万,九千余六百。中间三千年,迄今之陈迹。
治乱与废兴,著见于方策。吾能一贯之,皆如身所历。
我们从这几首诗中即可大体得知,邵雍原本的《皇极经世》的确是一部“本诸天道,质于人事”的书。“皇极”一词出于《尚书·洪范》,九畴中“五皇极”居中,所言为皇帝统治中国的法则。“经世”就是书中“以运经世”的三千年历史大事记。邵雍既曰“安乐窝中一部书,号云皇极意如何”、“中间三千年,迄今之陈迹”,则邵雍原本号为《皇极经世》一书,就是一部简记上下三千余年历史大事之书。
《皇极经世》“经世”,始于公元前2577年,止于公元1023年,时间跨度为3600年。其中有人事标注者,则始于公元前2357年“唐尧”,止于公元963年宋太祖建隆四年,时间跨度为3320年,此即邵雍所谓之“中间三千年”。可用下表简要概括《皇极经世》“以运经世”的内容:
巳会180运- |- 2149世(公元前2577年--2548年)
|
|-2155世(公元前2397年--2368年)
|
|-2156世--甲午(公元前2367年)
||
||-甲辰(公元前2357年)“唐帝尧肇位于平阳……”
||-癸亥(公元前2308年)唐尧二十年
|-2157世--甲子(公元前2337年)“唐帝尧二十一年”
||-癸巳(公元前2308年)唐尧五十年
|-2158世--甲午(公元前2307年)“唐尧五十一年”
||-癸亥(公元前2278年)虞舜八年
|-2159世(公元前2277年--2248年)
|-2160世(公元前2247年--2218年)
午会181运- |-2161世--甲子(公元前2217年)“夏王禹八年”
||-癸巳(公元前2188年)“夏太康”
·
·
·
·
·
·
|-2266世--甲午(公元934年)“后唐闵帝从厚元年”
||
| ·
||-己未(公元959年)“周征契丹……赵匡胤近位检校太傅”
||-癸亥(公元963年)
|-2267世(公元964年--993年)
|-2268世(公元994年--1023年)
这“中间三千年”的历史大事记,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纠正了前史中的一些错误。司马光向皇帝进《资治通鉴》,时当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已是邵雍去世后七年。邵雍与司马光过从甚密,二人必当于学术方面有所切磋。邵雍的《皇极经世》对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当有一定的影响,而皇帝准许司马光借用之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邵雍亦当引为参考。
邵雍《安乐窝中一部书》及《书皇极经世后》之诗作于公元1072年(邵雍时当62岁),由这几首诗可知《皇极经世》成书时间及其大致内容。
至于今见《皇极经世》中“以元经会”及“以会经运”之内容,我们亦可整理作两张简表:
“以元经会”简表:
日(元)甲1
月(会)子1 星(运) 甲1 至亥10 辰(世)子1 至亥120
甲11 至亥20 辰(世)子121至亥240
甲21 至亥30 辰(世)子241至亥360
丑2 星(运) 甲31 至亥40 辰(世)子361至亥480
甲41 至亥50 辰(世)子481至亥600
甲51 至亥60 辰(世)子601至亥720
寅3 星(运) 甲61 至亥70 辰(世)子721至亥840
甲71 至亥80 辰(世)子841至亥960 开物星己76
甲81 至亥90 辰(世)子961至亥1080
卯4 星(运) 甲91 至亥100 辰(世)子1081至亥1200
甲101 至亥110 辰(世)子1201至亥1320
甲111 至亥120 辰(世)子1320至亥1440
辰5 星(运) 甲121 至亥130 辰(世)子1441至亥1560
甲131 至亥140 辰(世)子1561至亥1680
甲141 至亥150 辰(世)子1681至亥1800
巳6 星(运) 甲151至亥160 辰(世)子1801至亥1920
甲161 至亥170 辰(世)子1921至亥2040
甲171 至亥180 辰(世)子2041至亥2160
午7 星(运) 甲181 至亥190 辰(世)子2161至亥2280
甲191 至亥200 辰(世)子2281至亥2400
甲201 至亥210 辰(世)子2401至亥2520
未8 星(运) 甲211 至亥220 辰(世)子2521至亥2640
甲221 至亥230 辰(世)子2641至亥2760
甲231 至亥240 辰(世)子2561至亥2880
申9 星(运) 甲241至亥250 辰(世)子2881至亥3000
甲251 至亥260 辰(世)子3001至亥3120
甲261 至亥270 辰(世)子3121至亥3240
酉10 星(运) 甲271至亥280 辰(世)子3241至亥3360
甲281 至亥290 辰(世)子3361至亥3480
甲291 至亥300 辰(世)子3481至亥3600
戌11 星(运) 甲301至亥310 辰(世)子3601 至亥3720
甲311 至亥320 辰 (世)子3721至亥3840 闭物星戌315
甲321 至亥330 辰(世)子3841至亥3960
亥12 星(运) 甲331至亥340 辰(世)子3961至亥4080
甲341 至亥350 辰(世)子4081至亥4200
甲351 至亥360 辰(世)子4201至亥4320
“以会经运”简表:
寅会之中“开物” 始76运(901世公元前40017年)--90运
卯会91运--120运
辰会121运--150运
巳会151运--180运
至180运2149世始以干支纪年,至2156世甲辰(公元前2357年)标注“唐尧”,
2158世甲辰“洪水方割命鲧治之”、癸丑“徵舜登庸”、乙卯“荐舜于天命之位”、
丙辰“虞舜 正月上日舜受命于文祖”,2159世癸未“帝尧殂落”、丙戌“月正
元日舜格于文祖”,2160世丙辰“荐禹于天命之位”、丁巳(公元前2224年)标
注“夏禹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至2160世末癸亥(公元前2218年)为禹七年。
午会181运--210运
其中181运2161世--190运2280世末为干支纪年,人事标注始2161世癸酉
(禹十七年)“舜陟方乃死”,止2270世丁巳(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
邵雍去世年)。191运--210运只列运数。
未会211运--240运
申会241运--270运
酉会271运--300运
戌会301运--315运(戌会之中“闭物”,始公元46384年)
《皇极经世》卷一、卷二“以元经会”的内容只列世数而不及年。每世为一列,两卷内容总4320列。自2157世列下记“唐尧二十一”至2270世列下记“宋仁宗三十二”,为有帝王纪年内容。如果继续往后推:1894年为2298世之始,当清光绪二十年,1924年为2299世之始,当中华民国十三年,1954年为2300世之始,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年,1984年为2301世之始,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六年……
《皇极经世》“以会经运”内容的时间跨度为86400年(公元前40017年--公元46383年),人事标注自公元前2357年“唐尧”至公元1077年“宋神宗十年”,时间跨度为3434年。“开物”至“闭物”之始总计86400年,“开物”前有27000年,“闭物”后有16200年,合计129600年。
显然,有了邵雍元会运世之说,以“以运经世”的内容即可反推出“以会经运”及“以元经会”的内容。其间人事纪录都是起于唐尧肇位而终于后周显德六年。只不过纪时有长短、纪事有详略之不同而已。
我们从邵雍的有关诗中得知,其所谓的《皇极经世》的内容是“中间三千年”的历史大事记。又从其弟子张岷的记述(《张岷述邵雍行略》:先生治《易》、《书》、《诗》、《春秋》之学,穷意、言、象、数之蕴,明皇、帝、王、霸之道,著书十余万言,研精极思三十年。观天地之消长,推日月之盈缩,考阴阳之度数,察刚柔之形体,故经之以元,纪之以会,始之以运,终之以世。又断自唐、虞,迄于五代,本诸天道,质以人事,兴废治乱,靡所不载。其辞约,其义广;其书著,其旨隐。)邵雍“著书十万余言”,则进一步得知原本《皇极经世》必不是今见之冗长版本,除却《观物篇》(程颢《邵雍先生墓志铭》:有《问》有《观》,以饫以丰。)数万字之外,原本《皇极经世》也只能是“经世”的“三千年”历史大事记内容。
由此可见,今见之《皇极经世》中之“以运经世”及《观物(内)篇》是为邵雍亲笔著述内容,而其余则为其子邵伯温辑入并有所扩展之内容。
四库馆臣谓邵雍之书“能明其理者甚鲜”,其原因则在于“其书浩繁”,而邵雍弟子张岷则称邵雍著述“其辞约,其义广”,显然矛盾。究其根本,“浩繁”的原因就在于邵伯温的整理过程中加入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其祖父的声音律吕之作,又扩展了“以元经会”及“以会经运”的版面,遂使得是书积板达“千三百余板”。如此,焉能不“浩繁”?
其实,我们今天研究邵雍著作,其主要内容就在原本《皇极经世》、《观物(内)篇》及张岷的听讲笔记(即《观物外篇》)。诚然,我们数落邵伯温之过时,亦当不忘他的贡献则在于《观物外篇》的整理存世。而邵古的“声律韵类古今切正,为之解曰正声正字正音者合三十篇”则不在邵雍的“先天之学”范围之内,亦不当为所谓“易外别传”的内容。
《皇极经世书》观物篇
郭彧点校(以《道藏》本为底本,参以《四库全书》本)
物之大者,无若天地,然而亦有所尽也。天之大,阴阳尽之矣;地之大,刚柔尽之矣。阴阳尽而四时成焉;刚柔尽而四维成焉。
夫四时四维者,天地至大之谓也。凡言大者,无得而过之也。亦未始以大为自得,故能成其大。岂不谓至伟至伟者欤?
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尽之矣。
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尽之矣。
静之始则柔生焉,静之极则刚生焉。一柔一刚交而地之用尽之矣。
动之大者谓之太阳,动之小者谓之少阳,静之大者谓之太阴,静之小者谓之少阴。
太阳为日,太阴为月,少阳为星,少阴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体尽之矣。
太柔为水,太刚为火,少柔为土,少刚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体尽之矣。
日为暑,月为寒,星为昼,辰为夜。暑寒昼夜交而天之变尽之矣。
水为雨,火为风,土为露,石为雷。雨风露雷交而地之化尽之矣。
暑变物之性,寒变物之情,昼变物之形,夜变物之体。性情形体交而动植之感尽之矣。雨化物之走,风化物之飞,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飞草木交而动植之应尽之矣。
走,感暑而变者性之走也;感寒而变者情之走也;感昼而变者形之走也;感夜而变者体之走也。
飞,感暑而变者性之飞也;感寒而变者情之飞也;感昼而变者形之飞也;感夜而变者体之飞也。
草,感暑而变者性之草也;感寒而变者情之草也;感昼而变者形之草也;感夜而变者体之草也。
木,感暑而变者性之木也;感寒而变者情之木也;感昼而变者形之木也;感夜而变者体之木也。
性,应雨而化者走之性也;应风而化者飞之性也;应露而化者草之性也;应雷而化者木之性也。
情,应雨而化者走之情也;应风而化者飞之情也;应露而化者草之情也;应雷而化者木之情也。
形,应雨而化者走之形也;应风而化者飞之形也;应露而化者草之形也;应雷而化者木之形也。
体,应雨而化者走之体也;应风而化者飞之体也;应露而化者草之体也;应雷而化者木之体也。
性之走善色,情之走善声,形之走善气,体之走善味。性之飞善色,情之飞善声,形之飞善气,体之飞善味。性之草善色,情之草善声,形之草善气,体之草善味。性之木善色,情之木善声,形之木善气,体之木善味。
走之性善耳,飞之性善目,草之性善口,木之性善鼻。走之情善耳,飞之情善目,草之情善口,木之情善鼻。走之形善耳,飞之形善目,草之形善口,木之形善鼻。走之体善耳,飞之体善目,草之体善口,木之体善鼻。
夫人也者,暑寒昼夜无不变,雨风露雷无不化,性情形体无不感,走飞草木无不应。以目善万物之色,耳善万物之声,鼻善万物之气,口善万物之味。灵于万物,不亦宜乎。
人之所以能灵于万物者,谓其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声色气味者,万物之体也。目耳口鼻者,万人之用也。
体无定用,惟变是用。用无定体,惟化是体。体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备矣。然则天亦物也,圣亦人也。
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万物之物,有亿物之物,有兆物之物。为兆物之物,岂非人乎!
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万人之人,有亿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为兆人之人,岂非圣乎!
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谓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谓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谓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谓也。以一至物而当一至人,则非圣人而何?人谓之不圣,则吾不信也。何哉?谓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物观万物,一世观万世者焉。又谓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功,身代天事者焉。又谓其能以上顺天时,下应地理,中徇物情,通尽人事者焉。又谓其能以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今古,表里时事者焉。
噫,圣人者,非世世而效圣焉。吾不得而目见之也。虽然吾不得而目见之,察其心,观其迹,探其体,潜其用,虽亿万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
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别有天地万物,异乎此天地万物。”则吾不得而知之也。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圣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谓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谓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恶得而言之乎?以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谓妄知也。以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谓妄言也。吾又安能从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所以谓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谓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谓之命者,处理性者也。所以能处理性者,非道而何?是知道为天地之本,天地为万物之本。以天地观万物,则万物为万物,以道观天地,则天地亦为万物。
道之道尽之于天矣,天之道尽之于地矣,天地之道尽之于万物矣,天地万物之道尽之于人矣。人能知其天地万物之道所以尽于人者,然后能尽民也。
天之能尽物,则谓之曰昊天。人之能尽民,则谓之曰圣人。谓昊天能异乎万物,则非所以谓之昊天也。谓圣人能异乎万民,则非所以谓之圣人也。万民与万物同,则圣人固不异乎昊天者矣。然则圣人与昊天为一道,圣人与昊天为一道,则万民与万物亦可以为一道。一世之万民与一世之万物亦可以为一道,则万世之万民与万世之万物亦可以为一道也。明矣。
夫昊天之尽物,圣人之尽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谓也。阴阳升降于其间矣。圣人之四府者,《易》、《书》、《诗》、《春秋》之谓也。《礼》、《乐》污隆于其间矣。春为生物之府,夏为长物之府,秋为收物之府,冬为藏物之府。号物之庶谓之万,虽曰万之又万,其庶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易》为生民之府,《书》长民之府,《诗》为收民之府,《春秋》为藏民之府。号民之庶谓之万,虽曰万之又万,其庶能出此圣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之四府者,时也。圣人之四府者,经也。昊天以时授人,圣人以经法天。天人之事,当如何哉?
观春则知《易》之所存乎?观夏则知《书》之所存乎?观秋则知《诗》之所存乎?观冬则知《春秋》之所存乎?
《易》之《易》者,生生之谓也。《易》之《书》者,生长之谓也。《易》之《诗》者,生收之谓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谓也。
《书》之《易》者,长生之谓也。《书》之《书》者,长长之谓也。《书》之《诗》者,长收之谓也。《书》之《春秋》者,长藏之谓也。
《诗》之《易》者,收生之谓也。《诗》之《书》者,收长之谓也。《诗》之《诗》者,收收之谓也。《诗》之《春秋》者,收藏之谓也。
《春秋》之《易》者,藏生之谓也。《春秋》之《书》者,藏长之谓也。《春秋》之《诗》者,藏收之谓也。《春秋》之《春秋》者,藏藏之谓也。
生生者修夫意者也,生长者修夫言者也,生收者修夫象者也,生藏者修夫数者也。
长生者修夫仁者也,长长者修夫礼者也,长收者修夫义者也,长藏者修夫智者也。
收生者修夫性者也,收长者修夫情者也,收收者修夫形者也,收藏者修夫体者也。
藏生者修夫圣者也,藏长者修夫贤者也,藏收者修夫才者也,藏藏者修夫术者也。
修夫意者三皇之谓也,修夫言者五帝之谓也,修夫象者三王之谓也,修夫数者五伯之谓也。
修夫仁者有虞之谓也,修夫礼者夏禹之谓也,修夫义者商汤之谓也,修夫智者周发之谓也。
修夫性者文王之谓也,修夫情者武王之谓也,修夫形者周公之谓也,修夫体者召公之谓也。
修夫圣者秦穆之谓也,修夫贤者晋文之谓也,修夫才者齐桓之谓也,修夫术者楚庄之谓也。
皇帝王伯者,《易》之体也。虞夏商周者,《书》之体也。文武周召者,《诗》之体也。秦晋齐楚者,《春秋》之体也。
意言象数者,《易》之用也。仁义礼智者,《书》之用也。性情形体者,《诗》之用也。圣贤才术者,《春秋》之用也。
用也者,心也。体也者,迹也。心迹之间有权存焉者,圣人之事也。
三皇同意而异化,五帝同言而异教,三王同象而异劝,五伯同数而异率。同意而异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归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无为无有之谓也。无为者,非不为也,不固为者也,故能广。无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固能大。广大悉备,而不固为固有者,其唯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归焉。所以圣人有言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其斯之谓欤?
三皇同仁而异教化,五帝同礼而异教,三王同义而异劝,五伯同智而异率。同礼而异皆者必以德。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归之,故尚让。夫尚让也者,先人后己之谓也。以天下授人而不为轻,若素无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为重,若素有之也。若素无素有者,谓不己无己有之也。若己无己有,则举一毛以取与于人,犹有贪鄙之心生焉,而况天下者乎?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己之天下者,其唯五帝乎?是故能以德教天下者,天下亦以德归焉。所以圣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其斯之谓欤?
三皇同性而异化,五帝同情而异教,三王同形而异劝,五伯同体而异率。同形而异劝者必以功。以功劝民者,民亦以功归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谓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则谓之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则谓之贼矣。以利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贼,安有弑君耶?是故知王者,正也。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下亦以功归焉。所以圣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其斯之谓欤?
三皇同圣而异化,五帝同贤而异教,三王同才而异劝,五伯同术而异率。同术而异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归之,故尚争。夫争也者,争夫利者也。取与利不以义,然后谓之争。小争交以言,大争交以兵。争夫强者也,犹借夫名也者,谓之曲直。名也者,命物正事之称也。利也者,养人成务之具也。名不以仁,无以守业。利不以义,无以居功。名不以功居,利不以业守,则乱矣,民所以必争之也。五伯者,借虚名以争实利者也。帝不足则王,王不足则伯,伯又不足则夷狄矣。若然则五伯不谓无功于中国,语其王则未也。过夷狄则远矣。周之东迁,文武之功德于是乎尽矣。犹能维持二十四君。王室不绝如线,夷狄不敢屠害中原者,由五伯借名之力也。是故知能以力率天下者,天下亦以力归焉。所以圣人有言曰:“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哸人,凶。武人为于大君。”其斯之谓欤?
夫意也者尽物之性也,言也者尽物之情也,象也者尽物之形也,数也者尽物之体也。仁也者尽人之圣也,礼也者尽人之贤也,义也者尽人之才也,智也者尽人之术也。
尽物之性者谓之道,尽物之情者谓之德,尽物之形者谓之功,尽物之体者谓之力。尽人之圣者谓之化,尽人之贤者谓之教,尽人之才者谓之劝,尽人之术者谓之率。
道德功力者,存乎体者也。化教劝率者,存乎用者也。体用之间有变存焉者,圣人之业也。夫变也者,昊天生万物之谓也。权也者,圣人生万民之谓也。非生物生民,而得谓之权变乎?
善化天下者,止于尽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于尽德而已。善劝天下者,止于尽功而已。
善率天下者,止于尽力而已。
以道德功力为化者,乃谓之皇矣。以道德功力为教者,乃谓之帝矣。以道德功力为劝者,乃谓之王矣。以道德功力为率者,乃谓之伯矣。
以化教劝率为道者,乃谓之《易》矣。以化教劝率为德者,乃谓之《书》矣。以化教劝率为功者,乃谓之《诗》矣。以化教劝率为力者,乃谓之《春秋》矣。
此四者,天地始则始焉,天地终则终焉。始终随乎天地者也。
夫古今者,在天地间犹旦暮也。以今观今,则谓之今矣;以后观今,则今亦谓之古矣。以今观古,则谓之古矣;以古自观,则古亦谓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为古,今亦未必为今。皆自我而观之也。安知千古之前万古之后,其人不自我而观之也。
若然,则皇帝王伯者,圣人之时也;《易》、《书》、《诗》、《春秋》者,圣人之经也。时有消长;经有因革。时有消长,否、泰尽之矣;经有因革,损、益尽之矣。否、泰尽而体、用分;损、益尽而心、迹判。体与用分,心与迹判,圣人之事业于是乎备矣。所以,自古当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摄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摄命者革而革者也。因而因者长而长者也;因而革者长而消也;革而因者消而长也;革而革者消而消也。革而革者,一世之事业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业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业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业也。可以因则因,可以革则革者,万世之事业也。一世之事业者,非五伯之道而何?十世之事业者,非三王之道而何?百世之事业者,非五帝之道而何?千世之事业者,非三皇之道而何?万世之事业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伯者命世之谓也;仲尼者不世之谓也。仲尼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如是则何止于百世而已哉!亿千万世皆可得而知之也。
人皆知仲尼之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为仲尼则已,如欲必知仲尼之所以为仲尼,则舍天地将奚之焉?
人皆知天地之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则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则舍动静将奚之焉?
夫一动一静者,天地至妙者欤?夫一动一静之间者,天地人至妙至妙者欤?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尽三才之道者,谓其行无辙迹也。
孔子赞《易》自羲、轩而下,序《书》自尧、舜而下,删《诗》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轩而下,祖三皇也。自尧、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孙五伯也。祖三皇,尚贤也。宗五帝,亦尚贤也。三皇尚贤以道,五帝尚贤以德。子三王,尚亲也。孙五伯,亦尚亲也。三王尚亲以功,五伯尚亲以力。呜呼,时之既往亿万千年,时之未来亦亿万千年,何祖宗之寡而子孙之多耶?此所以重赞尧、舜,至禹曰:“禹,吾无间然矣。”仲尼后禹千五百余年,今之后仲尼又千五百余年,虽不敢比德仲尼,上赞尧、舜、禹,岂不敢如孟子上赞仲尼乎?
人谓仲尼惜乎无土,吾独以为不然。匹夫以百亩为土,大夫以百里为土,诸侯以四境为土,天子以四海为土,仲尼以万世为土。若然则孟子言自生民以来,未有有如夫子,斯亦不为之过矣。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与其富然后能富。人不能自贵,必待天与其贵然后能贵。若然则富贵在天也,不在人也。有求而得之者,有求而不得者矣。是系乎天者也。功德在人也,不在天也。可修而得之,不修则不得。是非系乎天也,系乎人者也。夫人之能求而得富贵者,求其可得者也。非其可得者,非所以能求之也。昧者不知,求而得之,则谓其己之能得也,故矜之;求而不得,则谓其人之不与也,故怨之。如知其己之所以能得,人之所以能与,则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邪!
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贵也,岂可妄意求而得之也。虽然,天命亦未始不由积功累行,圣君艰难以成之,庸君暴虐以坏之。是天欤?是人欤?是人欤?是知人作之咎,固难逃已。天降之灾,禳之奚益?积功累行,君子常分,非有求而然也。有求而然者,所以谓利乎仁者也。君子安有余事于其间哉!然而有幸与不幸者,始可语命也已。
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虐失天下;殷汤以功有天下,殷纣以虐失天下;周武以功有天下,周幽以虐失天下。三者虽时不同,其成败之形一也。平王东迁,无功以复王业;赧王西走,无虐以丧王室。威令不逮一小国,诸侯仰存于五伯而已。此又奚足道哉!但时无真王者出焉。虽有虚名,与杞宋其谁曰少异?是时也。《春秋》之作不亦宜乎!
仲尼修经周平王之时,《书》终于晋文侯,《诗》列为王国风,《春秋》始于鲁隐公,《易》尽于未济卦。予非知仲尼者,学为仲尼者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出自诸侯,天子之重去矣。宗周之功德自文、武出,而出自幽、厉,文、武之基息矣。由是犬戎得以侮中国。周之诸侯非一,独晋能攘去戎狄,徙王东都洛邑,用存王国,为天下伯者之唱,秬鬯圭瓒之所锡,其能免乎?《传》称子贡欲去鲁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是知名存实亡者,犹愈于名实俱亡者矣。礼虽废而羊存,则后世安知无不复行礼者矣。晋文公尊王,虽用虚名,犹能力使天下诸侯知周有天子,而不敢以兵加之也。及晋之丧也,秦由是敢灭周。斯爱礼之言,信不诬矣。
齐景公尝一日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是时也,诸侯僭天子,陪臣执国命,禄去公室,政出私门。景公自不能上奉周天子,欲其臣下奉己,不亦难乎?厥后齐祚卒为田氏所移。夫齐之有田氏者,亦犹晋之有三家也。晋之有三家,亦犹周之有五伯也。韩、赵、魏之于晋也,既立其功,又分其地,既卑其主,又夺其国。田氏之于齐也,既得其禄,又专其政,既杀其君,又移其祚。其如天下之事,岂无渐乎?履霜之戒,宁不思乎?《传》称王者往也。能往天下者可以王矣。周之衰也,诸侯不朝天子久矣。及楚预中国会盟,仲尼始进爵为之子,其于僭王也,不亦陋乎?
夫以力胜人者,人亦以力胜之。吴尝破越而有轻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骄齐之志,贪婪攻取,不顾德义,侵侮齐晋,专以夷狄为事,遂复为越所灭。越又不监之,其后复为楚所灭。楚又不监之,其后复为秦所灭。秦又不监之,其后复为汉所伐。恃强凌弱,与豺狼何以异乎?非所以谓中国义理之师也,宋之为国也,爵高而力卑者乎?盟不度德,会不量力,区区与诸侯并驱中原,耻居其后。其于伯也,不亦难乎?
周之同姓诸侯而克永世者,独有燕在焉。燕处北陆之地,去中原特远,苟不随韩、赵、魏、齐、楚较利刃,争虚名,则足以养德待时,观诸侯之变。秦虽虎狼,亦未易加害。延十五、六年后,天下事未可知也。
中原之地方九千里,古不加多而今不加少。然而有祚长祚短地大地小者,攻守异故也。自三代以降,汉、唐为盛,秦界于周、汉之间矣。秦始盛于穆公,中于孝公,终于始皇。起于西夷,迁于岐山,徙于咸阳。兵渎宇内,血流天下,并吞四海,庚革古今。虽不能比德三代,非晋、隋可同年而语也。其祚之不永,得非用法太酷,杀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书》终于《秦誓》一事,其旨不亦远乎?
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杀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义,汉之好生也亦以义。秦之好杀也以利,楚之好杀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义,而汉且不及。秦之好杀也以利,而楚又过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择于周、秦、汉、楚哉?择乎善恶而已。是知善也者无敌于天下,而天下共善之。恶也者亦无敌于天下,而天下亦共恶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择于周、秦、汉、楚哉?择乎善恶而已。
昔者孔子语尧舜,则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语汤武,则曰“顺乎天而应乎人”。斯言可以该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尧禅舜以德,舜秛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则入于功矣。汤伐桀以放,武伐纣以杀。以放王也,以杀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则入于杀矣。是知时有消长,事有因革,前圣后圣非出于一途哉。
天与人相为表里。天有阴阳,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系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则民用正,上好佞则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来矣。虽圣君在上,不能无小人,是难其为小人。虽庸君在上,不能无君子,是难其为君子。自古圣君之盛,未有如唐尧之世,君子何其多耶,时非无小人也,是难其为小人,故君子多也。所以虽有四凶,不能肆其恶。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商纣之世,小人何其多耶,时非无君子也,是难其为君子,故小人多也。所以虽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知君择臣臣择君者,是系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系乎人也,系乎天者也。
贤愚人之本性,利害民之常情。虞舜陶于河滨,傅说筑于岩下。天下皆知其贤,而百执事不为之举者,利害使之然也。吁,利害丛于中而矛戟森于外,又安知有虞舜之圣而傅说之贤哉?河滨非禅让之所,岩下非求相之方。昔也在亿万人之下,而今也在亿万人之上,相去一何远之甚也!然而必此云者,贵有名者也。
《易》曰:“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险,往且有功,虽危无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以之,是知古之人患名过实者有之矣。其间有幸与不幸者,虽圣人力有不及者矣。伊尹行冢宰,居责成之地。借使避放君之名,岂曰不忠乎?则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终始之大忠者乎?吁,若委寄于匪人,三年之间其于嗣君何?则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伊尹也?“坎,有孚维心,亨”,不亦近之乎?
《易》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刚健主豫,动而有应,群疑乃亡,能自强故也。周公以之,是知圣人不能使人无谤,能处谤者也。周公居总,已当任重之地。借使避灭亲之名,岂曰不孝乎?则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保嗣君,成终始之大孝乎?吁,若委寄于匪人,七年之间其于嗣君何?则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周公也?“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不亦近之乎?
夫天下将治,则人必尚行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言也。尚行则笃实之风行焉;尚言则诡谲之风行焉。天下将治,则人必尚义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利也。尚义则谦让之风行焉;尚利则攘夺之风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伯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于义也,尚言者必入于利也。义利之相去一何远之如是耶?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尽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闻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见之;尽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聪明犹不可欺,况神之聪明乎?是知无愧于口不若无愧于身,无愧于身不若无愧于心。无口过易,无身过难。无身过易,无心过难。既无心过,何难之有?吁,安得无心过之人而与之语心哉!是故知圣人所以能立乎无过之地者,谓其善事于心者也。
仲尼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是知武王虽逮舜之尽善尽美,以其解天下之倒悬,则下于舜一等耳。桓公虽不逮武之应天顺人,以其霸诸侯一匡天下,则高于狄亦远矣。以武比舜,则不能无过,比桓则不能无功。以桓比狄则不能无功,比武则不能无过。汉氏宜立乎其武、桓之间矣。是时也,非会天下民厌秦之暴且甚,虽十刘季百子房,其于人心之未易何?且古今之时则异也,而民好生恶死之心非异也。自古杀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厌之乎?杀人之多不必以刃,谓天下之人无生路可趋,而又况以刃多杀天下之人乎?秦二世万乘也,求为黔首而不能得。汉刘季匹夫也,免为元首而不能已。万乘与匹夫相去有间矣,然而有时而代之者,谓其天下之利害有所悬之耳。天之道非祸万乘而福匹夫也,谓其祸无道而福有道也。人之情非去万乘而就匹夫也,谓其去无道而就有道也。万乘与匹夫相去有间矣,然而有时而代之者,谓其直以天下之利害有所悬之耳。
日既没矣,月既望矣,星不能不希矣。非星之希,是星难乎为其光矣,能为其光者不亦希乎?汉、唐既创业矣,吕、武既擅权矣,臣不能不希矣。非臣之希,是臣难乎为忠矣,能为其忠者不亦希乎?是知从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难。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难。苟能成之,又何计乎死与生也?如其不成,虽死奚益?况其有正与不正者乎?是其死于不正,孰若生于正?与其生于不正,孰若死于正?在乎忠与智者之一择焉。死固可惜,贵乎成天下事也。如其败天下之事,一死奚以塞责?生固可爱,贵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败天下之事,一生何以收功?噫,能成天下之事,又能不失其正而生者,非汉之留侯,唐之梁公而何?微斯二人,则汉唐之祚或几乎移矣。岂若虚生虚死者譬之萧艾,忠与智者不游乎其间矣。
仲尼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自极乱至于极治,必三变矣。三皇之法无杀,五伯之法无生。伯一变至于王矣,王一变至于帝矣,帝一变至于皇矣。其于生也,非百年而何?是知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如春温如也,如夏燠如也,如秋凄如如也,如冬冽如也。春夏秋冬者,昊天之时也。《易》、《书》、《诗》、《春秋》者,圣人之经也。天时不差则岁功成矣,圣经不忒则君德成矣。天有常时,圣有常经,行之正则正矣,行之邪则邪矣。邪正之间有道在焉。行之正则谓之正道,行之邪则谓之邪道。邪正由人乎?由天乎?
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则异也,其于由道一也。夫道也者,道也。道无形,行之则见于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亿万年行之,人知其归者也。或曰:“君子道长则小人道消,君子道消则小人道长。长者是,则消者非也;消者是,则长者非也。何以知正道邪道之然乎?”吁,贼夫人之论也!不曰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国行中国事,夷狄行夷狄事,谓之正道。君行臣事,臣行君事,父行子事,子行父事,夫行妻事,妻行夫事,君子行小人事,小人行君子事,中国行夷狄事,夷狄行中国事,谓之邪道。至于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伦之为道也;三代之世乱,乱未有不乱人伦之为道也。后世之慕三代之治世者,未有不正人伦者也;后世之慕三代之乱世者,未有不乱人伦者也。自三代而下,汉唐为盛,未始不由治而兴,乱而亡。况其不盛于汉唐者乎?其兴也,又未始不由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国之道盛;其亡也,又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盛。噫,二道对行,何故治世少而乱世多耶?君子少而小人多耶?曰:岂不知阳一而阴二乎?天地尚由是道而生,况其人与物乎?人者,物之至灵者也。物之灵未若人之灵,尚由是道而生,又况人灵于物者乎?是知人亦物也,以其至灵,故特谓之人也。
日经天之元,月经天之会,星经天之运,辰经天之世。
以日经日则元之元可知之矣;以日经月则元之会可知之矣;以日经星则元之运可知之矣;以日经辰则元之世可知之矣。
以月经日则会之元可知之矣;以月经月则会之会可知之矣;以月经星则会之运可知之矣;以月经辰则会之世可知之矣。
以星经日则运之元可知之矣;以星经月则运之会可知之矣;以星经星则运之运可知之矣;以星经辰则运之世可知之矣。
以辰经日则世之元可知之矣;以辰经月则世之会可知之矣;以辰经星则世之运可知之矣;以辰经辰则世之世可知之矣。
元之元一,元之会十二,元之运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
会之元十二,会之会一百四十四,会之运四千三百二十,会之世五万一千八百四十。
运之元三百六十,运之会四千三百二十,运之运一十二万九千六百,运之世一百五十五万五千二百。
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世之会五万一千八百四十,世之运一百五十五万五千二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万二千四百。
元之元以春行春之时也;元之会以春行夏之时也;元之运以春行秋之时也;元之世以春行冬之时也。
会之元以夏行春之时也;会之会以夏行夏之时也;会之运以夏行秋之时也;会之世以夏行冬之时也。
运之元以秋行春之时也;运之会以秋行夏之时也;运之运以秋行秋之时也;运之以秋春行冬之时也。
世之元以冬行春之时也;世之会以冬行夏之时也;世之运以冬行秋之时也;世之世以冬行冬之时也。
皇之皇以道行道之事也;皇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皇之王以道行功之事也;皇之伯以道行力之事也。
帝之皇以德行道之事也;帝之帝以德行德之事也;帝之王以德行功之事也;帝之伯以德行力之事也。
王之皇以功行道之事也;王之帝以功行德之事也;王之王以功行功之事也;王之伯以功行力之事也。
伯之皇以力行道之事也;伯之帝以力行德之事也;伯之王以力行功之事也;伯之伯以力行力之事也。时有消长,事有因革。非圣人无以尽之。所以仲尼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是知千万世之时,千万世之经,岂可画地而轻言也哉!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国,冬之余冽也。汉王而不足,晋伯而有余。三国,伯之雄者也。十六国,伯之丛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朝,伯之传舍也。隋,晋之子也。唐,汉之弟也。隋季诸郡之伯,江汉之余波也。唐季诸镇之伯,日月之余光也。后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
自尧舜至于今,上下三千余年,前后百有余世,书传可明纪者,四海之内,九州之间,其间或合或离,或治或隳,或强或羸,或唱或随,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风俗者。吁,古者谓三十年为一世,岂徒然哉?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浃,民之情始可一变矣。苟有命世之人继世而兴焉,则虽民如夷狄,三变而帝道可举。惜乎时无百年之世,世无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则贤之与不肖,何止于相半也?时之难不其然乎?人之难不其然乎?
太阳之体数十,太阴之体数十二,少阳之体数十,少阴之体数十二。少刚之体数十,少柔之体数十二,太刚之体数十,太柔之体数十二。
进太阳、少阳、太刚、少刚之体数,退太阴、少阴、太柔、少柔之体数,是谓太阳、少阳、太刚、少刚之用数。进太阴、少阴、太柔、少柔之体数,退太阳、少阳、太刚、少刚之体数,是谓太阴、少阴、太柔、少柔之用数。太阳、少阳、太刚、少刚之体数一百六十,太阴、少阴、太柔、少柔之体数一百九十二。太阳、少阳、太刚、少刚之用数一百一十二,太阴、少阴、太柔、少柔之用数一百五十二。
以太阳、少阳、太刚、少刚之用数唱太阴、少阴、太柔、少柔之用数,是谓日月星辰之变数。以太阴、少阴、太柔、少柔之用数唱太阳、少阳、太刚、少刚之用数,是谓水火土石之化数。日月星辰之变数一万七千二十四,谓之动数。水火土石之化数一万七千二十四,谓之植数。再唱和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变化通数二万八千九百八十一万六千五百七十六,谓之动植通数。
日月星辰者,变乎暑寒昼夜者也;水火土石者,化乎风雨露雷者也。暑寒昼夜者,变乎性情形体者也;风雨露雷者,化乎走飞草木者也。暑变走飞草木之性,寒变走飞草木之情,昼变走飞草木之形,夜变走飞草木之体。雨化性情形体之走,风化性情形体之飞,露化性情形体之草,雷化性情形体之木。性情形体者,本乎天者也;走飞草木者,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分阴分阳之谓也;本乎地者,分刚分柔之谓也。夫分阴分阳、分刚分柔者,天地万物之谓也。备天地万物者,人之谓也。
有日日之物者也,有日月之物者也,有日星之物者也,有日辰之物者也。
有月日之物者也,有月月之物者也,有月星之物者也,有月辰之物者也。
有星日之物者也,有星月之物者也,有星星之物者也,有星辰之物者也。
有辰日之物者也,有辰月之物者也,有辰星之物者也,有辰辰之物者也。
日日物者,飞飞也,日月物者,飞走也,日星物者,飞木也,日辰物者,飞草也。
月日物者,走飞也,月月物者,走走也,月星物者,走木也,月辰物者,走草也。
星日物者,木飞也,星月物者,木走也,星星物者,木木也,星辰物者,木草也。
辰日物者,草飞也,辰月物者,草走也,辰星物者,草木也,辰辰物者,草草也。
有皇皇之民者也,有皇帝之民者也,有皇王之民者也,有皇伯之民者也。
有帝皇之民者也,有帝帝之民者也,有帝王之民者也,有帝伯之民者也。
有王皇之民者也,有王帝之民者也,有王王之民者也,有王伯之民者也。
有伯皇之民者也,有伯帝之民者也,有伯王之民者也,有伯伯之民者也。
皇皇民者士士也,皇帝民者士农也,皇王民者士工也,皇伯民者士商也。
帝皇民者农士也,帝帝民者农农也,帝王民者农工也,帝伯民者农商也。
王皇民者工士也,王帝民者工农也,王王民者工工也,王伯民者工商也。
伯皇民者商士也,伯帝民者商农也,伯王民者商工也,伯伯民者商商也。
飞飞物者性性也,飞走物者性情也,飞木物者性形也,飞草物者性体也。
走飞物者情性也,走走物者情情也,走木物者情形也,走草物者情体也。
木飞物者形性也,木走物者形情也,木木物者形形也,木草物者形体也。
草飞物者体性也,草走物者体情也,草木物者体形也,草草物者体体也。
士士民者仁仁也,士农民者仁礼也,士工民者仁义也,士商民者仁智也。
农士民者礼仁也,农农民者礼礼也,农工民者礼义也,农商民者礼智也。
工士民者义仁也,工农民者义礼也,工工民者义义也,工商民者义智也。
商士民者智仁也,商农民者智礼也,商工民者智义也,商商民者智智也。
飞飞之物一之一,飞走之物一之十,飞木之物一之百,飞草之物一之千。
走飞之物十之一,走走之物十之十,走木之物十之百,走草之物十之千。
木飞之物百之一,木走之物百之十,木木之物百之百,木草之物百之千。
草飞之物千之一,草走之物千之十,草木之物千之百,草草之物千之千。
士士之民一之一,士农之民一之十,士工之民一之百,士商之民一之千。
农士之民十之一,农农之民十之十,农工之民十之百,农商之民十之千。
工士之民百之一,工农之民百之十,工工之民百之百,工商之民百之千。
商士之民千之一,商农之民千之十,商工之民千之百,商商之民千之千。
一一之飞当兆物,一十之飞当亿物,一百之飞当万物,一千之飞当千物。
十一之走当亿物,十十之走当万物,十百之走当千物,十千之走当百物。
百一之木当万物,百十之木当千物,百百之走当百物,百千之木当十物。
千一之草当千物,千十之草当百物,千百之草当十物,千千之草当一物。
一一之士当兆民,一十之士当亿民,一百之士当万民,一千之士当千民。
十一之农当亿民,十十之农当万民,十百之农当千民,十千之农当百民。
百一之工当万民,百十之工当千民,百百之工当百民,百千之工当十民。
千一之商当千民,千十之商当百民,千百之商当十民,千千之商当一民。
为一一之物能当兆物者,非巨物而何?为一一之民能当兆民者,非巨民而何?为千千之物能分一物者,非细物而何?为千千之民能分一民者,非细民而何?固知物有大小,民有贤愚。移昊天生兆物之德而生兆民,则岂不谓至神者乎?移昊天养兆物之功而养兆民,则岂不谓至圣者乎?吾而今而后知践形为大,非大圣大神之人,岂有不负于天地者矣?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谓之理者,穷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性者,尽之而后而知之也。所以谓之命者,至之而后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虽圣人无以过之也,而过之者非所以谓之圣人也。夫鉴之所以能为明者,谓其能不隐万物之形也。虽然鉴之能不隐万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万物之形也。虽然水之能一万物之形,又未若圣人之能一万物之情也。谓其圣人之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与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为己之目,其目无所不观矣。用天下之耳为己之耳,其耳无所不听矣。用天下之口为己之口,其口无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为己之心,其心无所不谋矣。夫天下之观,其于见也不亦广乎?天下之听,其于闻也不亦远乎?天下之言,其于论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谋,其于乐也不亦大乎?夫其见至广,其闻至远,其论至高,其乐至大,能为至广至远至高至大之事而中无一为焉,岂不谓至神至圣者乎?非唯吾谓之至神至圣者乎,而天下谓之至神至圣者乎。而千万世之天下谓之至神至圣者乎。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
郭彧点校
(以《四库全书》本张行成《观物外篇衍义》为主,参以《道藏》本)
天数五,地数五,合而为十,数之全也。天以一而变四,地以一而变四。四者有体也,而其一者无体也,是谓有无之极也。天之体数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地之体数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是故无体之一以况自然也。不用之一以况道也。用之者三以况天地人也。
体者八变,用者六变。是以八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以六卦变而成八也。
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反易者二十八,以三十六变而成六十四也。
故爻止于六,卦尽于八。策穷于三十六,而重卦极于六十四也。卦成于八,重于六十四,爻成于六;策穷于三十六,而重于三百八十四也。
天有四时,一时四月,一月四十日,四四十六,各去其一,是以一时三月,一月三十日也。四时体数也,三月、三十日用数也。体虽具四,而其一常不用也,故用者止于三而极于九也。体数常偶,故有四,有十二;用数常奇,故有三,有九。
大数不足而小数常盈者,何也?以其大者不可见而小者可见也。故时止乎四,月止乎三,而日盈乎十也。是以人之肢体有四而指有十也。
天见乎南而潜乎北,极于六而余于七。是以人知其前昧其后,而略其左右也。
天体数四而用三,地体数四而用三。天克地,地克天,而克者在地,犹昼之余分在夜也。是以天三而地四。天有三辰,地有四行也。然地之大,且见且隐,其余分之谓耶?
乾七子,兑六子,离五子,震四子,巽三子,坎二子,艮一子,坤全阴,故无子。乾七子,坤六子,兑五子,艮四子,离三子,坎二子,震一子,巽刚,故无子。
天有二正,地有二正,而共用二变以成八卦也。天有四正,地有四正,共用二十八变以成六十四卦也。是以小成之卦,正者四,变者二,共六卦也。大成之卦,正者八,变者二十八,共三十六卦也。乾坤坎离为三十六卦之祖也,兑震巽艮为二十八卦之祖也。
乾坤七变,是以昼夜之极不过七分也。艮兑六变,是以月止于六,共为十二也。离坎五变,是以日止于五,共为十日也。震巽四变,是以体止于四,共为八也。
卦之正、变共三十六,而爻又有二百一十六,则用数之策也。三十六去四则三十二也,又去四则二十八也,又去四则二十四也。故卦数三十二位,去四而言之也;天数二十八位,去八而言之也;地数二十四位,去十二而言之也。四者乾坤坎离也,八者并颐、中孚、大、小过也。十二者,并兑、震、泰、既济也。
日有八位而用止于七,去乾而言之也。月有八位而用止于六,去兑而言之也。星有八位而用止于五,去离而言之也。辰有八位而用止于四,去震而言之也。
日有八位,而数止于七,去泰而言之也。
月自兑起者,月不能及日之数也。故十二月常余十二日也。
乾,阳中阳,不可变,故一年止举十二月也。震,阴中阳,不可变,故一日之十二时不可见也。兑,阳中阴,离,阴中阳,皆可变,故日月之数可分也。是阴数以十二起,阳数以三十起,常存二六也。
举年见月,举月见日,举日见时,阳统阴也。是天四变含地四变。日之变含月与星辰之变也。是以一卦含四卦也。
日一位,月一位,星一位,辰一位。日有四位,月有四位,星有四位,辰有四位。四四有十六位。此一变而日月之数穷矣。
天有四变,地有四变,变有长也,有消也。十六变而天地之数穷矣。
日起于一,月起于二,星起于三,辰起于四。引而伸之,阳数常六,阴数常二,而小大之运穷。
三百六十变为十二万九千六百。
十二万九千六百变为一百六十七亿九千六百一十六万。
一百六十七亿九千六百一十六万变为二万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万七千四百五十六亿。
以三百六十为时,以十二万九千六百为日,以一百六十七亿九千六百一十六万为月,以二万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万七千四百五十六亿为年,则大小运之数立矣。
二万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万七千四百五十六亿分而为十二,前六限为长,后六限为消,以当一年十二月之数,而进退三百六十日矣。
一百六十七亿九千六百一十六万分而为三十,以当一月三十日之数,随大运消长而进退六十日矣。十二万九千六百分而为十二,以当一日十二时之数,而进退六日矣。三百六十以当一时之数,随小运之进退,以当昼夜之时也。
十六变之数,去其交数,取其用数,得二万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万七千四百五十六亿。分为十二限,前六限为长,后六限为消,每限得十三亿九千九百六十八万之一百六十七亿九千六百一十六万。
每一百六十七亿九千六百一十六万年,开一分,进六十日也。六限开六分,进三百六十日也。犹有余分之一,故开七分,进三百六十六日也。其退亦是矣。
十二万九千六百,去其三者,交数也,取其七者,用数也。用数三而成于六,加余分故有七也。七之得九万七百二十年,半之得四万五千三百六十年,以进六日也。
日有昼夜,数有杋杊,以成十有二日也。每三千六百年进一日,凡四万三千二百年进十有二日也。余二千一百六十年以进余分之六,合交数之二千一百六十年,共进十有二分以为闰也。
故小运之变,凡六十而成三百六十有六日也。六者三天也,四者两地也。天统乎体而托地以为体,地分乎用而承天以为用。天地相依,体用相附。
乾为一,乾之五爻分而为大有,以当三百六十之数也。乾之四爻分而为小畜,以当十二万九千六百之数也。乾之三爻分而为履,以当一百六十七亿九千六百一十六万之数也。乾之二爻分而为同人,以当二万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万七千四百五十六亿之数也。乾之初爻分而为姤,以当七稊九千五百八十六万六千一百一十垓九千九百四十六万四千八京八千四百三十九万一千九百三十六兆之数也。是谓分数也。分大为小,皆自上而下,故以阳数当之。
一生二为夬,当十二之数也。二生四为大壮,当四千三百二十之数也。四生八为泰,当五亿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二千之数也。八生十六为临,当九百四十兆三千六百九十九万六千九百一十五亿二千万之数也。十六生三十二为复,当二千六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七十垓三千六百六十四万八千八百京二千九百四十七万九千七百三十一兆二千万亿之数也。三十二生六十四,为坤,当无极之数也。是谓长数也。长大为小,皆自下而上,故以阴数当之。
天统乎体,故八变而终于十六;地分乎用,故六变而终于十二。天起于一而终于七稊九千五百八十六万六千一百一十垓九千九百四十六万四千八京八千四百三十九万一千九百三十六兆;地起于十二而终于二百四垓六千九百八十万七千三百八十一京五千四百九十三万八千四百九十九兆七百二十万亿也。
有地然后有二,有二然后有昼夜。二三以变,错综而成,故《易》以二而生数,以十二而变,而一非数也,非数而数以之成也。天行不息,未尝有昼夜,人居地上以为昼夜,故以地上之数为人之用也。
天自临以上,地自师以上,运数也。天自同人以下,地自遯以下,年数也。运数则在天者也;年数则在地者也。天自贲以上,地自艮以上,用数也。天自明夷以下,地自否以下,交数也。天自震以上,地自晋以上,有数也。天自益以下,地自豫以下,无数也。
天之有数起乾而止震,余入于无者,天辰不见也。地去一而起十二者,地火常潜也。故天以体为基而常隐其基,地以用为本而常藏其用也。
一时止于三月,一月止于三十日,皆去其辰数也。是以八八之卦六十四,而不变者八,可变者七。七八五十六,其义亦由此矣。
阳爻昼数也,阴爻夜数也。天地相衔,阴阳相交,故昼夜相杂,刚柔相错。春夏阳多也,故昼数多夜数少;秋冬阴多也,故昼数少夜数多。
体数之策三百八十四,去乾坤坎离之策为用数三百六十。
体数之用二百七十,去乾与坎离之策为用数之用,二百五十二也。体数之用二百七十,其一百五十六为阳,一百一十四为阴。去离之策得一百五十二阳,一百一十二阴,为实用之数也。盖阳去离而用乾,阴去坤而用坎也。是以天之阳策一百一十二,地之阴策一百一十二,阳策四十,去其南北之阳也。
极南大暑,极北大寒,物不能生,是以去之也。其四十为天之余分耶?阳侵阴,昼侵夜,是以在地也。合之为一百五十二阳,一百一十二阴也。阳去乾之策,阴去坎之策,得一百四十六阳,一百八阴,为用数之用也。阳三十六,三之为一百八;阴三十六,三之为一百八。三阳三阴,阴阳各半也。阳有余分之一为三十六,合之为一百四十六阳,一百八阴也。故体数之用二百七十,而实用者三百六十四,用数之用二百五十二也。
卦有六十四而用止乎三十六,爻有三百八十四而用止乎二百一十六也。六十四分而为二百五十六,是以一卦去其初、上之爻,亦二百五十六也,此生物之数也。故离坎为生物之主,以离四阳、坎四阴,故生物者必四也。阳一百一十二,阴一百一十二,去其离坎之爻则二百一十六也。阴阳之四十共为二百五十六也。
是以八卦用六爻,乾坤主之也。六爻用四位,离坎主之也。故天之昏晓不生物,而日中生物,地之南北不生物,而中央生物也。体数何为者也?生物者也。用数何为者也?运行者也。运行者天也,生物者地也。天以独运,故以用数自相乘,而以用数之用为生物之时也。地偶而生,故以体数之用,阳乘阴为生物之数也。
天数三,故六六而又六之,是以乾之策二百一十六也。地数两,故十二而十二之,是以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也。乾用九,故三其八为二十四,而九之亦二百一十有六,两其八为十六,而九之亦百四十有四也。坤用六,故三其十二为三十六,而六之亦二百一十有六也,两其十二为二十四,而六之亦百四十有四也。
坤以十二之三,十六之四,六之一与半,为乾之余分,则乾得二百五十二,坤得一百八也。
阳四卦十二爻,八阳四阴,以三十六乘其阳,以二十四乘其阴,则三百八十四也。
体有三百八十四而用止于三百六十,何也?以乾、坤、坎、离之不用也。乾、坤、坎、离之不用,何也?乾、坤、坎、离之不用所以成三百六十之用也。故万物变易而四者不变也,夫惟不变,是以能变也。用止于三百六十而有三百六十六,何也?数之盈也。数之盈则何用也?乾之全用也。乾、坤不用,则坎、离用半也。乾全用者,何也?阳主盈也。乾坤不用者,何也?独阳不生,寡阴不成也。离、坎用半,何也?离东坎西,当阴阳之半,为春秋昼夜之门也。或用乾,或用离、坎,何也?主阳而言之,故用乾也,主赢分而言之,则阳侵阴,昼侵夜,故用离、坎也。阳主赢,故乾全用也。阴主虚,故坤全不用也。阳侵阴,阴侵阳,故离、坎用半也。是以天之南全见而北全不见,东西各半也。离、坎,阴阳之限也,故离当寅,坎当申,而数常逾之者,盖阴阳之溢也。然用数不过乎寅,交数不过乎申。乾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为阴所克,坤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为所克之阳也。故乾得三十六,而坤得十二也。阳主进,是以进之为三百六十日;阴主消,是以十二月消十二日也。
顺数之,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逆数之,震一,离兑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
乾四十八,兑三十,离二十四,震十,坤十二,艮二十,坎三十六,巽四十。
乾三十六,坤十二,离兑巽二十八,坎艮震二十。对离上正更思之。
圆数有一,方数有二,奇偶之义也。六即一也,十二即二也。天圆而地方,圆者数之起一而积六;方者数之起一而积八。变之则起四而积十二也。六者常以六变,八者常以八变,而十二者亦以八变,自然之道也。
八者天地之体也,六者天地之用也,十二者地之用也。天变方为圆而常存其一,地分一为四而常执其方。天变其体而不变其用也,地变其用而不变其体也。六者并其一而为七,十二者并其四而为十六也。阳主进,故天并其一而为七;阴主退,故地去其四而止于十二也。是阳常存一而阴常晦一也,故天地之体止于八,而天之用极于七,地之用止于十二也。圆者刓方以为用,故一变四,四去其一则三也,三变九,九去其三则六也;方者引圆以为体,故一变三,并之四也。四变十二,并之十六也。故用数成于三而极于六,体数成于四而极于十六也。是以圆者径一而围三,起一而积六;方者分一而为四,分四而为十六,皆自然之道也。
一役二以生三,三去其一则二也。三生九,九去其一则八也,去其三则六也。故一役三,三复役二也。三役九,九复役八与六也。是以二生四,八生十六,六生十二也。三并一则为四,九并三则为十二也,十二又并四则为十六。故四以一为本,三为用;十二以三为本,九为用;十六以四为本,十二为用。
六变而三十六矣,八变而成六十四矣,十二变而成一百一十四矣。六六而变之,八八六十四变而成三百八十四矣。八八而变之,六八四十八变而成三百八十四矣。
圆者六变,六六而进之,故六十变而三百六十矣。方者八变,故八八而成六十四矣。阳主进,是以进之为六十也。
蓍数不以六而以七,何也?并其余分也。去其余分,则六,故策数三十六也。是以五十者,六十四卦闰岁之策也。其用四十有九者,六十卦一岁之策也。归奇挂一,犹一岁之闰也。卦直去四者,何也?天变而地效之。是以蓍去一,则卦去四也。
圆者径一围三,重之则六;方者径一围四,重之则八也。《易》始三画,圆者之用,径一围三也,重之则六,故有六爻。《易》始四象,方者之体,径一围四也,重之则八,故有八卦。天地万物体皆有四,用皆有三。圣人作《易》以自然之理而示诸人尔。
裁方而为圆,天所有运行;分大而为小,地所有生化。故天用六变,地用四变也。
一八为九,裁为七,八裁为六,十六裁为十二,二十四裁为十八,三十二裁为二十四,四十裁为三十,四十八裁为三十六,五十六裁为四十二,六十四裁为四十八也。一分为四,八分为三十二,十六分为六十四,以至九十六分为三百八十四也。
一生六,六生十二,十二生十八,十八生二十四,二十四生三十,三十生三十六,引而伸之,六十变而生三百六十矣,此运行之数也。四生十二,十二生二十,二十生二十八,二十八生三十六,此生物之数也。故乾之阳策三十六,离、巽之阳策二十八,坎、艮之阳策二十,坤之阳策十二也。
圆者一变则生六,去一则五也。二变则生十二,去二则十也。三变则生十八,去三则十五也。四变则二十四,去四则二十也。五变则三十,去五则二十五也。六变则三十六,去六则三十也。是以存之则六六,去之则五五也。五则四而存一也,四则三而存一也,三则二而存一也,二则一而存一也。故一生二,去一则一也,二生三,去一则二也,三生四,去一则三也,四生五,去一则四也。是故二以一为本,三以二为本,四以三为本,五以四为本,六以五为本也。更思之。
方者一变而为四,四生八,并四而为十二;八生十二,并八而为二十;十二生十六,并十二而为二十八;十六生二十,并十六而为三十六也。一生三,并而为四也,十二生二十,并而为三十二也,二十八生三十六,并而为六十四也。
《易》之大衍何数也?圣人之倚数也。天数二十五,合之为五十;地数三十,合之为六十。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五十者,蓍数也;六十者,卦数也。五者,蓍之小衍也,故五十为大衍也;八卦者,卦之小成也,则六十四为大成也。
蓍德圆以况天之数,故七七四十九也。五十者,存一而言之也。卦德方以况地之数也,故八八六十四也。六十者,去四而言之也。蓍者,用数也;卦者,体数也。用以体为基,故存一也;体以用为本,故去四也。圆者本一;方者本四,故蓍存一而卦去四也。蓍之用数七,若其余分亦存一之义也,挂其一亦存一之义也。
蓍之用数,挂一以象三,其余四十八则一卦之策也。四其十二为四十八也。十二去三为用九,四三十二,所去之策也,四九三十六,所用之策也,以当乾之三十六阳爻也。十二去五而用七,四五二十,所去之策也,四七二十八,所用之策也,以当兑、离之二十八阳爻也。十二去六而用六,四六二十四,所去之策也,四六二十四,所用之策也,以当坤之二十四阴爻也。十二去四而用八,四四十六,所去之策也,四八三十二,所用之策也,以当坎、艮之二十四阴爻也,并上卦之八阴为三十二爻也。是故,七、九为阳,六、八为阴也。九者,阳之极数,六者,阴之极数。数极则反,故为卦之变也。震、巽无策者,以当不用之数。天以刚为德,故柔者不见,地以柔为体,故刚者不生,是以震、巽无策也。乾用九,故其策九也。四之者,以应四时,一时九十日也。坤用六,故其策亦六也。
奇数四:有一,有二,有三,有四;策数四:有六,有七,有八,有九,合为八数,以应方数之八变也。归奇合卦之数有六:谓五与四四也;九与八八也;五与四八也;九与四八也;五与八八也;九与四四也。以应圆数之六变也。
奇数极于四而五不用,策数极于九而十不用。五则一也,十则二也,故去五、十而用四、九也。奇不用五,策不用十,有无之极也,以况自然之数也。
卦有六十四而用止于六十者,何也?六十卦者,三百六十爻也,故甲子止于六十也,六甲而天道穷矣。是以策数应之三十六与二十四,合之则六十也。三十二与二十八,合之亦六十也。
乾四十八,坤十二;震二十,巽四十;离兑三十二,坎艮二十八,合之为六十。
蓍数全,故阳策三十六与二十八合之为六十四也。卦数去其四,故阴策二十四与三十二合之为五十六也。
九进之为三十六,皆阳数也,故为阳中之阳;七进之为二十八,先阳而后阴也,故为阳中之阴;六进之为二十四,皆阴数也,故为阴中之阴;八进之为三十二,先阴而后阳也,故为阴中之阳。
蓍四进之则百,卦四进之则百二十。百则十也,百二十则十二也。
归奇合卦之数,得五与四四,则策数四九也;得九与八八,则策数四六也;得五与八八、得九与四八,则策数皆四七也;得九与四四、得五与四八,则策数皆四八也。为九者一变以应乾也,为六者一变以应坤也,为七者二变以应兑与离也,为八者二变以应艮与坎也。五与四四,去挂一之数,则四三十二也,九与八八,去挂一之数,则四六二十四也,五与八八、九与四八,去挂一之数,则四五二十也,九与四四、五与四八,去挂一之数,则四四十六也。故去其三、四、五、六之数,以成九、八、七、六之策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参伍以变,错综其数也。如天地之相衔,昼夜之相交也。一者,数之始而非数也,故二二为四,三三为九,四四为十六,五五为二十五,六六为三十六,七七为四十九,八八为六十四,九九为八十一,而一不可变也。百则十也,十则一也,亦不可变也。是故,数去其一而极于九,皆用其变者也。五五二十五,天数也,六六三十六,乾之策也,七七四十九,大衍之用数也,八八六十四,卦数也,九九八十一,《玄》、《范》之数也。
大衍之数,其算法之源乎?是以算数之起,不过乎方圆曲直也。乘数,生数也;除数,消数也。算法虽多,不出乎此矣。
阴无一,阳无十。
阳得阴而生,阴得阳而成。故蓍数四而九,卦数六而十也。犹干支之相错,干以六终而支以五终也。
三四十二也,二六亦十二也,二其十二二十四也,三八亦二十四也,四六亦二十四也,三其十二三十六也,四九亦三十六也,六六亦三十六也,四其十二四十八也,三其十六亦四十八也,六八亦四十八也,五其十二六十也,三其二十亦六十也,六其十亦六十也。皆自然之相符也。
四九三十六也,六六三十六也,阳六而兼阴六之半,是以九也,故以二卦言之,阴阳各三也,以六爻言之,天地人各二也。阴阳之中各有天地人,天地人之中各有阴阳,故参天两地而倚数也。
阳数一,衍之而十,十干之类是也;阴数二,衍之为十二,十二支、十二月之类是也。
一变而二,二变而四,三变二而八卦成矣。四变而十有六,五变而三十有二,六变而六十四卦备矣。
《易》有真数,三而已矣。参天者,三三而九;两地者,倍三而六。参天两地而倚数,非天地之正数也。倚者拟也,拟天地正数而生也。
《易》之生数十二万九千六百,总为四千三百二十世。此消长之大数,衍三十年之辰数,即其数也。岁三百六十日,得四千三百二十辰,以三十乘之,得其数矣。凡甲子、甲午为世首。此为《经世》之数,始于日甲月子星甲辰子。又云:此《经世》日甲之数,月子、星甲、辰子从之也。
一、十、百、千、万、亿,为倚天之数也;十二、百二十、千二百、万二千、亿二万,为偶地之数也。
五十分之则为十,若参天两之则为六,两地又两之,则为四。此天地分太极之数也。
复至乾,凡百有十二阳,姤至坤,凡八十阳;姤至坤,凡百有十二阴,复至乾,凡八十阴。
阳数于三百六十上盈;阴数于三百六十上缩。
人为万物之灵,寄类于走。走阴也,故百二十。
有一日之物,有一月之物,有一时之物,有一岁之物,有十岁之物,至于百千万皆有之。天地亦物也,亦有数焉。
卦之反对皆六阴六阳也。在《易》则六阳六阴者,十有二对也,去四正,则八阳四阴、八阴四阳者,各六对也,十阳二阴、十阴二阳者,各三对也。
圆者星也,历纪之数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画州井地之法其仿于此乎?
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
太极既分,两仪立矣。阳下交于阴,阴上交于阳,四象生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也。十分为百,百分为千,千分为万,犹根之有干,干之有枝,枝之有叶,愈大则愈少,愈细则愈繁,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是故,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长之,巽以消之,长则分,分则消,消则翕也。
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兑离坎艮再交也。故震阳少而阴尚多也,巽阴少而阳尚多也,兑离阳浸多也,坎艮阴浸多也,是以辰与火不见也。
一气分而阴阳判,得阳之多者为天,得阴之多者为地。是故,阴阳半而形质具焉,阴阳偏而性情分焉,形质又分,则多阳者为刚也,多阴者为柔也,性情又分,则多阳者阳之极也,多阴者阴之极也。
兑离巽得阳之多者也,艮坎震得阴之多者也,是以为天地用也。乾阳极,坤阴极,是以不用也。
乾四分取一以与坤,坤四分取一以奉乾。乾坤各合而生六子,三男皆阳也,三女皆阴也。兑分一阳以与艮,坎分一阴以奉离,震巽以二相易。合而言之,阴阳各半,是以水火相生而相克,然后既成万物也。
乾坤之名位不可易也,坎离名可易而位不可易也,震巽位可易而名不可易也,兑艮名与位皆可易也。
离肖乾,坎肖坤,中孚肖乾,颐肖离,小过肖坤,大过肖坎,是以乾、坤、坎、离、中孚、颐、大小过,皆不可易者也。
离在天而当夜,故阳中有阴也,坎在地而当昼,故阴中有阳也。震始交阴而阳生,巽始消阳而阴生,兑阳长也,艮阴长也。震兑在天之阴也,巽艮在地之阳也,故震兑上阴而下阳,巽艮上阳而下阴。天以始生言之,故阴上而阳下,交泰之义也,地以既成言之,故阳上而阴下,尊卑之位也。
乾坤定上下之位,离坎列左右之门,天地之所阖辟,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昼夜长短、行度盈缩,莫不由乎此矣。
自下而上谓之升,自上而下谓之降。升者生也,降者消也。故阳生于下,阴生于上,是以万物皆反生,阴生阳,阳生阴,阴复生阳,阳复生阴,是以循环而无穷也。
阴阳生而分两仪,两仪交而生四象,四象交而生八卦,八卦交而生万物。故两仪生天地之类,四象定天地之体;四象生日月之类,八卦定日月之体;八卦生万物之类,重卦定万物之体。类者,生之序也,体者,象之交也。推类者必本乎生,观体者必由乎象。生则未来而逆推,象则既成而顺观。是故,日月一类也,同出而异处也,异处而同象也。推此以往,物奚逃哉!
天变时而地应物,时则阴变而阳应,物则阳变而阴应。故时可逆知,物必顺成。是以阳迎而阴随,阴逆而阳顺。
语其体则天分而为地,地分而为万物,而道不可分也。其终则万物归地,地归天,天归道。是以君子贵道也。
有变则必有应也。故变于内者应于外,变于外者应于内,变于下者应于上,变于上者应于下也。天变而日应之,故变者从天而应者法日也。是以日纪乎星,月会于辰,水生于土,火潜于石,飞者栖木,走者依草,心肺之相联,肝胆之相属,无他,变应之道也。
阳交于阴而生蹄角之类也,刚交于柔而生根莇之类也,阴交于阳而生羽翼之类也,柔交于刚而生支干之类也。天交于地,地交于天,故有羽而走者,足而腾者,草中有木,木中有草也。各以类而推之,则生物不过是矣。走者便于下,飞者利于上,从其类也。
陆中之物,水中必具者,犹影象也。陆多走水多飞者,交也。是故,巨于陆者必细于水,巨于水者必细于陆也。
虎豹之毛犹草也,鹰鹍之羽犹木也。
木者星之子,是以果实象之。
叶阴也,华实阳也,枝叶软而根干坚也。
人之骨巨而体繁,木之干巨而枝繁,应天地之数也。
动者体横,植者体纵,人宜横而反纵也。
飞者有翅,走者有趾。人之两手,翅也,两足,趾也。
飞者食木,走者食草,人皆兼之而又食飞走也,故最贵于万物也。
体必交而后生,故阳与刚交而生心肺,阳与柔交而生肝胆,柔与阴交而生肾与膀胱,刚与阴交而生脾胃。心生目,胆生耳,脾生口,肺生骨,肝生肉,胃生髓,膀胱生血。故乾为心,兑为脾,离为胆,震为肾,坤为血,艮为儿子,坎为髓,巽为骨,泰为目,中孚为鼻,既济为耳,颐为口,大过为肺,未济为胃,小过为肝,否为膀胱。
天地有八象,人有十六象,何也?合天地而生人,合父母而生子,故有十六象也。
心居肺,胆居肝,何也?言性者必归之天,言体者必归之地,地中有天,石中有火,是以心胆象之也。心胆之倒悬,何也?草木者,地之体也,人与草木皆反生,是以倒悬也。
口目横而鼻耳纵,何也?体必交也。故动者宜纵而反横,植者宜横而反纵,皆交也。
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有四肢。是以指节可以观天,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指掌矣,可不贵之哉!
神统于心,气统于肾,形统于首。形气交而神主乎其中,三才之道也。
人之四肢各有脉也。一脉三部,一部三候,以应天数也。
四肢各一脉,四时也。一脉三部,一时三月也,一部三候,一月三旬也。四九三十六,乾之策,天之极数也。《素问》曰:“十二节,皆通乎天气。”十二节者,气应人之十二经脉,谓手足各三阴三阳也。三候者,亦沉浮中也,阴阳有太过不及也。
心藏神,肾藏精,脾藏魂,胆藏魄。
胃受物而化之,传气于肺,传血于肝,而传水谷于脬肠矣。
天圆而地方,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盖焉。然地东南下西北高,是以东南多水西北多山也。天覆地,地载天,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
天浑浑于上而不可测也,故观斗数以占天也。斗之所建,天之所行也。魁建子,杓建寅,星以寅为昼也。斗有七星,是以昼不过乎七分也。更详之。
天行所以为昼夜,日行所以为寒暑。夏浅冬深,天地之交也。左旋右行,天日之交也。
日朝在东,夕在西,随天之行也。夏在北,冬在南,随天之交也。天一周而超一星,应日之行也。春酉正,夏午正,秋卯正,冬子正,应日之交也。
日以迟为进,月以疾为退,日月一会而加半日减半日,是以为闰日也。日一大运而进六日,月一大运而退六日,是以为闰差也。
日行阳度则盈,行阴度则缩,宾主之道也。月去日则明生而迟,近日则魄生而疾,君臣之义也。
阳消则阴生,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阴盛则敌阳,故月望而东出也。天为父,日为子,故天左旋,日右行。日为夫,月为妇,故日东出月西生也。
日月相食,数之交也。日望月则月食,月掩日则日食,犹水火之相克也。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
日随天而转,月随日而行,星随月而见,故星法月,月法日,日法天。天半明半晦,日半赢半缩,月半盈半亏,星半动半静,阴阳之变化也。
天昼夜常见,日见于昼,月见于夜而半不见,星半见于夜,贵贱之等也。
月昼可见也,故为阳中之阴。星夜可见也,故为阴中之阳。
天奇而地偶,是以占天文者,观星而已,察地理者,观山水而已。观星而天体见矣,观山水而地体见矣。天体容物,地体负物。是故,体几于道也。
极南大暑,极北大寒,故南融而北结,万物之死地也。夏则日随斗而北,冬则日随斗而南,故天地交而寒暑和,寒暑和而物乃生焉。
天以刚为德,故柔者不见;地以柔为体,故刚者不生。是以震天之阴也,巽地之阳也。地阴也,有阳而阴效之,故至阴者辰也,至阳者日也,皆在乎天,而地则水火而已,是以地上皆有质之物。阴伏阳而形质生,阳伏阴而性情生,是以阳生阴,阴生阳,阳克阴,阴克阳。阳之不可伏者,不见于地,阴之不可克者,不见于天。伏阳之少者,其体必柔,是以畏阳,而为阳所用;伏阳之多者,其体必刚,是以御阳,而为阴所用。故水火动而随阳,土石静而随阴也。
阳生阴,故水先成;阴生阳,故火后成。阴阳相生也,体性相须也。是以阳去则阴竭,阴尽则阳灭。
金火相守则流,水火相得则然。从其类也。
水过寒则结,遇火则竭,从其所胜也。
阳得阴而为雨,阴得阳而为风,刚得柔而为云,柔得刚而为雷。无阴则不能为雨,无阳则不能为雷。雨柔也而属阴,阴不能独立,故待阳而后兴;雷刚也而属体,体不能自用,必待阳而后发也。
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为泰,坎离交而为既济也。乾生于子,坤生于午,坎终于寅,离终于申,以应天之时也。置乾于西北,退坤于西南,长子用事而长女代母,坎离得位,兑震为偶,以应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尽于是矣。
乾坤,天地之本;离坎,天地之用。是以《易》始于乾坤,中于离坎,终于既未济。而否泰为上经之中,咸恒当下经之首,皆言乎其用也。
坤统三女于西南,乾统三男于东北。上经起于三,下经终于四,皆交泰之义也。故易者用也:乾用九,坤用六,大衍用四十九,而潜龙勿用也。大哉!用乎。吾于此见圣人之心矣。
乾坤交而为泰,变而为杂卦也。
乾、坤、坎、离为上篇之用,兑、艮、震、巽为下篇之用也。颐、中孚、大小过为二篇之正也。
易者,一阴一阳之谓也。震兑始交也,故当朝夕之位;离坎交之极也,故当子午之位;巽艮虽不交而阴阳犹杂也,故当用中之偏位;乾坤纯阴阳也,故当不用之位。
乾坤纵而六子横,易之本也;震兑横而六卦纵,易之用也。
天之阳在南而阴在北,地之阴在南而阳在北。人之阳在上而阴在下,既交则阳下而阴上。
辰数十二,日月交会谓之辰,辰天之体也,天之体无物之气也。
天之阳在南,故日处之;地之刚在北,故山处之。所以地高西北,天高东南也。
天之神栖乎日,人之神发乎目,人之神,寤则栖心,寐则栖肾,所以象天,此昼夜之道也。
云行雨施,电发雷震,亦各从其类也。
吹喷吁呵呼,风雨云雾雷,言相类也。
万物各有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之次,亦有古今之象。
云有水火土石之异,他类亦然。
二至相去东西之度凡一百八十,南北之度凡六十。
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
四正者,乾坤坎离也。观其象无反复之变,所以为正也。
阳在阴中阳逆行,阴在阳中阴逆行,阳在阳中、阴在阴中,则皆顺行。此真至之理,按图可见矣。
草类之细入于坤。
五行之木,万物之类也,五行之金,出乎石也,故水火土石不及金木,金木生其间也。
得天气者动,得地气者静。
阳之类圆,成形则方;阴之类方,成形则圆。
木之枝干,土石之洒成,所以不易,叶花,水火之所成,故变而易也。
东赤南白西黄北黑,此正色也。验之于晓午暮夜之时,可见之矣。
冬至之子中,阴之极;春分之卯中,阳之中;夏至之午中,阳之极;秋分之酉中,阴之中。凡三百六十,中分之则一百八十。此二至二分相去之数也。
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天之道也。阳中之阳,日也,暑之道也。阳中之阴,月也,以其阳之类,故能见于昼。阴中之阳,星也,所以见于夜。阴中之阴,辰也,天壤也。
辰之于天,犹天地之体也。地有五行,天有五纬。地止有水火,天复有日月者,月为真水,日为真火,阴阳真精是生五行,所以天地之数各五。阳数独盈于七也,是故五藏之外,又有心包络命门而七者,真心离火,命门坎水,五藏生焉。精神之主,性命之根也。
干者幹之义,阳也;支者枝之义,阴也。干十而支十二,是阳数中有阴,阴数中有阳也。
鱼者水之族也,虫者风之族也。
目口凸而耳鼻窍,窍者受声嗅气,物或不能闭之,凸者视色别味,物则能闭之也。四者虽象于一,而各备其四矣。
水者火之地,火者木之气,黑者白之地,寒者暑之地。
草伏之兽,如草之茎,林栖之鸟,羽如林之叶。类使之然也。
石之花,盐消之类也。
水之物无异乎陆之物,各有寒熟之性,大较则陆为阳中之阴,而水为阴中之阳。
日月星辰共为天,水火土石共为地。耳目鼻口共为首,髓血骨肉共为身。此乃五之数也。
火生于无,水生于有。
辰至日为生,日至辰为用。盖顺为生而逆为用也。
《易》有三百八十四爻,真天文也。
鹰鹏之类食生,而鸡凫之类不传食生;虎豹之类食生,而猫犬之类食生又食谷。以类推之,从可知矣。
马牛皆阴类,细分之,则马为阳,牛为阴。
飞之类喜风而敏于飞上,走之类喜土而利于走下。阴阳之气使然也。
禽虫之卵,果谷之类也。谷之类多子,虫之类亦然。
蚕之类,今岁蛾而子,来岁则子而蚕;芜菁之类,今岁根而苗,来岁则苗而子。此皆一岁之物也。
天地之气运,北而南则治,南而北则乱,乱久则复北而南矣。天道人事皆然,推之历代,可见消长之理也。
在水者不暝;在风者瞑,走之类上睫接下;飞之类下睫接上。类使之然也。
在水而鳞鬣,飞之类也;龟獭之类,走之类也。
夫四象若错综而用之,日月,天之阴阳;水火,地之阴阳;星辰,天之刚柔;土石,地之刚柔。
飞之走,鸡凫之类是也;走之飞,龙马之属是也。
阳主舒长,阴主惨急。日入盈度,阴从于阳;日入缩度,阳从于阴。
神者,人之主。将寐在脾,熟寐在肾,将寤在肝,又言在胆,正寤在心。
天地之大寤在夏,人之神则存于心。
水之族以阴为主,阳次之;陆之类以阳为主,阴次之。故水类出水则死,风类入水则死。然有出入之类者,龟蟹鹅凫之类是也。
天地之交十之三。
天火,无体之火也;地火,有体之火也。无体因物以为体。金石之火烈于草木之火者,因物而然也。
气形盛则魂魄盛,气形衰则魂魄亦从而衰矣。
魂随气而变,魄随形而止。故形在则魄存,形化则魄散。
星为日余,辰为月余。
星之至微如尘沙者,陨而为堆阜。
藏者,天行也;府者,地行也。天地并行,则配为八卦。
八卦相错者,相交错而成六十四卦也。
夫《易》根于乾坤而生于复姤。盖刚交柔而为复,柔交刚而为姤,自兹而无穷矣。
龙能大能小,然亦有制之者,受制于阴阳之气,得时则能变化,变变则不能也。
一岁之闰,六阴六阳,三年三十六日,故三年一闰,五年六十日,故五岁再闰。
先天图,环中也。
月体本黑,受日之光而白。
水在人之身为血,土在人之身为肉。
胆与肾同阴,心与脾同阳。心主目,脾主鼻。
阳中阳,日也;阳中阴,月也;阴中阳,星也;阴中阴,辰也;柔中柔,水也;柔中刚,火也;刚中柔,土也;刚中刚,石也。
鼻之气,目见之,口之言,耳闻之。以类应也。
倚盖之说崑崙四垂而为海,推之理则不然。夫地直方而静,岂得如圆动之天乎?
动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根。
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应月者,从其类也。
震为龙,一阳动于二阴之下,震也。重渊之下有动物者,岂非龙乎?
风类,水类,大小相反。
天之阳在东南,日月居之;地之阴在西北,火石处之。
起震终艮一节,明文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错者,明交错而成六十四也。数往者顺,若顺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数往也;知来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旋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来也。夫《易》之数由逆而成矣。此一节直解图意,逆若逆知四时之谓也。
《尧典》期三百六旬有六日,夫日之余盈也,六则月之余缩也,亦六,若去日月之余十二,则有三百五十四,乃日行之数,以十二除之,则得二十九日。
《素问》,肺主皮毛,心脉,脾肉,肝筋,肾骨,上而下,外而内也。心血肾骨,交法也。交即用也。
“乾为天”之类,本象也,“为金”之类,别象也。
天地并行则藏府配四,藏天也,四府地也。
乾奇也,阳也,健也,故天下之健莫如天。坤偶也,阴也,顺也,故天下之顺莫如地,所以顺天也。震起也,一阳起也,起,动也,故天下之动莫如雷。坎陷也,一阳陷于二阴,陷,下也,故天下之下莫如水。艮止也,一阳于是而止也,故天下之止莫如山。巽入也,一阴入二阳之下,故天下之入莫如风。离丽也,一阴离于二阳,其卦错然成文而华丽也,故天下之丽莫如火,又如附丽之丽。兑说也,一阴出于外而说于物,故天下之说莫如泽。
火内暗而外明,故离阳在外,火之用,用外也;水外暗而内明,故坎阳在内,水之用,用内也。
人寓形于走类者,何也?走类者,地之长子也。
自泰至否,其间则有蛊矣,自否至泰,其间则有随矣。
天有五辰,日月星辰与天为五;地有五行,金木水火与土为五。
有温泉而无寒火,阴能从阳而阳不能从阴也。
有雷则有电,有电则有风。雨生于水,露生于土,雷生于石,电生于火。电与风同为阳之极,故有电必有风。
木之坚非雷不能震,草之柔非露不能润。
阳尊而神,尊故役物,神故藏用,是以道生天地万物而不自见也。天地万物亦取法于道矣。
阳者道之用,阴者道之体。阳用阴,阴用阳,以阳为用则尊阴,以阴为用则尊阳也。
阴几于道,故以况道也。六变而成三十六矣,八变而成六十四矣,十二变而成三百八十四矣。六六而变之,八八六十四变而成三百八十四矣。八八而变之,六八四十八变而成三百八十四矣。
无极之前阴含阳也,有象之后阳分阴也。阴为阳之母,阳为阴之父,故母孕长男而为复,父生长女而为姤。是以阳起于复而阴起于姤也。
性非体不成,体非性不生,阳以阴为体,阴以阳为体。动者性也,静者体也。在天则阳动而阴静,在地则阳静而阴动。性得体而静,体随性而动,是以阳舒而阴疾也。
阳不能独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唱。阳知其始而享其成,阴效其法而终其劳。
阳能知而阴不能知,阳能见而阴不能见也。能知能见者为有,故阳性有而阴性无也。阳有所不偏,而阴无所不偏也。阳有去,而阴常居也。无不偏而常居者为实,故阳体虚而阴体实也。
天地之本其起于中乎?是以乾坤屡变而不离乎中。
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则盛,月中则盈,故君子贵中也。
本一气也,生则为阳,消则为阴,故二者一而已矣;四者,二而已矣;六者,三而已矣;八者,四而已矣,是以言天不言地,言君不言臣,言父不言子,言夫不言妇也。然天得地而万物生,君得臣而万化行,父得子、夫得妇而家道成,故有一则有二,有二则有四,有三则有六,有四则有八。
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数。数立则象生,象生则言著彰,言著彰则意显。象、数则筌蹄也,言、意则鱼兔也。得鱼兔而忘筌蹄,则可也,舍筌蹄而求鱼兔,则未见其得也。
天变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贞《易》之变也;人行而天应之,故吉凶悔吝《易》之应也。以元亨为变,则利贞为应;以吉凶为应,则悔吝为变。元则吉,吉则利,应之亨则凶,凶则应之以贞悔则吉,吝则凶,是以变中有应,应中有变也。变中之应天道也,故元为变则亨应之,利为变则应之以贞。应中之变人事也,故变则凶,应则吉,变则吝,应则悔也。悔者吉之先,吝者凶之本,是以君子从天不从人。
元者春也,仁也,春者时之始,仁者德之长,时则未盛而德足以长人,故言德不言时。亨者夏也,礼也,夏者时之盛,礼者德之文,盛则必衰,而文不足救之,故言时不言德,故曰“大哉,乾元”,而上九有悔也。利者秋也,义也,秋者时之成,义者德之方,万物方成而获利,义者不通于利,故言时不言德也。贞者冬也,智也,冬者时之末,智者德之衰,贞则吉,不贞则凶,故言德不言时也,故曰“利贞者,性情也”。
道生天,天生地。
及其功成而身退,故子继父禅,是以乾退一位也。
象起于形,数起于质,名起于言,意起于用。天下之数出于理,违乎理则入于术。世人以数而入于术,故失于理也。
天下之事,皆以道致之,则休戚不能至矣。
天可以理尽而不可以形尽,浑天之术以形尽天,可乎?
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不精义则不能入神,则不能致用。
为治之道必通其变,不可以胶柱,犹春之时不可行冬之令也。
自然而然不得而更者,内象、内数也,他皆外象、外数也。
天道之变,王道之权也。
卦各有性有体,然皆不离乾坤之门,如万物受性于天而各为其性也。其在人则为人之性,在禽兽则为禽兽之性,在草木则为草木之性。
天以气为主,体为次;地以体为主,气为次。在天在地者亦如之。
气则养性,性则兼气,故气存则性存,性动则气动也。
天之象数则可得而推,如其神用则不可得而测也。
自然而然者,天也,唯圣人能索之。效法者人也,若时行时止,虽人亦天也。
生者性,天也;成者形,地也。
日入地中,交精之象。
体四而变六,兼神与气也。气变必六,故三百六十也。
凡事为之极,几十之七,则可止矣。盖夏至之日止于六十,兼之以晨昏,分可辨色矣。庶几乎十之七也。
图虽无文,吾终日言未尝离乎是,盖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矣。
气一而已,主之者乾也。神亦一而已,乘气而变化,出入于有无之间,无方而不测者也。
不知乾,无以知性命之理。
时然后言,乃应变而言,言不在我也。
仁配天地,谓之人,唯仁者,真可以谓之人矣。
生而成,成而生,《易》之道也。
气者神之宅也,体者气之宅也。
天六地四,天以气为质而以神为神,地以质为质而以气为神,唯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如禽兽之声,以其类而各能其一,无所不能者人也,推之他事亦莫不然。唯人得天地日月交之用,他类则不能也。人之生真可谓之贵矣,天地与其贵而不自贵,是悖天地之理,不祥莫大焉。
灯之明暗之境,日月之象也。
月者日之影也,情者性之影也。心性而胆情,性神而情鬼。
心为太极,又曰道为太极。
形可分,神不可分。
阴事大半,盖阳一而阴二也。
冬至之后为呼,夏至之后为吸,此天地一岁之呼吸也。
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发而中节者也。
不我物,则能物物。
任我则情,情则蔽,蔽则昏矣。因物则性,性则神,神则明矣。潜天潜地,不行而至,不为阴阳所摄者,神也。
天之孽十之一犹可违,人之孽十之九不可逭。
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出入有无死生者,道也。
神无所在无所不在。至人与他心通者,以其本乎一也。
道与一,神之强名也。以神为神者,至言也。
身,地也,本乎静,所以能动者,血气使之然也。
生生长类,天地成功,别生分类,圣人成能。
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
阳主辟而出,阴主翕而入。
日在子水则生,离则死,交与不交之谓也。
阴对阳为二,然阳来则生,阳去则死,天地万物生死主于阳,则归于一也。
神无方而性有质。
发于性则见于情,发于情则见于色,以类而应也。
以天地生万物,则以万物为万物,以道生天地,则天地亦万物也。
人之贵兼乎万物,自重而得其贵,所以能用万类。
凡人之善恶形于言,发于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诸心,发于虑,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独也。
气变而形化。
人之类,备乎万物之性。
人之神,则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戒哉!
人之畏鬼犹鬼之畏人,人积善而阳多,鬼亦畏之矣;积恶而阴多,鬼不畏之矣。大人者与鬼神合其吉凶,夫何畏之有?
至理之学,非至诚则不至。物理之学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强通。强通则有我,有我则失理而入于术矣。
心一而不分,则能应万物。此君子所以虚心而不动也。
圣人利物而无我。
明则有日月,幽则有鬼神。
夫圣人六经,浑然无迹,如天道焉。《春秋》录实事,而善恶形于其中矣。
中庸之法,自中者天也,自外者人也。
韵法,辟翕者律天,清浊者吕地。先闭后开者,春也;纯开者,夏也;先开后闭者,秋也;冬则闭而无声。东为春声,阳为夏声,此见作韵者亦有所至也。衔凡冬声也。
寂然不动,反本复静,坤之时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阳动于中,间不容发,复之义也。
不见动而动,妄也,动乎否之时是也;见动而动则为无妄。然所以有灾者,阳微而无应也。有应而动则为益矣。
“精气为物”,形也,“游魂为变”,神也。又曰,“精气为物”,体也,“游魂为变”,用也。
君子之学,以润身为本。其治人应物,皆余事也。
剸割者,才力也;明辨者,智识也;宽洪者,德器也。三者不可缺一。
无德者责人,怨人,易满,满则止也。
能循天理动者,造化在我也。
学不际天人,不足谓之学。
问高天下,亦若无有也。
得天理者,不独润身,亦能润心。不独润心,至于性命亦润。
历不能无差。今之学历者,但知历法,不知历理。能布算者,落下闳也,能推步者,甘石公也。落下闳但知历法,扬雄知历法又知历理。
颜子不迁怒,不贰过。迁怒、贰过皆情也,非性也。不至于性命,不足以谓之好学。
扬雄作《玄》,可谓见天地之心者。
《易》无体也,曰既有典常,则是有体也。恐遂以为有体,故曰“不可为典要”。既有典常,常也,不可为典要,变也。
庄周雄辩,数千年一人而已。如,庖丁解牛曰“踟蹰”、“四顾”,孔子观吕梁之水曰蹈水之道无私,皆至理之言也。
夫《易》者,圣人长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长也,辟之于未然;及其消也,阖之于未然。一消一长,一辟一阖,浑浑然无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大过,本末弱也。必有大德大位,然后可救。常分有可救者,有大德大位可过者也,尹、周其人也,不可惧也。有大德无大位不可过者也,孔、孟其人也,不可僭也。其位不胜德耶?
大哉,位乎!待时用之宅也。
复次剥明,治生于乱乎?姤次夬明,乱生于治乎?时哉!时哉!未有剥而不复,未有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长,子孙其昌。是以圣人贵未然之防,是谓《易》之大纲。
先天学,心法也,故图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生乎心也。
所行之路不可不宽,宽则少碍。
知《易》者,不必引用讲解,始为知《易》。孟子之言未尝及《易》,其间《易》道存焉,但人见之者鲜耳。人能用《易》,是为知《易》,孟子可谓善用《易》者也。
所谓皇帝王伯者,非独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而已,但用无为则皇也,用恩信则帝也,用公正则王也,用智力则伯也。
鬼神无形而有用,其情状可得而知也,于用则可见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叶华实颜色,皆鬼神之所为也。福善祸淫,主之者谁耶?聪明正直,有之者谁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谁耶?皆鬼神之情状也。
《易》有意象,立意皆所以明象,统下三者,有言象,不拟物而直言以明事;有像象,拟一物以明意;有数象,七日、八月、三年、十年之类是也。
《易》之数穷天地始终,或曰天地亦有始终乎?既有消长,岂无终始?天地虽大,是亦形器,乃二物也。
《易》有内象,理致是也;有外象,指定一物而不变者是也。
在人则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在物则乾道成阳,则坤道成阴。
“神无方而《易》无体”,滞于一方则不能变化,非神也。有定体则不能变通,非《易》也。《易》虽有体,体者象也,假象以见体,而本无体也。
事无大小,皆有道在其间。能安分则谓之道,不能安分谓之非道。
正音律数,行至于七而止者,以夏至之日出于寅而入于戌,亥子丑三时,则日入于地而目无所见,此三数不行者,所以比于三时也。故生物之数亦然,非数之不行也,有数而不见也。
六虚者,六位也。虚以待变动之事也。
有形则有体,有性则有情。
天主用,地主体。圣人主用,百姓主体,故“日用而不知”。
法始乎伏羲,成乎尧,革于三王,极于五伯,绝于秦。万世治乱之迹,无以逃此矣。
神者,《易》之主也,所以无方。《易》者,神之用也,所以无体。
循理则为常,理之外则为异矣。
火以性为主,体次之;水以体为主,性次之。
阳性而阴情,性神而情鬼。
《易》之首于乾坤,中于坎离,终于水火之交不交,皆至理也。
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
太极不动,性也,发则神,神则数,数则象,象则器。器之变复归于神也。
诸卦不交于乾坤者,则生于泰否。否泰,乾坤之交也。乾坤起自奇偶,奇偶生自太极。
天使我有,是之谓命。命之在我之谓性,性之在物之谓理。
朔易之阳气自北方而生,至北方而尽,谓之变易循环也。
春阳得权,故多旱;秋阴得权,故多雨。
元有,二有,生天地之始者,太极也。有万物之中各有始者,生之本也。
天地之心者,生万物之本也。天地之情者,情状也,与鬼神之情状同也。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此尽己之性,能尽物之性也。非鱼则然,天下之物则然。若庄子者,可谓善通物矣。
老子,知《易》之体者也。
无思无为者,神妙致一之地也。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
太极,道之极也;太玄,道之元也;太素,色之本也;太一,数之始也;太初,事之初也。其成功则一也。
太羹可和,玄酒可漓,则是造化亦可和可漓也。
易地而处,则无我也。
诚者,主性之具,无端无方者也。
智栽!留侯善藏其用。
《素问》、《密语》之类,于术之理可谓至也。
瞽叟杀人,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圣人虽天下之大,不能易天性之爱。
或问“显诸仁,藏诸用”,曰:若日月之照临,四时之成岁,是显仁也。其度数之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藏用也。
君子于《易》,玩象,玩数,玩辞,玩意。
兑,说也。其他皆有所害,惟朋友讲习,无说于此,故言其极者也。
中庸,非天降地出,揆物之理,度人之情,行其所安,是为得矣。
元亨利贞之德,各包吉凶悔吝之事。虽行乎德,若违于时,亦或凶矣。
汤放桀,武王伐纣,而不以为弑者,若孟子言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则援之以手,权也。故孔子既尊夷齐,亦与汤、武、夷齐仁也,汤、武义也。然唯汤、武则可,非汤、武则是篡也。
阴者阳之影,鬼者人之影也。
秦缪公有功于周,能迁善改过,为伯者之最。晋文侯世世勤王,迁平王于洛,次之。齐威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又次之。楚庄强大,又次之。宋襄公虽伯而力微,会诸侯而为楚所执,不足论也。治《春秋》者,不先定四国功过,则事无统理,不得圣人之心矣。春秋之间,有功者未见大于四国,有过者亦未见大于四国也。故四者,功之首罪之魁也。人言《春秋》非性命书,非也。至于书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犹三望,此因鲁事而贬之也。圣人何容心哉?无我故也,岂非由性命而发言也。又云,《春秋》皆教因事而褒贬,岂容人特立私意哉!又曰,《春秋》圣人之笔削,为天下之至公。不知圣人之所以为公也,如因牛伤,则知鲁之僭郊,因初献六羽,则知旧僭八佾,因新作雉门,则知旧无雉门,皆非圣人有意于其间,故曰,《春秋》尽性之书也。
《易》之为书,将以顺性命之理者,循自然也。孔子绝四从心,一以贯之,至命者也。颜子心齐履空,好学者也。子贡多积以为学,亿度以求道,不能刳心灭见,委身于理,不受命者也。《春秋》循自然之理,而不立私意,故为尽性之书也。
初与上同,然上亢不及初之进也;二与五同,然二之阴中不及五之阳中也;三与四同,然三处下卦之上,不若四之近君也。
人之贵兼乎万类,自重而得其贵,所以能用万类。
《素问》、《阴符》,七国时书也。
“显诸仁,藏诸用”,孔子善藏其用乎?
庄、荀之徒,失之辩。
伯夷义不食周粟,至饿且死,止得为仁而已。
三人行必有师焉,至于友一乡之贤,天下之贤,以天下为未足,又至于尚论,古人无以加焉。
义重则内重,利重则外重。
能医人能医之疾,不得谓之良医。医人之所不能医者,天下之良医也。能处人所不能处之事,则能为人所不能为之事也。
人患乎自满,满则止也,故禹不自满。假所以为贤,虽学亦当常若不足,不可临深以为高也。
人苟用心,必有所得,独有多寡之异,智识之有深浅也。
理穷而后知性,性尽而后知命,命知而后知至。
凡处失在得之先,则得亦不喜。若处得在失之先,则失难处矣,必至于陨获。
人必内重,内重则外轻。苟内轻必外重,好利好名无所不至。
天下言读书者不少,能读书者少。若得天理真乐,何书不可读?何坚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天时、地理、人事三者,知之不易。
资性得之天也,学问得之人也。资性由内出者也,学问由外入者也。自诚明,性也,自明诚,学也。
伯夷、柳下惠得圣人之一端,伯夷得圣人之清,柳下惠得圣人之和。孔子时清时和,时行时止,故得圣人之时。
《太玄》九日当两卦,余一卦当四日半。
用兵之道,必待人民富、仓廪实、府库充,兵强名正,天时顺地利得,然后可举。
《老子》五千言,大抵皆明物理。
今有人登两台,两台皆等,则不见其高,一台高,然后知其卑下者也。一国、一家、一身皆同,能处一身则能处一家,能处一家则能处一国,能处一国则能处天下。心为身本,家为国本,国为天下本。心能运身,苟心所不欲,身能行乎?
人之精神贵藏而用之,苟衒于外则鲜有不败者,如利刃,物来则剸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乎物,则刃与物俱伤矣。
言发于真诚,则心不劳而逸,人久而信之。作伪任数,一时或可以欺人,持久必败。
人贵有德,小人有才者有之矣,才不可恃,德不可无。
天地日月悠久而已,故人当存乎远,不可见其迩。
君子处畎亩,则行畎亩之事,居庙堂则行庙堂之事,故无入不自得。
智数或能施于一朝,盖有时而穷。惟至诚与天地同久。
天地无则至诚可息,苟天地不能无,则至诚亦不息也。
室中造车,天下可行,轨辙合故也。苟顺义理合人情,日月所照皆可行也。
敛天下之善则广矣,自用则小。
汉儒以反经合道为权,得一端者也。权所以平物之轻重,圣人行权,酌其轻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执中无权者,犹为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权,非王通莫能及此,故权在一身,则有一身之权,在一乡,则有一乡之权,以至于天下,则有天下之权。用虽不同,其权一也。
夫弓故有强弱,然一弓二人张之,则有力者以为弓弱,无力者以为弓强。故有力者不以己之力有余,而以为弓弱,无力者不以己之力不足,而以为弓强。何不思之甚也?一弓非有强弱也,二人之力强弱不同也。今有食一杯在前,二人大馁而见之,若相逊则均得食也,相夺则争,非徒争之而已,或不得其食矣。此二者皆人之情也,知之者鲜,知此,则天下之事皆如是也。
先天学主乎诚,至诚可以通神明,不诚则不可以得道。
良药不可以离手,善言不可以离口。
事必量力,量力故能久。
学以人事为大,今之经典,古之人事也。
《春秋》三传之外,陆淳、啖助可以兼治。
季札之才近伯夷,叔向、子产、晏子之才相等埒,管仲用智数,晚识物理,大抵才力过人也。
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书也。功过不相掩,圣人先褒其功,后贬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录之,不可不恕也。新作两观,新者贬之也,诛其旧无也;初献六羽,初者褒之也,以其旧僭八佾也。
某人受《春秋》于尹师鲁,师鲁受于穆伯长,某人后复攻伯长曰:《春秋》无褒,皆是贬也。田述古曰:孙复亦云《春秋》有贬而无褒。曰:《春秋》礼法废,君臣乱,其间有能为小善者,安得不进之也?况五霸实有功于天下,且五霸固不及于王,不犹愈于僭窃乎,安得不与之也?治《春秋》者不辩名实,不定五霸之功过,则未可言治《春秋》。先定五霸之功过而治《春秋》,则大意立,若事事求之,则无绪矣。
凡人为学,失于自主张太过。
平王名虽王,实不及一国之诸侯,齐、晋虽侯,而实僭王。皆《春秋》之名实也。子贡欲去告朔之餼羊,羊,名也,礼,实也。名存而实亡,犹愈于名实俱亡,苟存其名,安知后世无王者作?是以有所待也。
《春秋》为君弱臣强而作,故谓之名分之书。
圣人之难在不失仁义忠信而成事业,何如,则可在于绝四。
有马者借人乘之,舍己从人也。
或问:才难何谓也?曰:临大事然后见才之难也。曰:何独言才?曰:才者,天之良质也,学者所以成其才也。曰:古人有不由学问而能立功业者,何必曰学?曰:周勃、霍光能成大事,唯其无学,故未尽善也。人而无学,则不能烛理,不能烛理,则固执而不通。
人有出人之才必有刚,克中刚则足以立事业处患难,若用于他反邪恶,故孔子以申枨为“焉得刚”,既有恶心,必无刚也。
君子喻于义,贤人也,小人喻于利而已。义利兼忘者,唯圣人能之。君子畏义而有所不为,小人直不畏耳。圣人则动不逾矩,何义之畏乎!
颜子不贰过,孔子曰:“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是也,是一而不再也。韩愈以为将发于心而使能绝去,是过与颜子也。过与是为私意焉,能至于道哉?或曰:与善不亦愈于与恶乎?曰:圣人则不如是,私心过与善恶同矣。
为学养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诚,则无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当以直求之。若用智数,由径以求之,是屈天地而徇人欲也,不亦难乎?
事无巨细,皆有天人之理。修身,人也;遇不遇,天也。得失不动心,所以顺天也;行险侥幸是逆天也。求之者,人也;得之与否,天也。得失不动心,所以顺天也;强取必得,是逆天理也。逆天理者,患祸必至。
鲁之两观,郊天大秂,皆非礼也。诸侯苟有四时之秂,以为常祭可也,至于五年大秂不可为也。
仲弓可使南面,可使从政也。
谁能出不由户?户,道也,未有不由道而能济者也。不由户者,锁穴隙之类是也。
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虽多闻,必择善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识,别也,虽多见,必有以别之。
落下闳改颛帝历为太初历,子云准太初而作《太玄》,凡八十一卦,九分共二卦,凡一五隔一四,细分之,则四分半当一卦,气起于中心,故首中卦。
元亨利贞,变易不常,天道之变也;吉凶悔吝,变易不定,人道之应也。
“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无声无形,不可得而见者也,故假道路之道而为名。人之有行必由道,一阴一阳,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也。
“显诸仁”者,天地生万物之功,则人可得而见也;所以造万物,则人不可得而见,是“藏诸用”也。
十干,天也;十二支,地也。支干配天地之用也。
《易》始于三皇,《书》始于二帝,《诗》始于三王,《春秋》始于五霸。
自乾坤至坎离,以天道也;自咸恒至既济、未济,以人事也。
人谋,人也;鬼谋,天也。天人同谋而皆可,则事成而吉也。
变从时而使天下之事,不失礼之大经;变从时而顺天下之理,不失义之大权者,君子之道也。
五星之说,自甘石公始也。
人智强则物智弱。
庄子著《盗跖》篇,所以明至恶,虽至圣亦莫能化。盖上智与下遇不移故也。
鲁国之儒一人者,谓孔子也。
天下之事始于过重犹卒于轻,始于过厚犹卒于薄。况始以轻、始以薄者乎?故鲜失之重多失之轻,鲜失之厚多失之薄。是以君子不患过乎重,常患过乎轻,不患过乎厚,常患过乎薄也。
庄子《齐物》,未免乎较量,较量则争,争则不平,不平则不和。无思无为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谓一以贯之。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
当仁不让于师者,进仁之道也。
秦穆公伐郑而有悔过,自誓之言此非止霸之事。几于王道而能悔,则无失矣。此圣人所以录于书末也。
刘絢问无为,对曰: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此所谓无为也。
文中子曰:易乐者必多哀;轻施者必好夺。或曰:天下皆争利弃义,吾独若之何?子曰:舍其所争,取其所弃,不亦君子乎?若此之类,理义之言也。心迹之判久矣,若此之类,造化之言也。
庄子气豪,若吕梁之事,言之至者也。盗跖言事之无可奈何者,虽圣人亦莫如之何。渔父言事之不可强者,虽圣人亦不可强。此言有为无为之理,顺理则无为,强则有为也。
金须百炼然后精,人亦如此。
佛氏弃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岂自然之理哉?
志于道者,统而言之,志者潜心之谓也,德者得于己,有形故有据,德主于仁,故曰依。
庄子曰: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此君子思不出其位,素位而行之意也。
晋狐射姑杀阳处父,《春秋》书晋杀其大夫阳处父,上漏言也。君不密,则失臣,故书国杀。
人得中和之气则刚柔均,阳多则偏刚,阴多则偏柔。
作《易》者其知盗乎?圣人知天下万物之理而一以贯之。
以尊临卑曰临,以上观下曰观。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合而言之则一,分而言之则二;合而言之则二,分而言之则四。始于有意,成于有我,有意然后有必,必生于意,有固然后有我,我生于固,意有心必先期,固不化我有已也。
记问之学,未足以为事业。
学在不止,故王通没身而已。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后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圣而何?教而后善,非贤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谓也;不善也者,凶之谓也。
吉也者,目不观非礼之色,耳不听非礼之声,口不道非礼之言,足不践非理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义不取,亲贤如就芝兰,避恶如畏蛇蝎。或曰不谓之吉人,则吾不信也。凶也者,语言诡谲,动止阴险,好利饰非,贪滛乐祸,疾良善如雠隙,犯刑宪如饮食,小则殒身灭性,大则覆宗絶嗣。或曰不谓之凶人,则吾不信也。
传有之曰:吉人为善,惟日不足;凶人为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为吉人乎?欲为凶人乎?
《皇极经世书》邵子全书·渔樵问对
渔者垂钓于伊水之上。樵者过之,弛担息肩,坐于磐石之上,百问于渔者。
曰:“鱼可钩取乎?”
曰:“然。”
曰:“钩非饵可乎?”
曰:“否。”
曰:“非钩也,饵也。鱼利食而见害,人利鱼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异也。敢问何故?”
渔者曰:“子樵者也,与吾异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为子试言之。彼之利,犹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犹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鱼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鱼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鱼终日得食为利,又安知鱼终日不得食为害?如是,则食之害也重,而钩之害也轻。子知吾终日得鱼为利,又安知吾终日不得鱼不为害也?如是,则吾之害也重,鱼之害也轻。以鱼之一身,当人之食,是鱼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当鱼之一食,则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钓乎大江大海,则无易地之患焉?鱼利乎水,人利乎陆,水与陆异,其利一也;鱼害乎饵,人害乎财,饵与财异,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子之言,体也,独不知用尔。
樵者又问曰:“鱼可生食乎?”
曰:“烹之可也。”
曰:“必吾薪济子之鱼乎?”
曰:“然。”
曰:“吾知有用乎子矣。”
曰:“然则子知子之薪,能济吾之鱼,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济吾之鱼也。薪之能济鱼久矣,不待子而后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则子之薪虽积丘山,独且奈何哉?”
樵者曰:“愿闻其方。”
曰:“火生于动,水生于静。动静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也;草木,体也。用生于利,体生于害。利害见乎情,体用隐乎性。一性一情,圣人能成子之薪。犹吾之鱼,微火则皆为腐臭败坏,而无所用矣,又安能养人七尺之躯哉?”
樵者曰:“火之功大于薪,固已知之矣。敢问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后传?”
曰:“薪,火之体也。火,薪之用也。火无体,待薪然后为体;薪无用,待火然后为用。是故凡有体之物,皆可焚之矣。”
曰:“水有体乎?”
曰:“然。”
曰:“火能焚水乎?”
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随,故灭。水之体,能随而不能迎,故热,是故有温泉而无寒火,相息之谓也。”
曰:“火之道生于用,亦有体乎?”
曰:“火以用为本,以体为末,故动。水以体为本,以用为末,故静。是火亦有体,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济又能相息,非独水火则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尔。”
樵者曰:“用可得闻乎?”
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传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数取者,物之体也。用也者,妙万物为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传。”
曰:“不可以言传,则子恶得而知之乎?”
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言传,非独吾不能传之以言,圣人亦不能传之以言也。”
曰:“圣人既不能传之以言,则六经非言也耶?”
曰:“时然后言,何言之有?”
樵者赞曰:“天地之道备于人,万物之道备于身,众妙之道备于神,天下之能事毕矣,又何思何虑!吾而今而后,知事心践形之为大。不及子之门,则几至于殆矣。”
乃析薪烹鱼而食之饫,而论《易》。
渔者与樵者游于伊水之上。渔者叹曰:“熙熙乎万物之多,而未始有杂.吾知游乎天地之间,万物皆可以无心而致之矣。非子则孰与归焉?”
樵者曰:“敢问无心致天地万物之方?”
渔者曰:“无心者,无意之谓也。无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后定能物物。”
曰:“何谓我,何谓物?”
曰:‘以我徇物,则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则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万物也,何天地之有焉?万物亦天地也,何万物之有焉?万物亦我也,何万物之有焉?我亦万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则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况于人乎?况于物乎?“
樵者问渔者曰:“天何依?”
曰:“依乎地。”
曰:“地何附?”
曰:“附乎天。”
曰:“然则天地何依何附?”
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气。其形也有涯,其气也无涯。有无之相生,形气之相息。终则有始,终始之间,其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为本,以体为末;地以体为本,以用为末。利用出人之谓神,名体有无之谓圣。唯神与圣,能参乎天地者也。小人则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实丧之患也。夫名也者,实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于不足,得丧于有余。害生于有余,实丧于不足。此理之常也。养身者必以利,贪夫则以身殉得,故有害生焉。立身必以名,众人则以身殉名,故有实丧焉。窃人之财谓之盗,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败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贿之与赃,一物而两名者,利与害故也。窃人之美谓之徼,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败露,唯恐其多矣。夫誉与毁,一事而两名者,名与实故也。凡言朝者,萃名之地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争处乎其间,虽一日九迁,一货十倍,何害生实霄之有耶?是知争也者取利之端也;让也者趋名之本也。利至则害生,名兴则实霄。利至名兴,而无害生实霄之患,唯有德者能之。天依地,地会天,岂相远哉!
渔者谓樵者曰:“天下将治,则人必尚行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言也。尚行,则笃实之风行焉;尚言,则诡谲之风行焉。天下将治,则人必尚义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利也。尚义,则廉让之风行焉;尚利,则攘夺之风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于义也,尚言者必入于利也。义利之相去,一何如是之远耶?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干身,不若尽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闻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见之,尽之干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聪明犹不可欺,况神之聪明乎?是知无愧于口,不若无愧于身,无愧于身,不若无愧于心。无口过易,无身过难,无身过易,无心过难。既无心过,何难之有!吁,安得无心过之人,与之语心哉!”
渔者谓樵者曰:“子知观天地万物之道乎?”
樵者曰:“未也。愿闻其方。”
渔者曰:“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谓之理者,穷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性者,尽之而后可知也;所似谓之命者,至之而后可知也。此三知也,天下之真知也,虽圣人无以过之也。而过之者,非所以谓之圣人也。夫鉴之所以能为明者,谓其能不隐万物之形也。虽然鉴之能不隐万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万物之形也。虽然水之能一万物之形,又未若圣人之能一万物情也。圣人之所以我一万物之情者,谓其圣人之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又安有我于其间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与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为己之目,其目无所不观矣。用天下之耳为己之耳,其耳无所不听矣。用天下之口为己之口,其口无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为己之心,其心无所不某矣。天下之观,其于见也,不亦广乎!天下之听,其于闻也,不亦远乎!天下之言,其于论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谋,其于乐也,不亦大乎!夫其见至广,其闻至远,其论至高,其乐至大,能为至广、至远、至高、至大之事,而中无一为焉,岂不谓至神至圣者乎?非唯一时之天下谓之至神奎圣者乎,而千万世之天下谓之至神至圣者乎?非唯一时之天下渭之至神至圣者乎,而千万世之天下谓之至神圣者乎?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樵者问渔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鱼?”
曰:“吾以六物具而得鱼。”
曰:“六物具也,岂由天乎?”
曰:“具六物而得鱼者,人也。具六物而所以得鱼者,非人也。”
樵者未达,请问其方。
渔者曰:“六物者,竿也,纶也.浮也,沉也,钩也,饵也。一不具,则鱼不可得。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鱼者,非人也。六物具而不得鱼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鱼者也。是知具六物者,人也。得鱼与不得鱼,天也。六物不具而不得鱼者,非天也,人也。”
樵者曰:“人有祷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祷而求耶?求之而可得耶?敢问其所以。”
曰:“语善恶者,人也;福祸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祸淫,鬼神岂能违天乎?自作之咎,固难逃已;天之灾,禳之奚益?修德积善,君子常分。安有余事于其间哉!”
樵者曰:“有为善而遇祸,有为福而获福者,何也?”
渔者曰:“有幸与不幸也。幸不幸,命也;当不当,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逃乎?”
曰:“何谓分?何谓命?”
曰:“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当祸,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祸,非分也,有命也;当福,分也,非命也。”
渔者谓樵者曰:“人之所谓亲,莫如父子也;人之所渭疏,莫如路人也。利言在心,则父子过路人远矣。父子之道,天生也。利害犹或夺之,况非天必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则过之,固无相害之心焉,无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则路人与父子,又奚择焉?路人之能相交以义,又何况父子之亲乎!夫义者,让之本也;利者,争之端也。 让则有仁,争则有害,仁与害,何相去之远也!尧、舜亦人也。桀、纣亦人也,人与人同而仁与害尔,仁因义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义,则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岂若路人之相逢,一目而交袂于中逵者哉!”
樵者谓渔者曰:“吾尝负薪矣,举百斤而无伤吾之身,加十斤则遂伤吾之身.敢问何故?”
渔者曰:“樵则吾不知之矣。以吾之事观之,则易地皆然。吾尝钓而得大鱼,与吾交战。欲弃之,则不能舍,欲取之,则未能胜。终日而后获,几有没溺之患矣。非直有身伤之患耶?鱼与薪则二也,其贪而为伤则一也。百斤,力分之内者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虽一毫犹且为害,而况十斤乎!吾之贪鱼亦何以异子之贪薪乎!”
樵者叹曰:“吾而今而后,知量力而动者智矣哉!”
樵者谓渔者曰:“子可谓知《易》之道矣。吾也问:《易》有太极,太极何物也?”
曰:“无为之本也。”
曰:“太极生两仪,两仪,天地之谓乎?”
曰:“两仪,天地之祖也,非止为天地而已也。太极分而为二,先得一为一,后得一为二。一二谓两仪。”
曰:“两仪生四象,四象何物也?”
曰:“四象谓阴阳刚柔。有阴阳然后可以生天,有刚柔然后可以生地。立功之本,于斯为极。”
曰:“四象生八卦,八卦何谓也?”
曰:“谓乾、坤、离、坎、兑、良、震、巽之谓也。迭相盛衰终始于其间矣。因而重之,则六十四卦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始备矣。”
樵者问渔者曰:“复何以见天地之心乎?”
曰:“先阳已尽,后阳始生,则天地始生之际。中则当日月始周之际,末则当星辰始终之际。万物死生,寒署代谢,昼夜变迁,非此无以见之。当天地穷极之所必变,变则通,通则久,故《象》言’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顺天故也。”
樵者谓渔者曰:“无妄,灾也。敢问何故?”
曰:“则欺他,得之必有祸,斯有妄也.顺天而动,有祸及者,非祸也,灾也。犹农有思丰而不勤稼稿者,其荒也,不亦祸乎?农有勤稼穑而复败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灾乎?故《象》言’先
王以茂对时育万物‘,贵不妄也。”
樵者问曰:“姤,何也?”
曰:“姤,遇也。柔遇刚也,与夬正反。夬始逼壮,姤始遇壮,阴始遇阳,故称姤焉。观其姤,天地之心,亦可见矣。圣人以德化及此,网有不昌。故《象》言’后以施命诰四方‘,履霜之慎,其在此也。”
渔者谓樵者曰:“春为阳始,夏为阳极,秋为阴始,冬为阴极。阳则温,阳极则热;阴始则凉,阴极则寒。温则生物,热则长物,凉则收物,寒则杀物。皆一气别而为四焉。其生万物也亦然。”
樵者问渔者曰:“人之所以能灵于万物者,何以知其然耶?”
渔者对曰:“人之所以能灵于万物者,谓其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声色气味者,万物之体也。目耳口鼻者,万人之用也。体无定用,惟变是用。用无定体,惟化是体。体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备矣。然则天亦物也,圣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万物之物,有亿物之物,有兆物之物。为兆物之物,岂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万人之人,有亿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为兆人之人,岂非圣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谓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谓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谓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谓也。以一至物而当一至人,则非圣人而何?人谓之不圣,则吾不信也。何哉?谓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物观万物,一世观万世者焉。又谓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功,身代天事者焉。又谓其能以上顺天时,下应地理,中徇物情,通尽人事者焉。又谓其能以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今古,表里时事者焉。噫,圣人者,非世世而效圣焉。吾不得而目见之也。虽然吾不得而目见之,察其心,观其迹,探其体,潜其用,虽亿万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别有天地万物,异乎此天地万物。‘则吾不得而知之也。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圣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谓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谓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恶得而言之乎?以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谓妄知也。以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谓妄言也。吾又安能从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渔者谓樵者曰:“仲尼有言曰:殷因于夏礼,所捐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捐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则何止于百世而已哉!亿千万世,皆可得而知之也。人皆知仲尼之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为仲尼则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为仲尼,则舍天地将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则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则舍动静将奚之焉?夫一动一静者,天地至妙者欤?夫一动一静之间者,天地人至妙至妙者欤?是知仲尼之所以能尽三才之道者,谓其行无辙迹也。故有言曰:’予欲无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其此之谓与?”
渔者谓樵者曰:“大哉!权之与变乎?非圣人无以尽之。变然后知天地之消长,权然后知天下之轻重。消长,时也;轻重,事也。时有否泰,事有损益。圣人不知随时否泰之道,奚由知变之所为乎?圣人不知随时损益之道,奚由知权之所为乎?运消长者,变也;处轻重者,权也。是知权之与变,圣人之一道耳。”
樵者问渔者曰:“人谓死而有知,有诸?”
曰:“有之。”
曰:“何以知其然?”
曰:“以人知之。”
曰:“何者谓之人?”
曰:“目耳鼻口心胆脾肾之气全,谓之人。心之灵曰神,胆之灵曰魄,脾之灵曰魂,肾之灵曰精。心之神发乎目,则谓之视;肾之精发乎耳,则谓之听;脾之魂发乎鼻,则谓之臭;胆之魄发乎口,则谓之言。八者具备,然后谓之人。夫人也者,天地万物之秀气也。然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类也。若全得人类,则谓之曰全人之人。夫全类者,天地万物之中气也,谓之日全德之人
也。全德之人者,人之人者也。夫人之人者,仁人之谓也。唯全人,然后能当之。人之生也,谓其气行,人之死也,谓其形返。气行则神魂交,形返则精魄存。神行于天,精魄返于地。行于天,则渭之曰阳行;返于地,则谓之曰阴返。阳行则昼见而夜伏者也?阴返则夜见而昼伏者也。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阳者阴之形也,阴者阳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谓鬼无形而无知者,吾不信也。”
樵者问渔者曰:“小人可绝乎?”
曰:“不可。君子禀阳正气而生,小人禀阴邪气而生。无阴则阳不成,无小人则君子亦不成,唯以盛衰乎其间也。阳六分,则阴四分;阴六分,则阳四分。阳阴相半,则各五分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时有盛衰也。治世则君子六分。君子六分,则小人四分,小人固不能胜君子矣。乱世则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谓各安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妇不妇,谓各失其分也。此则由世治世乱使之然也。君子常行胜言,小人常言胜行。故世治则笃实之士多,世乱则缘饰之士从。笃实鲜不成事,缘饰鲜不败事。成多国兴,败多国亡。家亦由是而兴亡也。夫兴家与兴国之人,与亡国亡家之人,相去一何远哉!”
樵者问渔者曰:“人所谓才者,有利焉,有害焉者,何也?”
渔者曰:“才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
曰:“不正,则安得谓之才?”
曰:“人所不能而能之,安得不谓之才?圣人所以异乎才之难者,谓其能成天下之事而归之正者寡也。若不能归之以正,才则才矣,难乎语其仁也。譬犹药疗疾也,毒药亦有时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则速已,不已则杀人矣。平药则常常日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驱重疾而无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谓良药也。《易》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则小人亦有时而用之。时平治定,用之则否。《诗》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
樵者谓渔者曰:“国家之兴亡,与夫才之邪正,则固得闻命矣。然则何不择其人而用之?”
渔者曰:“择臣者,君也;择君者,臣也。贤愚各从其类而为。奈何有尧舜之君,必有尧舜之臣;有桀纣之君,而必有桀纣之臣。尧舜之臣,生乎桀纣之世,桀纣之臣,生于尧舜之世,必非其所用也。虽欲为祸为福,其能行乎?夫上之所好,下必好之。其若影响,岂待驱率百然耶?上好义,则下必好义,而不义者远矣;上好利,下必好利,而不利者远矣。好利者众,则天下日削矣;好义者众,则天下日盛矣。日盛则昌,日削则亡。盛之与削,昌之与亡,岂其远乎?在上之所好耳。夫治世何尝无小人,乱世何尝无君子,不用则善恶何由而行也。”
樵者曰:“善人常寡,而不善人常众;;治世常少,乱世常多,何以知其然耶?”
曰:“观之于物,何物不然?譬诸五谷,耘之而不苗者有矣。蓬莠不耘而犹生,耘之而求其尽也,亦未如之何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道,有自来矣。君子见善则嘉之,见不善则远之;小人见善则疾之,见不善则嘉之。善恶各人其类也。君子见善则就之,见不善则违之;小人见善则违之,见不善则就之。君子见义则迁,见利则止;小人见义则止,见利则迁。迁义则利人,迁利则害人。利人与害人,相去一何远耶?家与国一也,其兴也,君子常多而小人常鲜;其亡也小人常多而君子常鲜。君子多而去之者,小人也;小人多而去之者,君子也。君子好生,小人好杀。好生则世治,好杀则世乱。君子好义,小人好利。治世则好义, 乱世则好利。其理一也。”
钓者谈已,樵者曰:“吾闻古有伏羲,今日如睹其面焉。”拜而谢之,及旦而去。
整理者按:
程颢为邵雍所作《墓志铭》中有“有《问》有《观》”一句,《观》指《观物篇》,《问》则似指《渔樵问对》。又《朱子语类》卷一百有“康节《渔樵问对》、《无名公序》是一两篇书,次第将来刊成一集”之语录。还有“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依气。所以重复而言不出此意者,惟恐人于天地之外别寻去处故也”、“康节说得那’天依地,地附天,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气‘底几句,向尝以此数语附于《通书》之后”二条语录,卷一百十五又记:“旧尝见《渔樵问对》,问:’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天依形,地附气。其形远有涯,其气也无涯。‘意者当时所言,不过如此。某尝欲注此语于《遗事》之下,钦夫不许。细思无有出是说者。因问:’向得此书,而或者以为非康节所著。‘先生曰:’其间尽有好处,非康节不能著也。‘”。则知朱熹当时以《渔樵问对》为邵子书。《宋史·邵雍传》亦谓邵雍有《渔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