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记住本站永久中文域名:风水业协会.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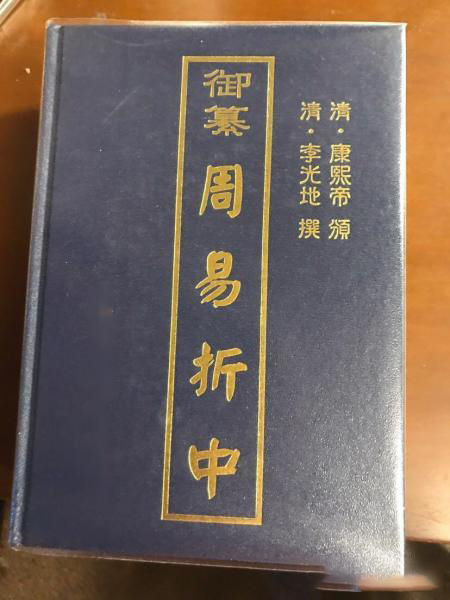
孔氏颖达曰:言圣人作《易》,与天地相准,谓准拟天地,则乾健以法天,坤顺以法地之类是也。
苏氏轼曰:“准”,符合也。“弥”,周浃也。“纶”,经纬也。所以与“天地准”者,以能“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说”,“鬼神之情状”也。
王氏宗传曰:天地之道,即下文所谓“一阴一阳”是也。是道也,其在天地,则为“幽明”,寓于始终,则为“生死”,见于物变,则为“鬼神”。
《朱子语类》云:凡天地间之物,无非天地之道,故《易》能“弥纶天地之道”。“弥”如卦弥之弥,糊合使无缝罅。“纶”如纶丝之纶,自有条理,言虽是弥得外面无缝罅,而中则事事物物,各有条理,“弥”而非“纶”,而空疏无物,“纶”而非“弥”,则判然不相干。此二字,见得圣人下字甚密也。
胡氏炳文曰:此“易”字,指《易》书而言,书之中具有天地之道,本自与天地相等,故于天地之道,“弥”之则是合万为一,浑然无欠,“纶”之则一实万分,粲然有伦。
案 此下三节,朱子分为“穷理”“尽性”“至命”者极确,然须知非有《易》以后,圣人方用《易》以穷之尽之至之,《易》是圣人穷理尽性至命之书,圣人全体易理,故言易穷理尽性至命,即是言圣人也。 “《易》与天地准”,“与天地相似”,“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此三句当为三节冠首,第二第三节不言《易》者,蒙第一节文义。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本义 此穷理之事。“以”者,圣人以《易》之书也。“易”者,阴阳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阴阳之变,天地之道也。“天文”则有昼夜上下,“地理”则有南北高深,“原”者,推之于前。“反”者,要之于后,阴精阳气,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为变,“鬼”之归也。
集说 韩氏伯曰:“幽明”者,有形无形之象,“死生”者,始终之数也。
苏氏轼曰:“鬼”常与体魄俱,故谓之“物”,“神”无适而不可,故谓之“变”,精气为魄,魄为鬼,志气为魂,魂为神。
《朱子语类》:问:“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曰:人未死,如何知得死之说,只是原其始之理,将后面摺转来看,便见得,以此之有,知彼之无。
又云:魄为鬼,魂为神,《礼记》有孔子答宰我问,正说此理甚详。宰我曰:吾闻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谓。子曰: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注,气,谓嘘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聪明为魄。《杂书》云:魂,人阳神也。魄,人阴神也。亦可取。
陈氏淳曰:人生天地间,得天地之气以为体,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则要其终而知所以死,古人谓得正而毙,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只缘受得许多道理,须知得尽得便自无愧,到死时亦只是这二五之气,听其自消化而已,所谓安死顺生,与天地同其变化,这个便是与造化为徒。
又曰:阴阳二气会在吾身之中为鬼神,以寤寐言,则寤属阳,寐属阴,以语默言,则语属阳,默属阴,及动静进退行止等,分属皆有阴阳,凡属阳者皆为魂为神,凡属阴者皆为魄为鬼。
真氏德秀曰:人之生,精与气合,精属阴,气属阳,精则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之聪。气亢乎体,凡人心之能思虑知识,身之能举动勇决,此之谓魂,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
胡氏炳文曰:《易》不曰阳阴而曰阴阳,此所谓“幽明”“死生”“鬼神”,即阴阳之谓也,即天地而“知幽明之故”,即始终而“知死生之说”,即散聚而“知鬼神之情状”,皆“穷理”之事也。
林氏希元曰:“幽明之故”,“死生之说”,“鬼神之情状”,其理皆在于《易》。故圣人用《易》以穷之也,然亦要见得为圣人穷理尽性之书尔,非圣人真个即《易》而后“穷理尽性”也。
郑氏维岳曰:原人之所以始,全而生之,即反其所以终,全而归之。
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
本义 此圣人尽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万物者,天也。道济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则知而不过矣。“旁行”者,行权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乐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无忧而其知益深,随处皆安而无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济物之心,而仁益笃。盖仁者爱之理,爱者仁之用,故其相为表里如此。
集说 韩氏伯曰:德合天地,故曰相似。
《朱子语类》云:“与天地相似故不违”,下数句是说与“天地相似”之事。
胡氏炳文曰:上文言“易与天地准”,此言“与天地相似”。“似”即”准”也,知似天,仁似地,有周物之知,而实诸济物之仁,则其知不过,有行权之知,而本诸守正之仁,则其知不流,至于“乐天知命”,而知之迹已泯,安土敦仁,而仁之心益著。此其知仁所以“与天地相似而不违”,尽性之事也。
俞氏琰曰:与天地相似者,《易》似天地,天地似《易》,彼此相似也。
案 知周万物,义之精也,然所知者皆济天下之道而不过,义合于仁也。旁行泛应,仁之熟也,然所行者皆合中正之则而不流,仁合于义也,乐玩天理,故所知者益深。达乎命而不忧,安于所处,故所行者益笃。根于性而能爱,所谓乐天之志,忧世之诚,并行不悖者,乃仁义合德之至也,若以旁行为知亦可,但恐于行字稍碍: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本义 此圣人至命之事也。“范”,如铸金之有模范。“围”,匡郭也。天地之化无穷,而圣人为之“范围”,不使过于中道,所谓“裁成”者也。“通”,犹兼也。“昼夜”,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谓,如此然后可见至神之妙,无有方所,《易》之变化,无有形体也。
此第四章,言《易》道之大,圣人用之如此。
集说 韩氏伯曰:“方”“体”者,皆系于形器者也,神则“阴阳不测”,易则“惟变所适”,不可以一方一体明。
孔氏颖达曰;“范”,谓模范。“围”,谓周围。言圣人所为所作,模范周围天地之化。
义曰:凡无方无体,各有二义,一者神则不见其处所云为,是“无方”也;二则周游运动,不常在一处,亦是“无方”也。“无体”者,一是自然而变,而不知变之所由,是无形体也;二则随变而往,无定在一体,亦是“无体”也。
邵子曰:“神”者,《易》之主也,所以“无方”。“易”者,神之用也,所以“无体”。
《朱子语类》云:“通乎昼夜之道而知”,“通”字,只是兼乎昼夜之道而知其所以然。
又云:“神无方而《易》无体”,“神”便是在阴底又忽然在阳,在阳底又忽然在阴,“易”便是或为阳,或为阴,交错代换,而不可以形体拘也。
蔡氏清曰:“神无方,易无体”,独系之至命一条,至命从穷理尽性上来,乃穷理尽性之极致,非穷理尽性之外,它有所谓至命也,故独系之至命,而自足以该乎“穷理尽性”。
林氏希元曰:“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只是通知昼夜之道,盖幽朋死生鬼神,其理相为循环,昼夜之道也,圣人通知昼夜,亦只是上文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说”,“知 又曰:天地之化,万物之生,昼夜之循环,皆有个神易,“易”则模写乎此理者也,故在易亦有神易。
姜氏宝曰:“昼夜之道”,乃幽明死生鬼神之所以然,圣人通知之而有以深彻乎其蕴,又不但知有其故,知有其说,知有其情状而已也。
江氏盈科曰:上说道济天下敦仁能爱,此则万物尽属其曲成,一上说知幽明死生鬼神,此则昼夜尽属其通知。
案 准是准则之,相似是与之合德,“范围”则造化在其规模之内,盖一节深一节也,“万物”者天地之化之迹也。“曲成”者,能尽其性,而物我联为一体也;“昼夜”者,天地之化之机也;“通”“知”者,洞见原本,而隐显贯为一条也。“易”者化之运用,“神”者化之主宰。天地之化,其主宰不可以方所求,其运用不可以形体拘,易之道能“范围”之,则所谓穷神知化者也,而神化在易矣。
一阴一阳之谓道。
本义 阴阳迭运者,气也,其理则所谓道。
集说 邵子曰:道无声无形,不可得而见者也,故假道路之道而为名。人之有行,必由乎道。一阴一阳,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者也。
程子曰:离了阴阳,便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
《朱子语类》云:理则一而已,其形者则谓之器,其不形者则谓之道。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盖阴阳亦器也。而所以阴阳者道也,是以一阴一阳,往来不息,而圣人指是以明道之全体也。
案 一阴一阳,兼对立与迭运二义,对立者,天地日月之类是也,即前章所谓“刚柔”也,迭运者,寒暑往来之类是也,即前章所谓“变化”也。
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本义 道具于阴而行乎阳。“继”,言其发也。“善”,谓化育之功,阳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谓物之所受,言物生则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阴之事也。周子程子之书,言之备矣。
集说 周子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务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杨氏时曰:“继之者善”,无间也,“成之者性”,无亏也。
《朱子语类》云:造化所以发育万物者,为“继之者善”,各正其性命者,为“成之者性”。
又云:“继”是接续不息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
又云:这个理在天地间时,只是善。无有不善者,生物得来,方始名曰性,只是这个理,在天则曰命,在人则曰性,性便是善。
问“成之者性”。曰:性如宝珠,气质如水。水有清有污,故珠或全见,或半见,或不见。
项氏安世曰:道之所生,无不善者,元也,万物之所同出也,善之所成,各一其性者,贞也,万物之所各正也,“成之者性”,犹孟子言人之性犬之性牛之性。
熊氏良辅曰:天道流行,发育万物。善之继也,“元者善之长”,善即元也。人物得所禀受者,性之成也,率性之谓道,则性即道也。
潘氏士藻曰:善者性之原,性者善之实,善性皆天理,中间虽有刚柔善恶巾偏之不同,而天命之本然无不同。
案 圣人用“继”字极精确,不可忽过此“继”字,犹人子所谓继体,所谓继志。
盖人者,天地之子也。天地之理,全付于人而人受之,犹《孝经》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者是也,但谓之付,则主于天地而言,谓之受则主于人而言,唯谓之继,则见得天人承接之意,而付与受两义皆在其中矣。天付于人而人受之,其理既无不善,则人之所以为性者,亦岂有不善哉,故孟子之道性善者本此也。然是理既具于人物之身,则其根原虽无不善,而其末流区以别矣,如下文所云仁知百姓者,皆局于所受之偏而不能完其所付之全,故程朱之言气质者,亦本此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唯《系传》此语,为言性与天道之至,后之论性者,折中子夫子,则可以息诸子之棼棼矣。
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本义 “仁”阳“知”阴,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随其所见而目为全体也。“日用不知”,则莫不饮食,鲜能知味者,又其每下者也。然亦莫不有是道焉。或曰:上章以知属乎天,仁属乎地,与此不同,何也?曰:彼以清浊言,此以动静言。
集说 韩氏伯曰:君子体道以为用,仁知则滞于所见,百姓则“日用而不知”,体斯道者,不亦鲜矣乎。
程子曰:道者,一阴一阳也,动静无端,阴阳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动静相因而成变化,顺继此道则为善也。成之在人,则谓之性也,在众人则不能识,随其所知,故仁者谓之仁,知者谓之知,百姓则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人鲜克知也。
王氏宗传曰:仁者知者,鲜克全之,百姓之愚,鲜克知之,此岂在我之善有所不足,在我之性有所不同与!非也,盖在限量使然尔。君子之道,乌得而不鲜与,“君子”者,具仁知之成名,得道之大全也。
《朱子语类》云:万物各具是性,但气禀不同。各以其性之所近者窥之,故仁者只 胡氏炳文曰:在造物者,方发而赋于物,其理无有不善,在人物者,各具是理以有生,则谓之性。其发者,是天命之性,其具者,天命之性已不能不丽于气质矣。“仁者”“知者”“百姓”,指气质而言也,上章说圣人之知仁,知与仁合而为一,此说知者仁者,仁与知分而为二。
保氏八曰:仁者见其有安土敦仁之理,则止谓之为仁,知者见其有知周天下之理,则止谓之为知,是局于一偏矣。百姓终日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知者鲜也。
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
本义 “显”,自内而外也。“仁”,谓造化之功,德之发也。“藏”,自外而内也。“用”,谓机缄之妙,业之本也。程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
集说 孔氏颖达曰:“显诸仁”者,显见仁功,衣被万物。“藏诸用”者,潜藏功用。
不使物知。
王氏凯冲曰:万物皆成,仁功著也,不见所为,藏诸用也。
程子曰:运行之迹,生育之功,“显诸仁”也;神妙无方,变化无迹,“藏诸用”也。
天地不与圣人同忧,天地不宰,圣人有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
《朱子语类》云:“显渚仁”,德之所以盛,“藏诸用”,业之所山成。譬如一树一根,生许多枝叶花实,此是“显诸仁”处,及至结实,一核成一个种子,此是“藏诸用”处,生生不已,所谓日新也,万物无不具此理,所谓富有也。
又云:恻隐羞恶辞逊是非,只是这个恻隐,随事发见,及至成那事时,一事各成一仁,此便是“藏诸用”。其发见时,在这道理中发去,及至成这事时,又只是这个道理,一事既各成一道理,此便是业,业是事之已成处,事未成时不得谓之业。
吴氏澄曰:“仁”者,生物之元,由春生而为夏长之亨,此仁显见而发达于外,长物之所显者,生物之仁也,故曰“显诸仁”。“用”者,收物之利,由秋收而为冬藏之贞,此用藏伏而归复于内,团物之所藏者,收物之用也,故曰“藏诸用”。二气运行于四时之间,鼓动万物而生长收闭之,天地无心而造化自然,非如圣人之于民,有所忧而治之教之也。仁之显而生长者,为德之盛,用之藏而收闭者,为业之大,其显者流行不息,其藏者充塞无间,此所谓易简之善,极其至者,故赞之曰“至矣哉”。
胡氏炳文曰:在圣人者则曰仁与知,在造化者则曰仁与用。
俞氏琰曰:仁本藏于内者也,“显诸仁”,则自内而外,如春夏之发生,所以显秋冬所藏之仁也。“用”本显于外者也,“藏诸用”,则自外而内,如秋冬之收成,所以藏春夏所显之用也。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本义 张子曰:富有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无穷。
生生之谓易。
本义 阴生阳,阳生阴,其变无穷,理与书皆然也。
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
本义 “效”,呈也。“法”,谓造化之详密而可见者。
集说 蔡氏渊曰:乾主气,故曰“成象”,坤主形,故曰“效法”。
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
本义 “占”,筮也。事之未定者,属乎阳也。“事”,行事也。占之已决者,属乎阴也,“极数知来”,所以通事之变,张忠定公言公事有阴阳,意盖如此。
集说 愈氏琰曰:或言通变,或言变通,同与。曰:“穷则变,变则通”,《易》也。
“通其变,使民不倦”,圣人之用《易》也。
张氏振渊曰:“成象”二条,本“生生之谓易”来,举乾坤,见天地间无物,而非阴阳之生生;举占事,见日用间无事,而非阴阳之生生。
谷氏家杰曰:生生谓易,论其理也。有理即有数,阴阳消息,易数也。推极之可以知来,占之义也,通数之变,亦《易》变也。变“不与时偕极”,通之“即成天下之事”。
徐氏在汉曰:一阴一阳,无时而不生生,是之谓《易》。成此一阴一阳生生之象,是之谓“乾”,效此一阴一阳生生之法,是之谓“坤”,极一阴一阳生生之数而知来,是“之谓占”,通一阴一阳生生之变,是“之谓事”。
阴阳不测之谓神。
本义 张子曰:两在故“不测”。
此第五章,言道之体用不外乎阴阳,而其所以然者,则未尝倚于阴阳也。
集说 《朱子语类》:问:“阴阳不测之谓神”,便是妙用处。曰:便是包括许多道理,横渠说得极好,一故神,横渠亲注云,“两在故不测”,只是这一物,却周行事物之间,如所谓阴阳屈信,往来上下,以至行乎什百千万之中,无非这一个物事,所谓“两在故不测”。
邱氏富国曰:上章言“易无体”,此言“生生之谓易”,唯其“生生”,所以“无体”。
上章言“神无方”,此言“阴阳不测之谓神”,唯其“不测”,所以“无方”。言《易》而以乾坤继之,“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也”。
粱氏寅曰:阴阳非神也,阴阳之不测者神也,一阴一阳,变化不穷,果孰使之然哉, 蔡氏清曰:合一不测为神,不合不谓之一,不一不为两在,不两在不为不测,合者,两者之合也,神化非二物也,故曰“一物两体也”。
总论 程氏敬承曰:此章承上章说来,上言“弥纶天地之道”,此则直指“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言神无方、易无体,此则直指阴阳之生生谓易,阴阳不测谓神。
案 程氏以此为申说上章极是,然只举其首尾天地之道,及神易两端而已,须知继善成性,见仁见知,即是申说“与天地相似”一节意。显仁藏用,盛德大业,即是申说“范围天地之化”一节意。见仁见知之偏,所以见知仁合德者之全也,显为昼藏为夜,鼓万物而无忧,所以见通知昼夜曲成万物以作《易》者之有忧患也。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近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
本义 “不御”,言无尽,“静而正”,言即物而理存。“备”,言无所不有。
案 远近是横说,天地之间是直说。理极于无外,故曰远。性具于一身,故曰近。
命者,自天而人,彻上彻下,故曰天地之间不御者,所谓弥纶也。静正者,所谓相似也,备者,所谓范围也。
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
本义 乾坤各有动静,于其四德见之,静体而动用,静别而动交也。乾一而实,故以质言而曰“大”,坤二而虚,故以量言而曰“广”,盖天之形虽包于地之外,而其气常行乎地之中也,《易》之所以广大者以此。
集说 孔氏颖达曰:若气不发动,则静而专一,故云“其静也专”,若其运转,则四时不忒,寒暑无差,刚而得正,故云“其动也直”。以其动静如此,故能“大生焉”。
闭藏翕敛,故“其静也翕”,动则开生万物,故“其动也辟”。以其如此,故能“广生”于物焉。
程子曰:乾阳也,不动则不刚。“其静也专,其动也直”不专一则不能直遂。坤阴也,不静则不柔,“其静也翕,其动也辟”,不翕聚,则不能发散。
《朱子语类》云:天是一个浑沦底物,虽包乎地之外,而气则进出乎地之中。地虽一块物在天之中,其中实虚,容得天之气迸上来。“大生”,是浑沦无所不包,“广生”,是广阔,能容受得那天之气,“专”“直”则只是一物直去,“翕”“辞”则是两个,翕则翕,辟则辟,此奇偶之形也。
又云;乾静专动直而“大生”,坤静翕动辟而“广生”,这说阴阳体性如此,卦画也髣髴似恁地,乾画奇,便见得“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坤画偶,便见得“其静也翕”,“其动也辟”。
胡氏炳文曰:乾唯健,故一以施;坤唯顺,故两而承;“静”“专”,一者之存;“动”“直”,一者之达;“静”“翕”,两者之合;“动”“辟”,两者之分;一之达,所以行乎坤之两。故以质言而曰“大”,两之分,所以承乎乾之一,故以量言而曰“广”。
林氏希元曰:此推《易》之所以广大也。乾坤,万物之父母也,乾坤各有性气,皆有动静,乾之性气,其静也专一而不它,唯其专一而不它,则其动也直遂而无屈挠。唯直遂而无屈挠,则其性气之发,四方八表,无一不到,而规模极其大矣,故曰“大生焉”。
坤之性气,其静也翕合而不泄,唯其翕合而不泄,则其动也开辟而无闭拒,唯其开辟而无闭拒,则乾气到处,坤皆有以承受之,而度量极其广矣,故曰“广生焉”。乾坤即天地也,“大生”“广生”,皆就乾坤说。《易》书之广大,则模写乎此,不可以本文广大作《易》书。
案 此节是承上节“广矣大矣”,而推言天地之所以广大者。一由于易简,故下节遂言《易》书“广大配天地”,而结归于易简也。静专动直,是豪无私曲,形容易字最尽,静翕动辟,是豪无作为,形容简字最尽,易在直处见,坦白而无艰险之谓也,其本则从专中来,简在辟处见,开通而无阻塞之谓也,其本则从翕中来。
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本义 易之广大变通,与其所言阴阳之说,易简之德,配之天道人事则如此。
此第六章。
集说 孔氏颖达曰:初章,《易》为“贤人之德”,简为“贤人之业”,今总云“至德”者,对则德业别,散则业由德而来,俱为德也。
吴氏澄曰:《易》书广大之中有变通焉,有阴阳之义焉,亦犹天地之有四时日月也,四时日月即天地,犹易之六子即乾坤也,易之广大变通阴阳,皆易简之善,为之主宰。
而天地之至德,亦此易简之善而已,是易书易简之善,配乎天地之至德也。
案 此上三章,申“变化者,进退之象”一节之义,首言《易》“能弥纶天地之道”,而所谓幽明死生神鬼之理,即进退昼夜之机也,次言《易》与天地相似,而所谓仁义之性,即三极之道也。又言《易》“能范围天地之化”,盖以其赞天地之化育,而又知天地之化育,则三极之道,进退昼夜之机,一以贯之矣,“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则神化之事备,此《易》之蕴也,既乃一一申明之。所谓天地之道者,一阴一阳之谓也;所谓天地之性者,一仁一智之谓也;所谓天地之化者,一显一藏以鼓万物之谓也;所谓《易》“无体”者,生生之谓也,著于乾坤,形乎占事者皆是;而所谓“神无方”者,则阴阳不测之谓也,终乃总而极赞之,谓《易》之穷理也。远不御,其尽性也,静而正,其至命也,于天地之间备矣。又推原其根于易简之理,“静专”“动直”,易也;“静翕”“动辟”,简也。易简之理,具于三极之道,而行乎进退昼夜之间。故《易》者,统而言之,“广大配天地”也。析而言之,“变化者,进退之象”,“变通配四时”也,“刚柔者,昼夜之象”,“阴阳之义配日月”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易简之善配至德也”。
系辞上传(下)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
本义 “十翼”皆夫子所作,不应自著“子曰”字,疑皆后人所加也,穷理则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则礼卑如地而业广,此其取类,又以清浊言也。
集说 韩氏伯曰:极知之崇,象天高而统物,备礼之用。象地广而载物也。
孔氏颖达曰:言《易》道至极,圣人用之以增崇其德,广大其业。
《朱子语类》云:知识贵乎高明,践履贵乎著实,知既高明,须放低著实作去。
又云:“知祟”者,德之所以祟;“礼卑”者,业之所以广,盖礼才有些不到处,便有所欠阙,业便不广矣,唯极卑无所欠阙,所以广。
又云:“礼卑”是卑顺之意,卑便广,地卑便广,高则狭了,人若只拣取高底作便狭,两脚踏地作方得。
吴氏澄曰:“崇德”者,立心之易,而所得日进日新也。“广业”者,行事之简,而所就日充日富也。德之进而新,由所知之崇,高明如天业之充而富,由所履之卑,平实如地。
张氏振渊曰:“知”,即德之虚明炯于中者。“礼”,即业之矩矱成于外者。天运于万物之上,而圣心之知,亦独超于万象之表,故曰“崇效天”。地包细微,不遗一物,而圣人之礼,亦不忽于纤悉细微之际,故曰“卑法地”。
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本义 天地设位而变化行,犹知礼存性而道义出也。成性,本成之性也。存存,谓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
此第七章集说 《朱子语类》云:识见高于上,所行实于下,中间便生生而不穷,故说《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俞氏琰曰:人之性,浑然天成,盖无有不善者,更加以涵养功夫,存之又存,则无所往而非道,无所往而非义矣。
林氏希元曰:此承上文“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而言,意谓“天地设位”,则阴阳变化,“而《易》行乎其中矣”,圣人知礼至于效天法地,则本成之性,存存不已,而道义从此出,故曰“道义之门。”盖道义之得于心者,日新月盛,则德于是乎祟矣,道义之见于事者,日积月累,则业于是乎广矣,此《易》所以为圣人之崇德广业,而《易》书所以为至也。
吴氏曰慎曰:道义之出不穷,犹《易》之生生不已也,然未有不存存而能生生者。
案 “门”字不可专以出说,须知兼出入两意,“知崇”于内,则万里由此生,是道所从出之门也,“礼卑”于外,则万行由此成,是义所从入之门也。若以四德配,则知属冬,礼属夏,道即仁也,属春,义属秋,仁主出而发用,然非一心虚明,万理毕照,则无以为发用之源,义主入而收敛,然非百行万善,具足完满,亦无以为收敛之地矣,此造化动静互根,显诸仁藏诸用之妙,其在人则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
总论 项氏安世曰:此章言圣人体《易》于身也,知穷万理之原,则乾之始万物也,礼循万理之则,则坤之成万物也,道者义之体,智之所知也,义者道之用,礼之所行也。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本义 赜,杂乱也。象,卦之象,如说卦所列者。
巢说《朱子语类》云:赜,杂乱也,古无此字,只是“啧”字,今从臣,亦是口之义,与《左传》啧有繁言之啧同,是口里说话多杂乱底意思,所以下文说不可恶,先儒多以“赜”为至妙之意,若如此说,何从谓之不可恶,“赜”只是一个杂乱冗闹底意思。
吴氏澄曰:不以“彖”对爻言,而以“象”对爻言者,文王未系彖辞之先,重卦之名谓之“象”,“象”先于“彖”,言“象”则“彖”在其中。
胡氏炳文曰:拟者象之未成,象者拟之已定,姑以乾坤二卦言之,未画则拟阴阳之形容,于是为奇偶之画,画则象也,已画又取象天地、首腹、牛马以至于为金、为玉、为釜、为布之类,皆象也。
郑氏维嶽曰:拟之在心,象之在画。
张氏振渊曰:拟诸形容者,拟之阴阳也,在未画卦之先。“象其物宜”,正画卦之事,“拟”是拟其所象,“象”是象其所拟,物而曰“宜”,不独肖其形,兼欲尽其理。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本义 会,谓理之所聚而不可遗处,通,谓理之可行而无所碍处,如庖丁解牛,会则其族,而通则其虚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会”以物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会”是众理聚处,虽觉得有许多难易窒碍,必于其中却得个通底道理,乃可行尔,且如事理间,若不于会处理会,却只见得一偏,便如何行得通,须是于会处都理会,其间却自有个通处,这“礼”字又说得阔,凡事物之常理皆是。
又云:会而不通,便窒塞而不可行,通而不会,便不知许多曲直错杂处。
吴氏澄曰:会通,谓大中至正之理,非一偏一曲有所拘碍者也,圣人见天下不一之动,而观其极善之理以行其事,见理精审,则行事允当也,以处事之法为辞,系于各爻之下,使筮而遇此爻者,如此处事则吉,不如此处事则凶也。
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
本义 恶,犹厌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杂乱处人易得厌恶,然都是道理中合有底事,自合理会,故“不可恶”。动亦是合有底,上面各自有道理故自“不可乱”。
吴氏澄曰:六十四卦之义,所以章显天下至幽之义而名言宜称,人所易知,则自不至厌恶其赜矣,三百八十四爻之辞,所以该载天下至多之事,而处决精当,人所易从,则自不至棼乱其动矣。
潘氏士藻曰:有至一者存,所以“不可恶”,有至常者存,所以“不可乱”。
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
本义 观象玩辞,观变玩占,而法行之,此下七爻,则其例也。
集说 王氏宗传曰:“拟之而后言”,“拟”是象而言也,“拟”是而言,则言有物矣。
“议之而后动”,“议”是爻而动也,“议”是而动,则动唯厥时矣。
《朱子语类》云:“拟议”只是裁度,自家言动,使合此理,变易以从道之意。
胡氏炳文曰:圣人之于象,拟之而后成,学《易》者如之何不拟之而后言,圣人之于爻,必观会通以行典礼,学《易》者如之何不议之而后动,前言变化,《易》之变化也,此言成其变化,学《易》者之变化也。
呜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平?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本义 释《中孚》,九二爻义。
集说 韩氏伯曰:鹤鸣于阴,气同则和,出言户庭,千里或应,出言犹然,况其大 蔡氏渊曰:居其室,即在阴之义。出其言,即鸣之义。千里之外应之,即和之之义。
感应者心也,言者心之声,行者心之迹,言行乃感应之枢机也。
保氏八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枢动而户开,机动而矢发,小则招荣辱,大则动天地,皆此唱而彼和,感应之最捷也。
汪氏砥之曰:居室照在阴看《中孚》者,诚积于中,在阴居室,正当慎独以修言行而进于诚也。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本义 释《同人》九五爻义。言君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后实无间,断金如兰,言物莫能问,而其言有味也。
集说 韩氏伯曰:君子出处默语,不违其中,其迹虽异,道同则应。
耿氏南仲曰:“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者,物或间之,而其迹异也,迹虽异而心同,故物不得而终间焉。“其利断金”,则其间除矣,间除则合,故又曰“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其相好之无斁也。
《朱子语类》云:同心之利,虽金石之坚,亦被他断决将去,断是断作两段。
俞氏琰曰:出处语默,即“先号咷后笑”之义。“二人同心”,断金臭兰,即相遇之义。
钱氏志立曰:断金,言其心志之坚,物不得间也。如兰,言其气味之一,物不能杂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本义 释《大过》初六爻义。
集说 程氏敬承曰:天下事成于慎而败于忽,况当《大过》时,时事艰难,慎心不到,便有所失,故有取于慎之至,言宁过于畏慎也。
案 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此句须对卦义看,卦取“栋”为义者,任重者也。茅之视栋,为物薄矣,然栋虽任重而犹有桡之患,故当大事者,每忧其倾坠也。若藉茅于地,则虽重物而不忧于倾坠也。岂非物薄而用可重乎,自古图大事必以小心为基,故《大过》之时义虽用刚,而以初爻之柔为基者此也。
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本义 释《谦》九三爻义。:“德言盛,礼言恭。”言德欲其盛,礼欲其恭也。
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本义 释《乾》上九爻义,当属《文言》,此盖重出。
集说 孔氏颖达曰:上既以谦德保位,此明无谦则有悔,故引《乾》之上九,“亢龙有悔。”证骄亢不谦也。
王氏宗传曰:知圣人深予乎《谦》之九三,则知圣人深戒乎《乾》之上九,何也,亢者谦之反也,九三致恭存位,上九则“贵而无位”,九三“万民服”,上九则“高而无民”,九三“能以功下人”,上九则“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此九三所以谦而有终,上九所以亢而有悔也。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本义 释《节》初九爻义。
集说 蔡氏渊曰:不言则是非不形,人之招祸,唯言为甚,故言所当节也,密于言语,即“不出户庭”之义。
吴氏澄曰:此爻辞所象慎动之节,而夫子以发言之辞释之。程子曰:在人所节,唯言与行,节于言则行可知,言当在先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本义 释《解》六三爻艾。
此第八章,言卦爻之用。
集说 孔氏颖达曰:此结上不密失身之事,事若不密,人则乘此机危而害之,犹若财之不密,盗则乘此机危而窃之。
胡氏瑗曰:小人居君子之位,不唯盗之所夺,抑亦为盗之侵伐矣。盖在上之人,不能选贤任能,遂使小人乘时得势而至于高位,非小人之然也。
陈氏琛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则处非其据,而“盗思夺之矣”,且小人在位,则慢上暴下,人所不堪,而“盗思伐之矣”。
赵氏光大曰:强取曰“夺”,执辞曰“伐”。
案 “慢”、“暴”如陈氏说亦通,然以“慢”字对下文慢藏观之,则当为上亵慢其 总论 谷氏家杰曰:此章重拟议成变化句,前章以存存用《易》,尊德性也,此章以拟议用《易》,道问学也。
案 此上二章中“君子所居而安者”一节之义,得《易》理于心之谓德,成《易》理于事之谓业,圣人犹然,况学者乎,是故不可以至赜而恶也,不可以至动而乱也,拟之于至赜之中,得圣人所谓“拟诸形容”者,则沛然无疑而可以言矣,议之于至动之际,得圣人所谓观其会通者,则确然不《易》而可以动矣,知礼成性,不待拟议而变化出焉者,圣人之事也,精义利用,拟议以成其变化者,学者之功也,《中孚》以下七爻举例言之。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本义 此简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从之,此言天地之数,阳奇阴偶,即所谓河图者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就此章而言之,则中五为衍母,次十为衍子,次一二三四为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为四象之数,二老位于西北,二少位于东南,其数则各以其类交错于外也。
集说 郭氏雍曰:天数五,地数五者,此也,《汉志》言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故或谓天一至五为五行生数,地六至地十为五行成数,虽有此五行之说,而于易无所见,故五行之说,出于历数之学,非《易》之道也。
《朱子语类》云:自“大衍之数五十”,至“再扐而后挂”,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与祐神矣”为一节,是论大衍之数,自“天一至地十”,却连“天数五至而行鬼神也”为一节,是论河图五十五之数,今其文间断差错,不相连接,舛误甚明。
项氏安世曰:姚大老云,天一地二至天九地十,班固《律历志》及卫元嵩《元包运蓍篇》,皆在天数五地数五之上。
吴氏澄曰:案《汉书律历志》,引此章“天一地二至行鬼神也”,六十四字相连,则是班固时此简犹未错也。
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本义 此简本在大衍之后,今按宜在此,天数五者,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数五者,二四六八十皆偶也。相得,谓一与二,三与四,五与六,七与八,九与十,各以奇偶为类而自相得。有合,谓一与六,二与七,三与八,四与九,五与十,皆两相合。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积也。三十者,五偶之积也。变化,谓一变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变成之,三变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变成之,五变生土,而十化成之。
集说 孔氏颖达曰:言此阳奇阴偶之数,成就其变化,而宣行鬼神之用。
程子曰:数只是气,变化鬼神亦只是气,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变化鬼神,皆不越于其间。
龚氏焕曰:“五位相得”之说,当从孔氏,盖既谓之“五位相得”,则是指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东,四九居西,五十居中而言,且一二三四之相得不见其用,不若孔之的也。
案 龚氏之意,谓“相得”者,言四方相次,如一三七九,二四六八是也。“有合”昔,言四方相交,如一六二七,三八四九是也,此说极合图意。盖“相得”者,是二气之迭运,四时之顺播,所以成变化者此也。“有合”者,是动静之互根,阴阳之互藏,所以行鬼神者此也,然成变化行鬼神,不直言于相得有合之后,必重叙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者,盖非重叙细数,则无以见相得者之自少而多,自微而盛,有合者之多少相间,微盛相错,而往来积渐之迹,屈伸交互之机,有所未明者矣。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
本义 “大衍之数五十”,盖以河图中宫,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则又止用四十有九,盖皆出于理势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损益也。两,谓天地也。挂,悬其一于左手小指之间也。三,三才也。揲,间而数之也。奇,所揲四数之余也。扐,勒于左手中三指之两间也。闰,积月之余日而成月者也。五岁之间,再积日而再成月,故五岁之中,凡有再闰,然后别起积分,如一挂之后,左右各一揲而一扐,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扐,然后别起一挂也。
集说 韩氏伯曰:王弼曰:演天地之数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也。
孔氏颖达曰:分而为二以象两者,五十之内去其一,余有四十九,合同未分。今以四十九分而为二,以象两仪也。挂一以象三者,就两仪之间,于天数之中,分挂其一以象三才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时者,分揲其蓍,皆以四四为数,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者,谓四揲之余,归此残奇于扐而成数,以象天道归残聚余分而成闰也。五岁再闰者,凡前闰后闰,相去大略三十二月,在五岁之中,故五岁再闰。
张氏浚曰:“归奇于扐以象闰”,何也?大衍用四十有九,老阳余数十有三,老阴余数二十有五,合之为三十有八,少阳余数二十有一,少阴余数十有七,合之亦为三十有八,乘以六爻之位,则二百二十有八也,凡术于筭者,率以二百二十八为求闰之法,盖自然之纪如此。
朱子《蓍卦考误》曰;五十之内去其一,但用四十九策,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
以四十九策分置左右两手,左手象天,右手象地,是象两仪也。挂,犹悬也,于右手之中,取其一策,悬于左手小指之间,所以象人而配天地,是象三才。揲,数之也。谓先 又答郭雍曰:过揲之数,虽先得之,然其数众而繁,归奇之数,虽后得之,然其数寡而约,纪数之法,以约御繁,不以众制寡,故先儒旧说,专以多少决阴阳之老少,而过揲之数,亦冥会焉,初非有异说也。然七八九六所以为阴阳之老少者,其说又本于图书。定于四象,其归奇之数,亦因揲而得之耳。大抵河图洛书者,七八九六之祖也。四象之形体次第者,其父也。归奇之奇偶方园者,其子也。过揲而以四乘之者,其孙也。
今自归奇以上,皆弃不录,而独以过揲四乘之数为说,恐或未究象数之本原也。
吴氏澄曰:衍毋之一,数之所起,故大衍五十之数,虚其一而不用,所用者四十有九,其数七七,盖以一一为体,七七为用也。
胡氏炳文曰:历法再闰之后,又从积分而起,则筮法再扐之后,又必从挂一而起也。
附录 虞氏翻曰:奇此挂一策,扐所揲之余,不一则二,不三则四也。取奇以归扐,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故“归奇于扐以象闰也”。
张子曰:奇,所挂之一也。劫,左右手四揲之余也。再扐后挂者,每成一爻而后挂也。谓第二第三揲不挂也。闰尝不及三岁而再至,故曰五岁再闰,此归奇必俟于再扐者,象闰之中间再岁也。
郭氏忠孝曰:奇者,所挂之一也。扐者,左右两揲之余也。得左右两揲之余寘于前,以奇归之也。归奇,象闰也。五岁再闰,非以再扐象再闰也,盖闰之后有再岁,故归奇之后亦有再扐也。再扐而后复挂,挂而复归,则五岁再闰之义矣。自唐初以来,以奇为扐,故揲法多误,至横渠先生而后奇扐复分。
又曰:扐者数之余也,如《礼》言祭用数之仂是也,或谓指间为扐者非,《系辞》言“归奇于扐”,则奇与扐为二事也。又言“再扐而后挂”,则扐与奇亦二事也,由是知《正义》误以奇为扐,又误以左右手揲为再扐,如曰最末之余,归之合于扐挂之一处,其说自相抵捂,莫知所从,唯当从横渠先生之说为正。
又曰:《系辞》以两扐一挂为三变而成一爻,是有三岁一闰之象,《正义》以每一揲左右两手之余即为再扐,是一变之中,再扐一挂皆具,则一岁一闰之象也。凡揲蓍第一变必挂一者,谓不挂一则无变,所余皆得五也,唯挂一则所余非五则九,故能变,第二第三揲虽不挂,亦有四八之变,盖不必挂也,故圣人必再扐后挂者以此。
案 郭雍本其先人郭忠孝之说,以为蓍说,引张子之言为据,朱子与之往复辨论,今附录于后以备参考,大约孔《疏》、《本义》,则以左右揲余为奇,而即以再扐象再闰,张子郭氏则以先挂一者为奇,而归之于扐以象闰,其说谓唯初变挂一而后二变不挂,故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
本义 凡此策数,生于四象,盖河图四面。太阳居一而连九,少阴居二而连八,少阳居三而连七,太阴居四而连六,揲蓍之法,则通计三变之余,去其初挂之一,凡四为奇,凡八为偶,奇圆围三,偶方围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积而数之,则为六七八九,而第三变揲数策数,亦皆符会,盖余三奇则九,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为居一之太阳。余二奇一偶则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为居二之少阴。二偶一奇则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为居三之少阳。三偶则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为居四之老阴,是其变化往来进退离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为也,少阴退而未极乎虚,少阳进而末极乎盈,故此独以老阳老阴计乾坤六爻之策数,余可推而知也。期,周一岁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特举成数而概言之耳。
集说 孔氏颖达曰:乾之少阳。一爻有二十八策,六爻则有一百六十八策,此经据老阳之策也。若坤之少阴,一爻有三十二,六爻则有一百九十二,此经据坤之老阴,故百四十有四也。
《朱子语类》云:大凡易数皆六十,三十六对二十四,三十二对二十八,皆六十也,十甲十二辰,亦凑到六十也,钟律五声十二律,亦积为六十也,以此知天地之数,皆至六十为节。
又答程大昌曰:《大传》专以六爻乘二老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实六爻之为阴阳者,老少错余,其积而为乾者,未必皆老阳,其积而为坤者,未必皆老阴,其为六子诸卦者,或阳或阴,亦互有老少焉。
胡氏炳文曰:前则挂扐象月之闰,此则过揲之数象岁之周,盖揲之以四,已合四时之象,故总过揲之数,又合四时成岁之象也。
案 《大传》不言乾之挂扐若干,坤之挂扐若干,而但言乾之策坤之策,则以策数定七八九六者似是。
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本义 二篇,谓上下经。凡阳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阴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得此数。
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
集说 陆氏绩曰:分而为二以象两,一营也。挂一以象三,二营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时,三营也。归奇于扐以象闰,四营也。
孔氏颖达曰:营,谓经营,谓四度经营蓍策,乃成易之一变也,每一爻有三变,初一揲不五则九,是一变也;第二揲不四则八,是二变也;第三揲亦不四则八,是三变也。
若三者俱多为老阴,谓初得九,第二第三俱得八也。若三者俱少为老阳,谓初得五,第二第三俱得四也。若两少一多为少阴,谓初与二三之间,或有四有五而有八,或有二四面有一九也,其两多一少为少阳,谓三揲之间,或有一九一八而有一四,或为二八而有一五也。三变既毕,乃定一爻,六爻则十有八变乃始成卦也。
《朱子语类》云:这处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
八卦而小成。
本义 谓九变而成三画,得内卦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八卦而小成者,象天地雷风日月山泽,于大象略尽,是易道“小成”。
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本义 谓已成六爻,而视其爻之变与不变,以为动静,则一卦可变而为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六卦也。
案 六十四卦变为四千九十六卦之法,即如八卦变为六十四卦之法,画上加画,至于四千九十六卦,则六画者积十二画矣。如引寸以为尺,引尺以为丈,故曰“引而伸之”。
圣人设六十四卦,又系以辞,则事类大略已尽,今又就其变之所适而加一卦焉,彼此相触,或相因以相生,或相反以相成,其变无穷,则义类亦无穷,故曰“触类而长之”。
如此则足以该事变而周民用,故曰“天下之能事毕。”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祐神矣。
本义 道因辞显,行以数神。酬酢,谓应对。祐神,谓助神化之功。
集说 韩氏伯曰:可以应对万物之求,助成神化之功也。酬酢,犹应对。
张子曰:示人吉凶,其道显,阴阳不测,其德神,显故可与酬酢,神故可与祐神。
又曰:显道者,危使平,易使倾,惧以终始,其要无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动,冥会于万化之感,而莫知为之者也。受命如响,故可与酬酢。曲尽鬼谋,故可与祐神,显道神德行,此言蓍龟之德也。
项氏安世曰:天道虽幽,可阐之以示乎人,人事虽显,可推之以合乎天,明可以酬酢事物之官,幽可以赞出鬼神之命。
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而今不可考耳,其可推者,《启蒙》备言之。
集说 韩氏伯曰:变化之道,不为而自然,故知变化之道者,则知神之所为。
张子曰:唯神为能变化,以其一天下之动也,人能知变化之道,其必知神之所为也。
苏氏轼曰:神之所为不可知,现变化而知之矣,变化之间,神无不在。
董氏铢曰:阳化为阴,阴变为阳者,变化也。所以变化者,道也。道者本然之妙,变化者所乘之机,故阴变阳化,而道无不在,两在故不测,故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龚氏焕曰:此所谓“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即承上文所谓“成变化而行鬼神”为言也,盖河图之数体也,故曰“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大衍之数用也,故曰“知变化之遭,其知神之所为”,成变化所以行鬼神,故知变化之道,则知神之所为。
变化者神之所为,而神不离于变化,知道者必能知之。
陆氏振奇曰:神妙变化而为言,故知鬼神之行,即在成变化处。
谷氏家杰曰:神之所为,是因图数之神,以赞衍法之神,见其亦如天地之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指蓍法之变化为神,非总承数法而并赞其神也。
案 此节是承蓍卦而赞之,龚氏谷氏之论为得,盖菁卦之法,乃所以写变化之机,而阴阳合一不测之妙,行乎其间也,下文象变辞占,即是变化之道,至精至变以极于至神,即是神之所为。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本义 四者皆变化之道,神之所为者也。
集说 虞氏翻曰:以言者尚其辞,圣人之情见于辞,系辞焉,以尽言也,动则玩其占,故尚其占者也。
孔氏颖达曰:策是筮之所用,并言卜者,卜虽龟之见兆,亦有阴阳五行变动之状。
程子曰:言所以述理,以言者尚其辞,谓以言求理者,则存意于辞也;以动者尚其变,动则变也;顺变而动,乃合道也;制器作事,当体乎象,卜筮吉凶,当考乎占。
《朱子语类》:问: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用龟亦使易占否?曰:不用,则是文势如此。
胡氏炳文曰:辞以明变象之理,占以断变象之应,故四者之目,以辞与占始终焉。
蔡氏清曰:尚辞与尚占有别。后章云:“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于此可见尚辞尚占之别矣。
又曰:言动制器卜筮,不必俱以筮易言,“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亦可用易也;“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亦可用易也。
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本义 此尚辞尚占之事,言人以蓍问《易》,求其卦爻之辞,而以之发言处事,则易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如响之应声,以决其来来之吉凶也。以言,与“以言者尚其辞”之以言义同。命,则将筮而告蓍之语,《冠礼》筮日宰自右赞命是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问焉而以言,以上下文推之,以言却是命筮之词,古人亦大段重这命筮之词。
吴氏澄曰:有为,谓作内事。有行,谓作外事。
蔡氏清曰:行之于身是有为,措之事业是有行。
案 此节是释“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之意,又起下章所谓“蓍之德”也。蓍以知来,故曰“遂知来物”。至精者,虚明鉴照,如水镜之无纤翳也。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
本义 此尚象之事。变则象之未定者也,参者三数之也,伍者五数之也,既参以变,又伍以变一先一后,更相考覈,以审其多寡之实也。错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谓也。
综者,总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谓也,此亦皆谓揲蓍求卦之事,盖通三揲两手之策,以成阴阳老少之画,究七八九六之数,以定卦爻动静之象也。参伍错综皆古语,而参伍尤难晓,按《荀子》云:窥敌制变,欲伍以参。韩非曰:省同异之言,以知朋党之分,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又曰:参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参。《史记》曰:必参而伍之。
又曰:参伍不失。《汉书》曰:参伍其贾,以类相准,此足以相发明矣。
集说 虞氏翻曰:观变阴阳始立卦,故“成天地之文”,“物相杂故曰文也”。数,六画之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故定天下吉凶之象也。
《朱子语类》云:纪数之法以三数之,则遇五而齐,以五数之,则遇三而会,所谓“参伍以变”者,前后多寡,更相反复,以不齐而要其齐。
又云:参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简而疏,错综所以极之,其治之也繁而密。
案 此节是释“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之意,又起下章所谓“卦之德六爻之义”也,卦爻以藏往,故曰“遂成天地之文”、“遂定天下之象”。成文,谓八卦也,雷风水火山泽之象具,而天地之文成矣。定象,谓六爻也,内外上下贵贱之位立,而天下之象定矣,参伍错综,亦是互文,总以见卦爻阴阳互相参错尔,至变者,变动周流,如云物之无定质也。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程子曰:老子曰“无为”,又曰“无为而无不为”。圣人作《易》未尝言无为,唯曰无思也,无为也,此戒夫作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动静之理,未尝为一偏之说矣。
胡氏居仁曰:天下之理。虽万殊而实一本,皆具于心,故感而遂通,若原不曾具得此理,如何通得。
林氏希元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即是上文“遂成天地之文”,“遂定天下之象”,“受命如响,遂知来物”之意,盖即上文而再謄说以归于至神也。
张氏振渊曰:十数“遂”字,已含有“神”字意,非精变之外别有神。
案 此节是总蓍卦爻之德而赞之。“遂通天下之故”,即上文“遂知来物”,“遂成天地之文”。而此谓之至神者,以其皆感通于寂然不动之中,其知来物非出于思,其成文定象非出于为也,神不在精变之外,其即精变之自然而然者与。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
本义 研,犹审也。几,微也。所以极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几者,至变也。
集说 韩氏伯曰:极未形之理则曰“深”,适动微之会则曰“几”。
孔氏颖达曰:言《易》道弘大,故圣人用之,所以穷极幽深而研覆几微也,“无有远近幽深”,是“极深”也。“参伍以变,错综其数”,是“研几”也。
俞氏琰曰:深,蕴奥而难见也。几,细微而未著也。极深,谓以易之至梢,穷天下之至精。研几,谓以易之至变,察天下之至变。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本义 所以通志而成务者,神之所为也。
集说 虞氏翻曰:深谓“幽赞神明”。“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故通天下之志”,谓蓍也。务,事也。谓《易》研几,故成天下之务,谓卦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故“不行而至”者也。
孔氏颖达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者,圣人用易道以极深,故圣人德深也,能通天下之志意,即是“受命如响,遂知来物”。“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者,圣人用易道以研几,故能知事之几微,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是也。
张子曰:一故神,譬之人身四体皆一物,故能触之而无不觉,不待心使至此而后觉 张氏浚曰:“精之能烛,来物遂知,天下之志,于此而可通,变之所该,万象以定,天下之务,于此而可成。
《朱子语类》云:通天下之志,犹言开物,开通其闭塞也,故其下对“成务”。
又《易精变神说》曰:变化之道,莫非神之所为也,故知变化之道,则知神之所为矣。《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所谓变化之道也。观变玩占,可以见其精之至矣;玩辞观象,可以见其变之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则亦何以为精为变而成变化之道哉,此变化之所以为神之所为也。
案 《本义》以至精为尚辞尚占之事,至变为尚象尚变之事,而《易说》以至精为变占,至变为象辞,盖本第二章居则观象玩辞,动则观变玩占而来,此与下章“蓍之德”,“卦之德”既相应,而第二章“观”、“玩”之义,亦因以明,当从此说。
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本义 此第十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
集说 蔡氏清曰:上章“四营而成易”,至“显道神德行”,则辞变象占四者俱有,但末及枚举而明言之耳,故此章详之。
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本义 开物成务,谓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业。冒天下之道,谓卦爻既设,而天下之道皆在其中。
集说 《朱子语类》云:古时民淳俗朴,风气未开,于天下事全未知识,故圣人立龟与之卜,作《易》与之筮,使人趋吉避害以成天下之事,故曰“开物成务”,物是人物,务是事务,冒是罩得天下许多道理在里。
又云:读《系辞》者,须要就卦中一一见得许多道理,然后可读系辞也。盖《易》之为书,大抵皆是因卜筮以教,逐爻开示吉凶,将天下许多道理,包藏在其中,故“冒天下之道”。
龚氏焕曰:通志以“开物”言,定业以“成务”言,断疑以“冒天下之道”言,唯其能“冒天下之道”,所以能“断天下之疑”,苟其道有不备,又何足以断天下之疑也哉。
案 此“通志”,即是上章“通志”,定业断疑,则是上章“成务”,言通志成务,则断疑在其中矣,又多此一句者,以起下文蓍卦爻二事。
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
本义 圆神,谓变化无方。方知,谓享有定理。易以贡,谓变易以告人。圣人体具 所谓无卜筮而知吉凶也,神武不杀,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谓。
集说 虞氏翻曰:吉凶与民同患,谓作《易》者其有忧患也。
韩氏伯曰:“圆”者运而不穷,“方”者止而有分,唯变所适,无数不周,故曰“圆”。
卦列爻分,各有其体,故曰“方”。
又曰:表吉凶之象,以同民所忧患之事,故曰“吉凶与民同患”也。
孔氏颖达曰:易道深远,故古之聪明睿知神武之君,用此易道,不用刑杀而威服之也。
崔氏憬曰:蓍之数,七七四十九,象阳园,其为用变通不定,因之以知来物,是“蓍之德园而神”也。卦之数八八六十四,象阴方,其为用也爻位有分,因之以藏往知事,是“卦之德方以知”也。
张子曰:圆神故能通天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业,易贡故能断天下之疑。
程子曰:安有识得《易》后,不知“退藏于密”,密是用之源,圣人之妙处。
龚氏原曰:圆者其体动而不穷,神者其用虚而善应,卦者象也,象则示之以定体,爻者变也,变则其义不可为典要,以此“洗心”者,所以“无思”也,以此“退藏于密”者,所以“无为”也,以此“吉凶与民同患”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王氏宗传曰:圣人以此蓍卦六爻,洗去夫心之累,则是心也,廓然而大公,用能退藏于密,而不穷之用,默存于我焉,此即《易》之所谓寂然不动也,无妙用之源,默存于圣人之心,则发而为用也,酬酢万物而不穷,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故曰“吉凶与民同患”,此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朱子语类》云;此言圣人所以作《易》之本也,蓍动卦静,而爻之变易无穷,未画之前,此理已具于圣人之心矣,然物主未感,则寂然个动,而无联兆之可名,及其出而应物,则忧以天下,而圆神方知者,各见于功用之实。“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言其体用之妙也,“洗心”、“退藏”言体,知来藏往言用,然亦只言体用具矣,而未及使出来处,到下文是“兴神物以前民用”,方发挥许多道理以尽,见于用也。
项氏安世曰:蓍用七,其德圆,卦用八,其德方,爻用九六,其义易贡。
胡氏居仁曰:“退藏于密”,只是其心湛然无事,而众理具在也。
何氏楷曰;德统而义析,故爻以义言。
又曰:吉凶之几,兆端已发,将至而未至者曰来,吉凶之理,见在于此,一定而可知者曰往。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
本义 神物,谓蓍龟。湛然纯一之谓齐,肃然警惕之谓戒,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兴,察民故,故知其用之不可不有以开其先,是以作为卜筮以教人,而于此焉斋戒以考其占,使其心神明不测,如鬼神之能知来也。
《朱子语类》云:此言作《易》之事也,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言用《易》之事也,斋戒敬也,圣人无一时一事而不敬,此特因卜筮而尤见其精诚之至,如孔子所慎斋战疾之意也。
又云“圣人既具此理,又将此理就蓍龟上发明出来,使民亦得前知而用之也。德,即圣人之德,圣人自有此理,又用蓍龟之理以神明之。
邱氏富国曰:心即神明之舍,人能洗之而无一点之累,则此心静与神明一,于揲蓍求卦之时,能以斋戒存之,则此心动与神明通,心在则神在矣。
案 “以此洗心”者,圣人体易之事也,在学者则居而观象玩辞,亦必如圣人之洗心,然后可以得其理,以此斋戒者,圣人用《易》之事也,在学者则动而观变玩占,亦必如圣人之斋戒,然后可以见其几,言圣人,以为君子之楷则也。
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
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戒用之谓之神。
本义 阖辟,动静之机也。先言坤者,由静而动也。乾坤变通者,化育之功也。见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法者,圣人修道之所为。而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也。
集说 荀氏爽曰:见乃谓之象,谓日月星辰,光见在天而成象也,“形乃谓之器”,万物生长,在地成形,可以为器用者也。观象于天,观形于地,制而用之,可以为法。
虞氏翻曰:阖,闭翕也,坤象夜,故以闭户也。辟,开也,乾象昼,故以开户也。
阳变阖阴,阴变辟阳,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也。
陆氏绩曰:圣人制器以周民用,用之不遗,故曰“利用出入”也,民皆用之而不知所由来,故“谓之神”也。
朱氏震曰:知阖辟变通者,“明于天之道”,知“利用出人民咸用之”者,“察于民之故。”《朱子语类》云:阖辟乾坤,理与事皆如此,书亦如此,这个只说理底意思多。
问:阖户谓之坤一段,只是这一个物,以其阖谓之坤,以其辟谓之乾,以其阖辟谓之变,以其不穷谓之通,以其发见而未成形谓之象,以其成形则谓之器,圣人修明以立教则谓之法,百姓日用则谓之神。曰:是如此,又曰:利用出入者,便是人生日用,都离他不得。
案 此节是说天道民故如此,“易有太极”一节,是说圣人作《易》以模写之。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本义 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阴阳之变。太极者,其理也,两仪者,始为一画以分阴阳。四象者,次为二画以分太少。八卦者,次为三画而三才之象始备,此数言者实圣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丝毫智力而成者,画卦揲蓍,其序皆然,详见序例《启蒙》。
《朱子语类》云:太极十全是具一个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恶,皆阴阳变化后方有。
又云,若说其生则俱生,太极依旧在阴阳里,但言其次序,须有这实理,方始有阴阳也,自一见在事物而观之,则阴阳函太极,推其本,则太极生阴阳。
又云:“易有太极”,便是下面两仪四象八卦,自三百八十四爻总为六十四,自六十四总为八卦,自八卦总为四象,自四象总为两仪,自两仪总为太极,以物论之,易之太极,如木之有根,浮图之有顶,但木之根,浮图之顶,是有形之极,太极却不是一物,无方所顿放,是无形之极,故周子曰:无极而太极,是它说得有功处,然太极之所以为太极,却不离乎两仪四象八卦,如一阴一阳之谓道,指一阴一阳为道则不可,然道不离乎阴阳也。
陈氏淳曰:太极只是浑沦极至之理,非可以形气言。《传》曰:“易有太极”。“易”只是阴阳变化,其所以为阴阳变化之理,则“太极”也。又曰:三极之道,三极云者,只是三才极至之理,其谓之三极者,以见三才之中,各具一太极,而太极之妙,无不流行于三才之中也,外此百家诸子,都说属气形去,如《汉志》谓太极函三为一,乃是指天地人,气形已具而浑沦未判,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正指此也。庄子谓“道在太极之先”,所谓太极,亦是指此浑沦未判者。而道又别悬空在太极之先,则道与太极分为二矣,不知道即是太极,道是以理之通行者而言,太极是以理之极至者而言,唯理之极至,所以古今人物通行,唯古今人物通行,所以为理之极至,更无二理也。
胡氏居仁曰:太极,理也。道理最大,无以复加,故曰“太极”,凡事到理上,便是极了,再改移不得,“太”是尊大之义,“极”是至当无以加也。
郑氏维嶽曰:《系辞传》中,乾坤多指奇偶二画言,三画六画,皆此二画之所生,而坤又乾之所生,乾者一而已,一者太极也。
徐氏在汉曰:同一乾坤也,以其一神则谓之太极,以其两化则谓之两仪,奇参偶中,乾体而有坎象,偶参奇中,坤体而有离象,故谓之四象,乾体而有坎象,则震艮之形成矣,坤体而有离象,则巽兑之形成矣,故谓之八卦。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本义 有吉有凶。是生大业。
集说 俞氏琰曰:八卦具而定吉凶,则足“以断天下之疑”矣,吉凶定而生大业,则有“以成天下之务”矣。
案 圣人作《易》,准天之道,故阴阳互变而定为八卦之象形,效民之故,故制为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
本义 富贵,谓有天下履帝位,“立”下疑有阙文。亹亹,犹勉勉也,疑则怠,决故勉。
集说 侯氏行果曰;亹,勉也。夫幽隐深远之情,吉凶未兆之事物,皆勉勉然愿知之,然不能也,及蓍成卦,龟成兆也,虽神道之幽密,未来之吉凶,坐可观也,是蓍龟成天下之勉勉也。
《朱于语类》:问:“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曰:人到疑而不能决处,便放倒了,不肯向前动有疑阻,既知其吉凶,自然勉勉住不得,则其所以亹亹者,卜筮成之也。
俞氏琰曰:颐,谓杂乱。探者抽而出之也。隐谓隐僻。索者,寻而得之也。深,谓不可测。钩者,曲而取之也。远谓难至。致者,推而极之也。
赵氏玉泉曰:八卦定吉凶而生大业,蓍龟定吉凶而成亹亹,可见卦画者蓍龟之体,蓍龟者卦画之用。
吴氏曰慎曰:上文“易有太极”四句,言作《易》之序,定吉凶生大业,言《易》之用,此节赞蓍龟之大用而先之以五者,又与阖户八句相应。
案 此节是合上文造化易书而通赞之,天地即乾坤,四时即变通,日月即见象,不言形器者,下文有“立成器”之文,盖在天者,示人以象而已,在地者,则民生器用之资,故上文“制而用之”,亦偏承形器而言也,此“备物致用立成器”之圣人,非富贵则不能,故中间又著此一句,明前文“制而用之”者,是治世之圣人也,至画卦生蓍,乃是作《易》之圣人,总而叙之,则见作《易》之功,与造物者同符,与治世者相配也。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本义 此四者,圣人作《易》之所由也,河图洛书,详见《启蒙》。
集说 孔氏颖达曰:河出图,洛出书,如郑康成之义,则《春秋纬》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孔安国以为河图则八卦是也,洛书则九畴是也,辅嗣之义,未知何从。
刘氏子翚曰:河图昧乎太极,则八卦分而无统,洛书昧乎皇极,则九畴滞而不通。
朱氏震曰:天生神物,谓蓍龟也。天地变化,四时也。天垂象,见吉凶,日月也。
河图洛书,象数也。则者彼有物而此则之也。
郭氏雍曰:河出图而后画八卦,洛出书而定九畴,故河图非卦也;包牺画而为卦,洛书非字也,大禹书而为字,亦犹箕子因九畴而陈《洪范》,文王因八卦而演《周易》, 胡氏炳文曰:四者言圣人作《易》之由,而《易》之所以作,由于卜筮,故以天生神物始焉。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本义 四象,谓阴阳老少。示,谓示人以所值之卦爻。
此第十一章,专言卜筮。
集说 游氏让溪曰:四象,谓阴阳老少。示,谓示人以变化之道,即上文“以通天下之志”者也。“系辞焉以尽其言”,故曰“告”’即上文以“定天下之业”者也。定之以吉凶,则趋避之机决矣,故曰“断”,即上文“以断天下之疑”者也,此结上数节之意。
案 此上三章,申“君子居则观其象”一节之义,首之以河图,次之以蓍策,遡《易》之所因起,是象变之本,辞占之源也。中间遂备列四者,为圣人之道,其又以辞为之先者,明学易从辞入也。辞生于变,变出于象,象归于占,故其序如此。辞变象占四者,以其包含来物,故谓之至精。以其错综万象,故谓之至变。以其无思无为而感通万故,故谓之至神。其所以为圣为之道者,以其皆出于圣人之心也,蓍德圆神,至精也,即圣心之所以知来。卦德方知,爻义易贡,至变也,即圣心之所以藏往。蓍卦之寂然感通,至神也,即圣心之所以“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也。以此洗心,则为圣人之德,以此立教,斯为圣人之道,故其易之所以作也,明于天道,则变化象形之类是也。察于民故,则制法利用之类是也。因而写之于《易》,其两仪四象八卦之交错,则变化象形具矣。吉凶定,事业起,则制法利用寓矣,于是託之蓍龟以前民用,盖与天地四时日月,及崇高有位备物成器之圣人,其道上下同流,而未之有异也,言易之道,于此尽矣,故复总言以结之。“天生神物”,结大衍之数也,天地变化垂象,结阖辟变通见象形器之类也。“河出图,洛出书”,结河图数也,《易》以蓍策而兴,以仰观俯察而作,而其发独智者,则莫大于龙马之祥,故其序又如此,四象兼象变,系辞辞也,定吉凶占也,复说四者以起《大有》上爻之意,而终“自天祐之占无不利”之指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本义 释《大有》上九爻义,然在此无所属,或恐是错简,宜在第八章之末。
集说 侯氏行果曰:此引《大有》上九辞以证之也,《大有》上九履信思顺,“自天祐之”,古人能依四象所示,系辞所告,则天及人皆共祐之,吉无不利者也。
朱氏震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六五履信而思乎顺,又自下以尚贤,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言此明获天人之理,然后“吉无不利”,圣人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合天人者也。
何氏楷曰:取《大有》上九爻辞以结上文,居则观象而玩辞,动则观变而玩占。则孜孜尚贤之意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与第二章“自天祐之”语遥应,非错简也。
案 何氏说是,然即是申释第二章结语之意,非遥应也。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本义 言之所传者浅,象之所示者深,观奇偶二画,包含变化,无有穷尽,则可见矣,变通鼓舞以事而言,两“子曰”字宜衍其一,盖“子曰”字皆后人所加,故有此误,如近世《通书》,乃周子所自作,亦为后人每章加以“周子曰”字,其设问答处,正如此也。
集说 崔氏憬曰:言伏羲仰观俯察,而立八卦之象以尽其意,设卦,谓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卦,情伪尽在其中矣,作卦爻之辞以系伏羲立卦之象,象既尽意,故辞亦尽言也。
苏氏轼曰:辞约而义广,故能尽其言。
《朱子语类》云:立象尽意,是观奇偶两画,包含变化,无有穷尽,设卦以尽情伪,谓有一奇一偶,设之于卦,自是尽得天下情伪,系辞焉便断其吉凶,“变而通之以尽利”,此言占得此卦,阴阳老少交变,因其变便有通之之理,“鼓之舞之以尽神”,既占则无所疑,自然行得顺便,如言“显道神德行”,“成天下之亹亹”,皆是“鼓之”“舞之”意。
又云:欧公说《系辞》不是孔子作,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者非,盖他不曾看立象以尽意一句,唯其言不尽意,故立象以尽之,学者于言上会得者浅,于象上会得者深。
问“鼓之舞之以尽神”,又言“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鼓”、“舞”恐只是振扬发明底意思否?曰:然,盖提撕警觉,使人各为其所当为也。
吴氏澄曰:立象,谓羲皇之卦画,所以示者也。尽意,谓虽无言,而与民同患之意,悉具于其中。设卦,谓文王设立重卦之名。尽情伪,谓六十四名,足以尽天下事物之情。
辞,谓文王周公之彖爻,所以告者也。羲皇之卦画,足以尽意矣,文王又因卦之象,设卦之名以尽情伪,然卦虽有名,而未有辞也,又系彖辞爻辞,则足以尽其言矣,设卦一句,在立象之后,系辞之前,盖竟尽意之绪,启尽言之端也。
梁氏寅曰:意非言可尽,则立象以尽意矣,言非书可尽,而又谓系辞尽其言何也?曰:言止于是而已矣,而意之无穷,圣人故贵于象也,故特首之曰“立象以尽意。”钱氏志立曰:圣人之意,不能以言尽,而尽于立象,此圣人以象为言也,因而系辞,凡圣人所欲言者,又未尝不尽于此。
又案 象足以尽意,故因象系辞,足以尽言,但添一“焉”字而意自明,圣笔之妙也。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
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本义 组,所包蓄者,犹衣之著也,《易》之所有,阴阳而已。凡阳皆乾,凡阴皆坤,画卦定位,则二者成列,而《易》之体立矣,乾坤毁,谓卦画不立,乾坤息,谓变化不行。
集说 胡氏瑗曰:此言大易之道,本始于天地,天地设立,阴阳之端,万物之理,万事之情,以至寒暑往来,日月运行,皆由乾坤之所生,故乾坤成而易道变化建立乎其中矣。若乾坤毁弃,则无以见易之用,易既毁,则无以见乾坤之用,如是,“乾坤或几乎息矣”。
张子曰:乾坤,天地也,易,造化也。
苏氏轼曰:乾坤之于《易》,犹日之于岁也,除日而求岁,岂可得哉,故乾坤毁则易不可见矣,易不可见则乾为独阳,坤为独阴,生生之功息矣。
叶氏良佩曰:乾位乎上,坤位乎下,乾坤成列,而易已立乎其中矣,四德之循环,万物之出入,易与天地相为无穷,必乾坤毁则无以见耳,若“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案 此节及“形而上者”一节,皆是就造化人事说,以见圣人立象设卦之所从来,未是说卦画蓍变,夫象以下,方是说圣人立象设卦系辞之事。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本义 卦爻阴阳皆“形而下者”,其理则道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变之义也,“变”、“通”二字,上章以天言,此章以人言。
集说 孔氏颖达曰:阴阳之化,自然相裁,圣人亦法此而裁节也。
程子曰:“形而上者”为道,“形而下者”为器,须著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也。
又曰:《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唯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元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也。
张氏浚曰:道形而上,神则妙之,器形而下,体则著之,道之与器,本不相离,散而在天地万物之间者,其理莫不皆然。
《朱子语类》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个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个形迹,有道须有器,有器须有道,物必有则。
问: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当,设若以有形无形言之,便是物与理相间断了,所以谓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间,分别得一个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别而不相离也。
问:只是这一个道理,但即形器之本体而离乎形器则谓之道,就形器而言则谓之器,圣人因其自然,“化而裁之则谓之变,推而行之则谓之通,举而措之则谓之事业。”裁也,行也,措也,都只是裁行措这个道。曰:是。
方氏应祥曰:此节正好体认立象尽意处,乾坤象也,而曰“《易》之緼”,曰“《易》立乎其中”,则意尽矣,正以象之所在即道也,“是故”字,承上乾坤来,形而上形而下,所以俱言形者,见得本此一物,若舍此一字,专言上者下者,便分两截矣。
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本义 重出以起下文。
集说 陆氏绩曰:此明说立象尽意设卦尽情伪之意也。
孔氏颖达曰:下文“极天下之赜存乎卦,鼓天下之动存乎辞”,为此故史引其文也。
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
本义 卦即象也,辞即爻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谓卦体之中,备阴阳变易之形容,“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是说出这天下之动,如“鼓之”“舞之”相似。
俞氏琰曰:赜以象著,卦有象,则穷天下之至杂至乱,无有遗者,故曰极,动以辞决,使天下乐于趋事赴功者,手舞足蹈而不能自己,故曰鼓。
案 极天下之赜,结“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两句,鼓天下之动,结“系辞焉以尽其言”一句。
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本义 卦爻所以变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
集说 程子曰:《易》因爻象论变化,因变化论神,因神论人,四人论德行、大体通论《易》道,而终于“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程氏敬承曰:上系末章归重德行,下系末章亦首揭出德行,此之德行,即所谓乾坤易简者乎。
张氏振渊曰:谓之变,谓之通,变通,因化裁推行而有也,“存乎变”,“存乎通”,化裁推行,因变通而施也。
案 “化而裁之推而行之”,结“变而通之以尽利”一句,“神而明之”以下,结“鼓之舞之以尽神”一句,上文化裁推行,是泛说天地间道理,故曰“谓之变”“谓之通”。
此化裁推行,是说《易》书中所具,故曰“存乎变”“存乎通”,言就《易》道之变处,见得圣人化裁之妙,就《易》道之通处,见得圣人推行之善也,“神而明”之“神”字,即根鼓舞尽神来,辞之鼓舞乎人者,固足以尽神,然必以人心之神,契合乎《易》之神,然后鼓舞而不自知,此所谓神而明之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是其所以能神明处。
总论 胡氏炳文曰:上系凡十二章,末乃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盖欲学者自得于书言之外也,自立象尽意至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反复《易》之书言可谓尽矣,末乃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然则《易》果书言之所能尽哉,得于心为德,履于身为行,《易》之存乎人者,盖有存乎心身,而不徒存乎书言者矣。
案 此章盖总上十一章之意而通论之,“言不尽意”,故“立象以尽意”,谓伏羲也。
“书不尽言”,故因象而“系辞焉以尽其言”,谓文周也。象之足以尽意者,言之指陈有限,而象之该括无穷也。因象系辞之足以尽言者,象为虚傲之象,而该括无穷,则辞亦为假託之辞,而包涵无尽也。变通尽利者,象所自具之理,而所以定吉凶。鼓舞尽神者,辞所发挥之妙,而所以成亹亹也,其言乾坤者,推象之所自来也。有天地故有变化,滞于形以观之,亦器焉而已;超乎形以观之,则道之宗也。因天地之变化而裁之,则人事所由变也;因其可通之理而推行之,则人事所由通也。自古圣人所以定天下之业者,此而已矣,是以作《易》之圣,观乾坤之器而立象,推其变通之用而设辞,使天下后世,欲裁化而推行者,于是乎在,其动可谓盛矣。虽然,象足以尽意,而有画前之《易》,故贵乎默而成之也,辞足以尽言,而有言外之意,故贵乎不言而信也,此则所谓神而明之。盖学之不以观玩之文,而明之不以口耳之粗者也,德行,谓有得于易简之理。
系辞下传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本义 成列,谓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类。象,谓卦之形体也,因而重之,凋各田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为六十四也。爻,六爻也,既重而后卦有六爻也。
集说 韩氏伯曰:夫八卦备天下之理而未极其变,故“因而重之”,以象其动用,则爻卦之义,所存各异,故“爻在其中矣”。
《朱子语类》云;八卦所以成列,乃是从太极两仪四象渐次生出,以至于此,画成之后,方见其有三才之象,非圣人因见三才,遂以己意思维而连画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节次生出,若施生逐爻,则更加三变,方成六十四卦,若并生全卦,则只用一变,便成六十四卦,虽有迟速之不同,然皆自渐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画成之后,然后见其可尽天下之变。
柴氏中行曰:“八卦列成”,则凡天下之象,举在其中,不止八物,如《说卦》中所列皆是。
郑氏曰:卦始于三画,未有爻也,“因而重之”,其体有上下,其位有内外,其时有初终,其序有先后,而“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椎,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
本义 “刚柔相推”,而卦爻之变,往来交错,无不可见,圣人因其如此而皆系之辞以命其吉凶,则占者所值当动之爻象,亦不出乎此矣。
集说 虞氏翻曰:“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故“变在其中矣”,系彖象九六之辞,故“动在其中”,“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者也。
孔氏颖达曰:上系第二章云,“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变化之道,在刚柔相推之中。
蔡氏清曰:天文地理,人事物类,一刚一柔尽之矣,二者之外,再无余物也,故凡刚者皆柔之所推也,凡柔者皆刚之所推也,而《易》卦中亦只是刚柔二者而已,非刚则柔,非柔则刚,在刚皆柔之所推,在柔皆刚之所推。
苏氏濬曰:动在其中,虞翻谓“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此说极是,此“动”字,与下文“生乎动”,“天下之动”,三“动”字俱同,《易》之辞,原是圣人见天下之动而系之者,故曰“鼓天下之动存乎辞”,此即动在其中之说,非当动卦爻之谓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
集说 龚氏原曰:象者一卦之成体也,故天下之赜存焉;爻者六位之变动也,故天下之动存焉,刚柔相推所以成爻也。面“爻者言乎变”,则“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所以明爻也,而辞者以鼓天下之动,则“动在其中矣”,卦则兆于成列而备于重,爻则兆于变而备于动,故吉凶悔吝生焉。
苏氏濬曰:《传》曰“寂然不动”,又曰“动之微吉之先见”,当其不动也,尚无所谓吉,又何有于凶,唯动而微也,吉斯见焉,动而纷纭杂乱也,凶与悔吝,始生于其间矣。
案 此是复说“系辞焉而命、动在其中”之意。凡天下之吉凶悔吝,皆生于人事之动,故《易》中有吉凶悔吝之辞,而动在其中。
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
本义 一刚一柔,各有定位,自此而彼,变以从时。
集说 朱氏震曰:爻有刚柔,不有两则一不立,所以“立本”也,刚柔相变,通其变以尽利者趣时也,“趣时者”时中也。
张氏浚曰:刚柔相推,往来进退,为变无常,而莫不因乎自然之时,故曰“趣时”。
《朱子语类》云:此两句相对说,刚柔者阴阳之质,是移易不得之定体,故谓之本,若刚变为柔,柔变为刚,便是变通之用。
又云:刚柔者昼夜之象,所谓“立本”,变化者进退之象,所谓“趣时”,刚柔两个是本,变通便只是其往来者。
胡氏炳文曰:卦有卦之时,爻有爻之时,立本者天地之常经,“趣时者”古今之通义。
梁氏寅曰:刚柔者立本,乃不易之体,即所谓“阖户”、“辟户”也,变通者趣时,乃变易之用,即所谓往来不穷也。
蔡氏清曰:刚柔立本,所谓变易而对待者,变通趣时,所谓变易而流行者。
案 此是复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之意,凡天地间之理,两者对待,斯不偏而可以立本,两者迭用,斯不穷而可以趣时,故《易》中刚柔相推,而变在其中。
吉凶者,贞胜者也。
本义 贞,正也,常也。物以其所正为常者也,天下之事,非吉则凶,非凶则吉,常相胜而不已也。
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
本义 观,示也,天下之动,其变无穷,然顺理则吉,逆理则凶,则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
集说 《朱子语类》云:吉凶常相胜,不是吉胜凶,便是凶胜吉,二者常相胜,占曰“贞胜”。天地之道则常示,日月之道则常明,“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天下之动虽 高氏萃曰:天常示人以易,地常示人以简,虽阴不能以不愆,阳不能以不伏,而贞观之理常自若也,日明乎昼,月明乎夜,虽中不能以不昃,盈不能以不食,而贞明之理常自若也,天下之动,进退存亡,不可以一例测,然而顺理则裕,从欲唯危同一揆也,惠迪之吉,从逆之凶,无二致也,是则造化人事之正常,即吉凶之贞胜,岂可以二而求之哉。
案 自“吉凶”“贞胜”至此为一节,又承“吉凶悔吝生乎动”之意,而明其理之一也,“贞胜”之义,张子以为以正为胜,朱子以为二者常相胜,今玩文义当为以常为胜,盖天下容有善而遇凶,恶而获古者,然非其常也,惠迪吉,从逆凶,乃理之常,故当以常者为胜,如天地则以常者观示,日月则以常者照临,偶有变异,不足言也,天下之动,岂不常归于一理乎。
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
本义 确然,健貌。隤然,顺貌,所谓贞观者也。
集说 韩氏伯曰:确,刚貌也。隤,柔貌也。乾坤皆恒一其德,故简易也。
案 此节又承刚柔立本,变通趣时之意,而明其理之一也。乾坤者,刚柔之宗也,乾坤定位,而变化不穷矣,然其所以立本者,一归于易简之理,所谓天有显道,厥类维彰,万古不易者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本义 此,谓上文乾坤所示之理,爻之奇偶卦之消息,所以效而像之。
案 “爻也者效此”,是结“吉凶悔吝生乎动”而“贞夫一”之意,“象也者像此”,是结刚柔变通而归于易简之意。
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
本义 内,谓蓍卦之中。外,谓蓍卦之外。变,即动乎内之变。辞,即见乎外之辞。
集说 韩氏伯曰:功业由变以兴,故“见乎变”也。辞也者各指其所之,故曰“情”也。
张子曰:因爻象之既动明吉凶于未形,故曰“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随爻象之变以通其利,故功业见也,圣人之情,存乎教人而已。
吴氏澄曰:圣人与民同患之情,皆于《易》而著见,圣人之道而独归重于辞,盖此篇为《系辞》之传故也。
案 爻象者,动而无形,故曰“内”。吉凶者,显而有迹,故曰“外”,非专以蓍筮言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此第一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业。
集说 陆氏绩曰:人非财不聚,故圣人观象制器,备物尽利,以业万民而聚之也,盖取聚人之本矣。
崔氏憬曰:言圣人行易之道,当须法天地之大德,宝万乘之大位,谓以道济天下为宝,是其大宝也。夫财货人所贪爱,不以义理之,则必有败也,言辞人之枢要,不以义正之,则必有辱也。百姓有非,不以义禁之,则必不改也,此三者皆资于义,以此行之,得其宜也,故知仁义,圣人宝位之所要也。
张子曰:将陈理财养物于下,故先叙天地生物。
朱氏震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者仁也,圣人成位乎两间者仁而已,不仁不足以参大地,义所以为仁,非二本也,故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王氏宗传曰:圣人所以配天地而王天下者,亦有仁义而已矣。仁,德之用也。义,所以辅仁也。“理财”,如所谓作网罟以佃渔,作耒耜以耕耨,致民聚货以变易之类是也。
“正辞”,如所谓易结绳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是也。“禁民为非”,如所谓重门击柝以待暴客,剡矢弦弧以威天下是也。
《朱子语类》云:“正辞”便只是分别是非。又曰:教化便在正辞里面。
项氏安世曰:圣人之仁,即天地之生,“大宝曰位”,即“崇高莫大乎富贵”也,自此以下,以包牺氏神农氏黄帝尧舜氏实之,皆圣人之富贵者也。财者,百物之总名,皆民之所利也。理财,谓水火金木土谷推修,所以利之也。正辞,谓殊贵贱使有度,明取予使有义,辨名实使有信,利之所在,不可不导之使知义也。禁民为非,谓宪禁令,致刑罚,以齐其不可导者也。盖养之教之而后齐之,圣人之政,尽于此三者矣,其德意之所发,主于仁民,义者,仁之见于条理者也。
真氏德秀曰:案《易》之并言仁义者,此章及《说卦》“立天之道”章而已,在天地则曰生,在圣人则曰仁,仁之义盖可识矣。
李氏心传曰:蔡邕云,以仁守位,以财聚人,则汉以前已用此“仁”字矣。
总论 孔氏颖达曰:此第一章,复释上系第二章象爻刚柔吉凶悔吝之事,更具而详之。
案 此章与《上传》第二章相应,故《上传》第三章以后,皆申说第二章之意,《下传》则自第二章之后,皆申说此章之意也。“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即所谓设卦观象也。
因爻象中刚柔相推之变,面系之吉凶悔吝之辞,即所谓“系辞焉而明吉凶”也,此四句,由象以及于辞者,作《易》之序也。下文又由辞之吉凶悔吝而推本于刚柔之象,盖《传》本为系辞而作,而《下传》尤详焉,故其立言如此。吉凶悔吝,由动而生者,盖以刚柔迭运,变面从时故也,吉凶之遇,参差不齐,然以常理为胜,而天下之动可一者,以刚柔变化,不离乾坤,乾易坤简,而天下之理得故也。“爻象动乎内”四句,又总而结言之,“天地大德”一节,《本义》原属此章,然诸儒多言宜为下章之首,盖下章所取十三卦,无非“理财”、“正辞”、“禁非”之事,其说可从也。
本义 王昭素曰:与地之间,诸本多有“天”字,俯仰远近所取不一,然不过以验阴阳消息两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顺动止之性,万物之情,如雷风山泽之象。
集说 朱氏震曰:自此以下,明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者,无非有取于《易》,皆仁也。曰:王天下者,明守位也。
王氏申子曰:伏羲氏继天立极,画八卦以前民用,后之圣人,相继而作,制为相生相养之具,皆所以广天地生生之德,自网罟至书契是也。
蔡氏清曰:“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二句,一是精,一是粗,一是性情,一是形体,其下十三卦所尚之象,一皆出此。
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本义 两目相承而物丽焉。
集说 孔氏颖达曰:案诸儒象卦制器,皆取卦之爻象之体,韩氏之意,直取卦名因以制器,案《上系》云,以“制器者尚其象”,则取象不取名也,韩氏乃取名不取象,于义未善。
胡氏瑗曰:盖者疑之辞也,言圣人创立其事,不必观此卦而成之,盖圣人作事立器,自然符合于此之卦象也,非准拟此卦而后成之,故曰“盖取”。
案 孔氏所议韩氏是也,且六十四卦名,是文王所命,包牺之时,但有八卦名象而已,黄农尧舜,不应便取卦名,经文盖取之云,虽曰假托,不必拘泥,然亦不应大段疏脱也。
古者网罗所致曰离。《诗》曰:“鱼网之设,鸿则离之。”又曰:“有兔爰爰,雉离于罗。”二体皆离,上下网罗之象。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本义 二体皆木,上入下动,天下之益,莫大于此。
集说 蔡氏渊曰:耜,耒首也,断木之锐而为之。耒,耜柄也,揉木使曲面为之。
吴氏澄曰:《益》上巽二阳,象耒之自地上而入,下震一阳,象耜之在地下而动也。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本义 日中为市,上明而下动,又借噬为市,嗑为合也。
集说 耿氏南仲曰:有菽粟者,或不足乎禽鱼,有禽鱼者,或不足乎菽粟,罄者无所取,积者无所散,则利不布,养不均矣,于是“日中为市”焉。日中者,万物相见之 郑氏东卿曰:十三卦始《离》次《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货而已。食货者,生民之木也。
案 离为日中,震为动出,当日中而动出,市集之象。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本义 乾坤变化而无为。
集说 郭氏雍曰:“垂衣裳而天下治”,无为而治也,无为而治者无也焉,法乾坤易简而已。
王氏申子曰:神农以上,民用未滋,所急者食货而已,此聚人之本也,及黄帝尧舜之世,民用日滋,若复守其朴略,则非变而通之之道,故“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
使民由之而不倦,神其化,使民宜之而不知,凡此者非圣人喜新而恶旧也。“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之道然也。
吴氏澄曰:风气渐开,不可如朴略之世,此穷而当变也,变之则通而不穷矣,其能使民喜乐不倦者,以其通之之道,神妙不测,变而不见其迹,便于民而民皆宜利之故尔。
俞氏琰曰:时当变则变,不变则穷,于是乎有变而通之之道焉,变而通之所以趣时也,民之所未厌,圣人不强去,民之所末安,圣人不强行,夫唯其数穷而时将变,圣人因而通之,则民不倦。由之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神也,以渐相忘于不言之中者,化也。
蔡氏清曰:时之当变也而通其变,然其所以变通之者,非圣人强用其智虑作为于其间也,因其自然之变,而以自然之理处之,是谓神而化之也,神而化,即其变通之妙于无为也。
苏氏濬曰:言通变神化,而独详于黄帝尧舜;言黄帝尧舜,而独取渚乾坤,乾坤诸卦之宗也。黄帝尧舜,千古人文之始,中天之运,至此而开,洪荒之俗,至此而变,此所以为善发羲皇之精蕴也。
案 守旧则倦更新则不宜,凡事之情也,变其旧使民不倦者,化也,趋于新使民咸宜者,神而化之也。
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揖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
本义 木在水上也,致远以利天下,疑衍。
集说 《九家易》曰:木在水上,流行若风,舟楫之象也。
何氏楷曰:近而可以济不通,远而可以致远,均之为天下利矣,取诸《涣》者,其象巽木在坎水之上,故《彖》曰“利涉大川”,《彖传》曰“乘木有功。”本义 下动上说。
集说 董氏真卿曰:平地任载之大车,载物之多者,则服牛以引重,田车兵车乘车之小车,载人而轻者,则乘马以致远。
案 外说内动,象牛马之奔于前而车动于后也。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
本义 豫,备之意。
集说 杨氏文焕曰:川途既通,则暴客至矣,又不可无御之之术,重门以御之,击柝以警之,则暴客无自而至。
俞氏琰曰:坤为阖户,“重门”之象也。震,动而有声之木,“击柝”之象也。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
本义 下止上动。
集说 邱氏富国曰:以象言之,上震为木下艮为土,震木上动,艮土下止,杵臼治米之象。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
本义 睽乖然后威以服之。
集说 朱氏震曰:知耒耜而不知杵臼之利,则利天下者有未尽,故教之以杵臼之利,知门柝而不知“弧矢之利”,则威天下者有末尽,故教之以“弧矢之利。”徐氏几曰:其害之大者,以“重门”“击柝”不足以待之,故必有弧矢以威之。
案 离,威也。兑,说也。威而以说行之,所谓说以犯难,民忘其死。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本义 壮固之意。
集说 司马氏光曰:风雨,动物也,风雨动于上,栋宇健于下,《大壮》之象也。
蔡氏渊曰:栋,屋脊檩也。宇,椽也。栋直而上,故曰“上栋”。字两垂而下,故曰“下宇”。
俞氏琰曰:圣人之干物,有为之者,有易之者,古未有是而民利之也,今则为之,所以贻于后也,古有是而民厌之也,今则易之,所以革于前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
本义 送死大事,而过于厚。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本义 明决之意。
此第二章,言圣人制器尚象之事。
集说 耿氏南仲曰:已前不云“上古”,已下三事,或言“古”,与上不同者,盖未造此器之前,更无余物之用,故不言“上古”也,以下三事,皆是未造此物之前,别有所用,今将后用而代前用,故本之云“上古”及“古”者。
案 兑为言语可以通彼此之情,书之象也。乾为健固,可以坚彼此之信,契之象也。
总论 吴氏澄曰:十三卦之制作,自画卦而始,至书契而终,盖万世文字之祖,肇于画卦,而备于书契也。
案 此章申第一章“变通”、“趣时”而原于易筒之意,盖在天地,则为刚柔,在人则为仁义,仁义者立本者也,因风气之宜而通其变,则其所以趣时者也,法始于伏羲成于尧舜,故自八卦既画,而可以周万事之理,凡网罟耒耜至于书契,莫非易理之所有也,观其穷而变,变而通,则趣时之用不穷,然其神而化之,无为而民安焉,则易简之理唯一,故其取诸诸卦者,取诸其趣时也,而其取诸乾坤者,取诸其易简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本义 易卦之形,理之似也。
集说 干氏宝曰:言是故,又总结上义也。
崔氏憬曰:上明取象以制器之义,故以此重释于象,言易者象于万物,象者形像之象也。
吴氏澄曰:此章之首第一节,总叙以起下文,自包牺至书契,言制作之事,而以是故总结之,谓《易》卦皆器物之象,象者像似之义,圣人制器,皆与卦象合也。
案 凡章首不用“是故”字,曰“是故”者,承上结上之辞也,诸儒以此句为上章结语者,似是。
彖者材也。
本义 彖,言一卦之材。
集说 韩氏伯曰:彖,言成卦之材,以统卦义也。
案 “材”者,构屋之木也,聚众材而成室,彖亦聚卦之众义以立辞,故《本义》谓“彖言一卦之材。”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
本义 效,放也。
集说 胡氏瑗曰:爻有变动,位有得失,变而合于道者为得,动而乖于理者为失,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本义 “悔吝”本微,因此而“著”。
此第三章。
集说 保氏八曰:彖者,言一卦之材,所以断一卦之吉凶悔吝,爻者言一爻之动,所以断一爻之吉凶悔吝。
何氏楷曰:吉凶在事本显,故曰“生”。悔吝在心尚微,故曰“著”。悔有改过之意,至于吉则悔之著也,吝有文过之意,至于凶则吝之著也,原其始而言,吉凶生于悔吝,要其终而言,则悔吝著而为吉凶也。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
本义 震坎艮为阳卦,皆一阴二阴,巽离兑为阴卦,皆一阴二阳。
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偶。
本义 凡阳卦皆五画,凡阴卦皆四画。
集说 韩氏伯曰:夫少者多之所宗,一者众之所归,阳卦二阴,故奇为之君,阴卦二阳,故偶为之主。
陈氏埴曰:二偶一奇,即奇为主,是为阳卦,二奇一偶,即偶为主,是为阴卦,故曰“阳卦多阴,阴卦多阳。”案 “阳卦奇,阴卦偶”。言阳卦主奇,阴卦主偶也,须如韩氏陈氏之说,乃与下文相应。
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本义 君,谓阳。民,谓阴。
此第四章。
集说 朱氏震曰:阴阳二卦,其德行不同何也,阳卦一君而遍体二民,二民共事一君,一也,故为君子之道,阴卦一民共事二君,二君共争一民,二也,故为小人之道。
吴氏曰慎曰:阳卦固主阳也,而阴卦亦主阳,可见阳有常尊也。
案 此章是释“彖者材也”之义,而原其理于一也,自八卦始成而分阴分阳,一奇则为阳卦者,以其一君二民,是君之权出于一,君为主也,君为主,则君子之道行,故曰“君子之道。”一偶则为阴卦者,以其二君一民,是君之权出于二,反若民为主也,民为主,则小人之道行,故曰“小人之道。”古今言《易》者,曰阳为君子,阴为小人,盖以为善恶淑慝之称焉,岂知阴阳不可以相无,如有君不可以无民,乌有善恶淑慝之分哉,唯其君之道,一而有统,则民之众,翕然从令,岂非君子之道乎,若君之道二而多门,则民之卑,各行其私,岂非小人之道乎,善恶淑慝,由此而生,吉凶治乱,由此而 《易》曰:“幢幢往来,朋从尔思。”予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
本义 引《咸》九四爻辞而释之,言理本无二,而殊涂百虑,莫非自然,何以思虑为哉,必思而从,则所从者亦狭矣。
集说 韩氏伯曰:天下之动,必归于一,思以求朋,未能一也,一以感物,不思而至。
孔氏颖达曰:此一之为道为可尚,结成前文阳卦,以一为君,是君子之道也。
徐氏几曰:涂虽殊而归同,则往来自不容无,而加之憧憧则私矣,虑虽百而致一,则思亦人心所当有,而局于朋从则狭矣。
蔡氏清曰:天下感应之理,本同归也,但事物则千形万状,而其涂各殊耳,天下感应之理,本一致也,但所接之事物不一,而所发之虑,亦因之有百耳,夫虑虽百而其致则一,涂虽殊而其归则同,是其此感彼应之理,一出于自然而然,而不必少容心于其间者,吾之应事接物,一唯顺其自然之理而已矣,“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本义 言“往”、“来”、“屈”、“信”,皆感应自然之常理,加憧憧焉则入于私矣,所以必思而后有从也。
集说 张子曰: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诚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杂之伪也。
《朱子语类》云:“日往则月来”一段,乃承上文“憧憧往来”而言,往来皆人之所不能无,但憧憧则不可。
案 夫子引此爻,是发明贞一之理,故亦从天地日月说来,日月有往来,而归于生明,所谓贞明者也。寒暑有往来,而归于成岁,所谓贞观者也。天下之动,有屈有信,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本义 因言屈信往来之理,而又推以言学亦有自然之机也,精研其义,至于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适不安,信之极也,然乃所以为人而崇德之资,内外交相养,互相发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复明上往来相感,屈信相须,尺蠖之虫,初行必屈,言信必须屈也,龙蛇初蛰,是静也,以此存身,言动必因静也,圣人用精粹微妙之义,入于神化,寂然不用,乃能致其所用,先静后动,是动因静而来也,利己之用,安静其身,可以增祟其德,此亦先静后动,动亦由静而来也。
《朱子语类》云:且如“精义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的却不必思,致用的是事功,是效验。
俞氏琰曰:精研义理,无毫厘之差,而深造于神妙,所以致之于用也。见于用而利,施于身而安,所以为崇德之资也。“精义入神”,内也;“致用”,外也,自内而达外,犹“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利用安身”,外也;“崇德”,内也,即外以养内,亦犹“龙蛇之蛰以存身也”。
蔡氏清曰:利用如何以崇其德,盖外边事事都能迎刃解将去,则胸中所得益深,所造亦远矣,精义以致知言,义者,事理之宜也,入神,只谓到那不容言之妙处,利用以行言,利用故安身,若其用有不利,则亦不能在在皆安,而泰然处之矣,盖躬行心得,自是相关之理。
吴氏一源曰:人皆知信之利,而不知屈之所以利也,故以“尺蠖”、“龙蛇”明之,专言屈之利以示人,正欲人养静以一动,无感以待感也。
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本义 下学之事,尽力于精义利用,而交养互发之机,身不能己,自是以上,则亦无所用其力矣,至于“穷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来而信也,是亦感应自然之理而已。张子曰: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
此上四节,皆以释《咸》九四爻义。
集说 孔氏颖达曰:“精义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二者皆人理之极,过此二者以往,则微妙不可知,穷极微妙之神,晓知变化之道,乃是圣人德之盛极也。
张子曰:“精义入神”,事豫吾内,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豫吾外,致养吾内也。“穷神知化”,乃养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又曰: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其在人也,知义用利,则神化之 又曰:穷神,是穷尽其神也。入神,是仅能入于神也,言人如自外而入,义固有浅深。
《朱子语类》云:“穷神知化”德之盛,这“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后便能“穷神知化”,便如聪明睿知皆由此出,自诚而明相似。
又云;“穷神知化”,“化”是逐些子挨将去底,一日复一日,一月复一月,节节挨将去,便成一年。“神”是一个物事,或在彼,或在此,当其在阴时,全体在阴,在阳时,全体在阳,都只是这一物,两处都在不可测,故谓“神”。横渠言:一故神,两故化。又注云:两在故不测。这说得甚分晓。
又云:“天下何思何虑”一句,便先打破那个思字,却说“同归殊涂,一致百虑”,又再说“天下何思何虑”,谓何用如此“憧憧往来”,“尺蠖”、“龙蛇”之屈信,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则不来,不屈则亦不信也。今之为学,亦只是如此。“精义入神”,用力于内,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乎外,乃所以崇德乎内,只是如此作将去,虽至于穷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虑之有。
蔡氏清曰:“未之或知”者,不容于有思,不容于有为也,神以存主处言,化以运用处言,其神化者,亦岂出于精义利用之外哉,其始有待于思为,则曰精义利用,其终无待于思为,则曰“穷神知化”,所造有浅深,理则无精粗也。
张氏振渊曰:未有下学功夫不到,而顿能上达者,神化功夫,正在精义利用作起,此正实落下手处,即造到神化地位,不过精义利用,渐进渐熟耳,德盛不是就穷神知化上赞他德之盛,唯德盛方能“穷神知化。”案 “精义入神”,则所知者精深,穷理之事也。“利用安身”,则所行者纯熟,尽性之事也。“穷神”则不止于入神,其心与神明相契者也,‘知化”则不止于利用,其事与造化为徒者也,至命之事也,穷理尽性,学者所当用力,至命则无所用其力矣,故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又案 此章是释“爻者效天下之动”之义,而原其理于一也,自此以下十一爻,皆是发明此意,而此爻之义,尤为亲切,盖感应者动也,不可逐物憧憧,而唯贵于贞固其心者一也,所以然者,此心此理,一致同归,本不容以有二也,故首以此爻,而以致一恒心两爻终焉。
《易》曰:“团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邪?本义 释《困》六三爻义。
集说 《朱于语类》云:有著力不得处,若只管著力去作,少间去作不成,他人便道自家无能,便是辱了名。
本义 括,结碍也。此释《解》上六爻义。
集说 韩氏伯曰:括,结也。君子待时而动,则无结阂之患也。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屦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
本义 此释《噬嗑》初九爻义。
集说 冯氏椅曰:不以不仁为耻,故见利而后劝于为仁,不以不义为畏,故畏威而后惩于不义。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
本义 此释《噬嗑》上九爻义。
集说 董氏仲舒曰: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
吴氏曰慎曰:恶,以己之所行者言,罪,以法之所丽者言。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本义 此释《否》九五爻义。
集说 孔氏颖达曰:所以今有倾危者,由前安乐于其位,自以为安,故致今日危也。
所以今日灭亡者,由前保有其存,恒以为存,故今致灭亡也。所以今有祸乱者,由前自恃有其治理,恒以为治,故今致祸乱也。是故君子今虽获安,心恒不志倾危之事,国虽存,心恒不忘灭亡之事,政虽治,心恒不忘祸乱之事,心恒畏惧其将灭亡,其将灭亡,乃“系于苞桑”之固也。
谷氏家杰曰:养尊处优曰“安”,宗社巩固曰“存”,纲举目张曰“治”。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
本义 此释《鼎》九四爻义。
集说 张氏浚曰:自昔居台鼎之任,德力知三者一有阙,则弗能胜其事,而况俱不 钱氏时曰: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后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度力度德而后居其任,虽百工胥史,且犹不苟,况三公乎,为君不明于所择,为臣不审于自择,以至亡身危主,误国乱天下,皆由不胜任之故,可不戒哉。
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本义 此释《豫》六二爻义,《汉书》吉之之间有凶字。
集说 孔氏颖达曰:动,谓心动,事动,初动之时,其理未著,唯纤微而已,已著之后,则心事显露,若未动之先,又寂然顿无,几是离无入有,在有无之际,故云“动之微”也。直云古不云凶者,凡豫前知几,皆向吉而背凶,违凶而就吉,无复有凶,故特云吉也,诸本或有“凶”字者,其定本则无。
崔氏憬曰:此爻得位于中,于豫之时,能顺以动而防于豫,如石之耿介,守志不移,虽暂豫乐,以其见微而不终日,则能“贞吉”,“断可知矣”。
张子曰:“知几”者,为能以屈为信。
《朱子语类》云:上交贵于恭逊,恭则便近于谄,下交贵于和易,和则便近于渎,盖恭与谄相近,和与渎相近,只争些子便至于流也。
又云:“几者动之微”,是欲动未动之间,便有善恶,便须就这处理会,若到发出处,便怎生奈何得,所以圣贤说谨独,便都是要就几微处理会。
项氏安世曰:谄者本以求福,而祸常基于谄,渎者本以交欢,而怨常起于渎,《易》言“知几”,而孔子以不谄不渎明之,此真所谓“知几者”矣,欲进此道,唯存察之密,疆界素明者能之,此所以必归之于“介如石”者与。
何氏楷曰;“知微知彰”,微而能彰,“介于石”也。“知柔知刚”。柔而能刚,“不终日”也。
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祗悔,元吉。”本义 殆,危也。庶几,近意,言近道也,此释《复》初九爻义。
集说 虞氏翻曰:“复以自知”,“自知”者明,谓颜子不迁怒,不贰过,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也。
侯氏行果曰:失在未形,故有不善,知则速改,故无大过。
《朱子语类》云:或以几为因上文“几”字而言,但《左传》与《孟子》“庶几”两字,都只作“近”字说。
项氏安世曰:于微而知其彰,于柔而知其刚,盖由用心之精,烛理之明,是以至此。
欲进此者,当自颜子始,毫厘丝忽之过,一萌于方寸之间,可谓“微”矣。而吾固已了然而见之,可谓“柔”矣。而吾已斩然而绝之,此章内十一爻,虽各为一段,而意皆相贯,此爻尤与上爻文意相关。
陆氏振奇曰:诚则明者,“知几”之神,由介石来也,明则诚者,不远之复,由真知得也,在《豫》贵守之固,故日“贞吉”,在《复》贵觉之早,故曰“元吉”。
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
本义 絪緼,交密之状。醇,谓厚而凝也。言气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此释《损》六三爻义。
集说 侯氏行果曰:此明物情相感,当上法“姻緼”“化醇”致一之道。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本义 此释《益》上九爻义。
此第五章。
集说 项氏安世曰:“危以动则民不与”,党与之与,“无交而求则民不与”,取与之与也。
又曰:以“《易》”对“惧”,其义可见,直者其语“《易》”,曲者其浯“惧”,乾之所以“《易》”者;以其直也。
郭氏鹏海曰:事不顺理,从欲唯危,为“危以动。”心知非理,自觉惶恐,为“惧以语”,恩非素结,信非素孚,为“无交而求”。
总论 叶氏良佩曰:下十爻,皆承《咸》九四而言。
吴氏一源曰:《咸》后十爻,皆发明理之贞一而不憧憧耳,往来屈信无二致也。天地,所以成造化,圣人所以臻造化,推之事事物物,莫不皆然,故知动静之一致,则能藏器而时动,知小大之一致,则能谨小以无咎,知安危之一致,则能危以保其安,各显微之一致,则能见几而作,不远而复,知损益之一致,则能损而得友,彼非所困而困非所任而任,忽小而恶积,求益而或击,皆昧于屈信之义以取凶耳。
案 此上三章,申吉凶效动而归于贞一之理。第三章,统论彖爻也。第四章,举彖所以取材之例。第五章,举爻所以效动之例也。盖卦有小大辞有险易,故凡卦之以阳为主,而阳道胜者,皆大卦也,以阴为主,而阴道胜者,皆小卦也,其原起于八卦之分阴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本义 诸卦刚柔之体,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门”。撰,犹事也。
集说 荀氏爽曰:阴阳相易,出于乾坤,故曰“门”。
叶氏良佩曰:此章论文王系辞之义,故首节先本伏羲卦画而言之。
何氏楷曰:有形可拟,故曰“体”,有理可推,故曰“通”。“体天地之凌’’承“刚柔有体”言,两“体”字相应,“通神明之德”,承“阴阳合德”言,两“德”字相应。
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
本义 万物虽多,无不出于阴阳之变,故卦爻之义,虽杂出而不差缪,然非上古淳质之时思虑所及也,故以为衰世之意,盖指文王与纣之时也。
集说 《九家易》曰:名,谓卦名。阴阳虽错,而卦象各有次序,不相踰越。
侯氏行果曰:《易》象考其事类,但以吉凶得失为主,则非淳古之时也,故云衰世之意耳,言“邪”,示疑不欲切指也。
《朱子语类》:问;“其称名也,杂而不越”,是指系辞而言,是指卦名而言。曰:他下面两三番说名,后又举九卦说,看来只是谓卦名。
又云:其衰世之意邪,伏羲画卦时,这般事都已有了,只是未曾经历,到文王时,世变不好,古来未曾有底事都有了,他一一经历这崎岖万变过来,所以说出那卦辞。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
本义 “而微显”,恐当作“微显而”,“开而”之“而”,亦疑有误。
集说 郭氏雍曰:当名,卦也。辨物,象也。正言,彖辞也。断辞,系之以吉凶者也。
《朱子语类》云:“微显阐幽”,‘幽”者不可见,便就这显处说出来,“显”者便就上面寻其不可见底,教人知得。又曰:如“显道神德行”相似。
又云:“微显阐幽”,是将道来事上看,言那个虽是粗的,然皆出于道义之蕴,“微显”所以“阐幽”,“阐幽”所以“微显”,只是一个物事。
吴氏澄曰:“彰往”,即“藏往”也,谓明于天之道,而彰明已往之理。“察来”,即“知来”也,谓“察于民之故”,而察知未来之事。“微显”,即“神德行”也,谓以人事之显,而本之于天道,所以微其显。“阐幽”,即显道也,谓以天道之幽,而用之于人 蔡氏清曰:人事粗迹也,《易》书有以微之,盖于至著之中,寓至微之理也,天道至幽也,《易》书有以阐之,盖以至微之理,寓于至著之象也。
案 “彰往察来”,“微显阐幽”,承首节伏羲卦画言。“当名辨物,正言断辞”,承次节文王卦名言,而因及乎辞也。“彰往察来”,即所谓“体天地之撰。”“微显阐幽”,即所谓“通神明之德”。“当名”者,即所谓“称名杂而不越”也。命名之后,又复辩卦中所具之物,以系之辞而断其占,则所谓彖也,文王因卦画而为之名辞,故曰“开而”,有画无文易道未开也。
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
本义 肆,陈也。贰,疑也。
此第六章,多阙文疑字,不可尽通,后皆放此。,集说 程氏敬承曰:理贞夫一而民贰之,有失得故“贰”也,“明失得之报”,则天下晓然归于理之一,而民行济矣,“济”者,出之陷溺之危,而措之安吉之地,此其所以为衰世之意邪。
案 “称名小取类大”,以卦名言;“旨远辞文”,以蒙辞言;“其言曲而中”,又申旨远辞文之意,旨远则多隐约,故“曲”也。辞文则有条理,故中也。其事“肆而隐”,又申名小类大之意,小名则事物毕具,故“肆”也。类大则义理包涵,故“隐”也。
总论 项氏安世曰:此章专论《易》之彖辞,《易》不过乾坤二画,乾坤即阴阳刚柔也,凡《易》之辞,其称名取类,千汇万状,大要不越于二者,而其所以系辞之意,则为世衰道微,与民同患,不得已而尽言之耳,此断辞之所以作也。断辞,即彖辞也。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本义 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于羡里而系彖辞,《易》道复兴。
集说 孔氏颖达曰:《易》之爻卦之象,则在上古伏羲之时,但其时理尚质素,直观其象,足以垂教,中古之时,事渐浇浮,非象可以为教,故爻卦之辞,起于中古,此之所论,谓《周易》也,身既忧患,须垂法以示于后,以防忧患之事。
吴氏澄曰:羲皇之《易》,有画而已,三画之卦虽有名,而六画之卦未有名,文王始名六画之卦,而系之以辞,易道几微,至此而复兴也,卦名及辞,皆前此所未有,故不云述而云作,作《易》在羡里时,故云其有忧患乎,盖于名卦而知其有忧患也,下文举九卦之名,以见其忧患之意。
谷氏家杰曰:“忧患”二字,以忧患天下言,乃吉凶同患意,民志未通,务未成,圣人切切然为天下忧患之,于是作《易》,故《易》皆处忧患之道。
何氏楷曰:圣人之“忧患”者,“忧虑”天下之迷复也,乃其处困又何“忧患”焉,是故《易》者,所以“忧患”天下之“忧患”也。
本义 履,礼也。上天下泽,定分不易,必谨乎此,然后其德有以为基而立也。谦者,自卑而尊人,又为礼者之所当执持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反身修德以处忧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复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恒者守不变而常且久,惩忿窒慾以修身,迁善改过以长善,困以自验其力,井以不变其所,然后能巽顺于理以制事变也。
集说 郑氏康成曰:辨,别也,遭闲之时,君子固穷小人则滥,德于是别也。
干氏宝曰:柄所以持物,谦所以持礼者也。
《朱子语类》:问:“巽”何以为“德之制”?曰:巽为资斧,“巽”多作断制之象,盖“巽”字之义,非顺所能尽,乃顺而能入之义,是入细直彻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如此方能断得杀,若不见得尽,如何可以行权。
陆氏九渊曰:上天下泽,尊卑之义,礼之本也,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皆本诸此。
“履德之基”,谓以行为德之基也。基,始也。德,自行而进也。不行则德何由而积,有而不居为谦,谦者不盈也,盈则其德丧矣,常执不盈之心,则德乃日积,故曰“德之柄”。既能谦,然后能复,复者阳复,为复善之义,人性本善,其不善者迁于物也,知物之为害而能自反,则知善者乃吾性之固有,循吾固有而进德,则沛然无它适矣,故曰“复德之本也”。知复则内外合矣,然而不常则其德不固,所谓虽得之必失之,故曰“恒德之固也”。君子之修德,必去其害德者,则德日进矣,故曰“损德之修也”。善日积则宽裕,故日“益德之裕也”。不临患难难处之地,未足以见其德,故曰“困德之辨也。”井以养人利物为事,君子之德亦犹是也,故曰“井德之地也”。夫然可以有为,有为者常顺时制宜,不顺时制宜者,一方一曲之士,非盛德之事也,顺时制宜,非随俗合污,如禹稷颜子是已,故曰“巽德之制也”。
陈氏琛曰:“德之基”,就积行上说;“德之本”,就心里说,要当有辨,“德之固”,是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德之地”,则全体不穷矣,亦要有辨。
卢氏曰:基与地有别,基小而地大,基是初起脚跟,积累可由此而上,地是凝成全体,施用之妙,皆由此而出也。
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
本义 此如书之九德,礼非强世,然事皆至极,“谦以自卑”,而尊且光,复阳微而不乱于群阴,恒处杂而常德不厌,损欲先难,习熟则《易》,益但充长,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动而及物,巽称物之宜而潜隐不露。
集说 韩氏伯曰:“和而不至”,从物者也,和而能至,故可履也,微而辨之,不远 程子曰:“益长裕而不设”,谓固有此理而就上充长也,“设”是撰造也,撰造则为伪也。
《朱子语类》云:“称而隐”,是巽顺恰好底道理,有隐而不能称量者,有能称量而不能隐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权”,都是此意。
陆氏九渊曰:“履和而至”,兑以柔悦承乾之刚健,故“和”。天在上,泽处下,理之至极不可易,故“至”。君子所行,体履之义,故“和而至”。“谦尊而光”,不谦则必自尊自耀,自尊则人必贱之,自耀则德丧,能谦则自卑自晦,自卑则人尊之,自晦则德益光显,“复小而辨于物”,复贵不远,言动之微,念虑之隐,必察其为物所诱与否,不辨于小,则将致悔咎矣。“恒杂而不厌”,人之生,动用酬酢,事变非一,人情于此多至厌倦,是不恒其德者也。能恒者虽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人情逆之则难,顺之则《易》,凡抑损其过必逆乎情,故“先难。”既损抑以归于善,则顺乎本心,故“后《易》”。“益长裕而不设”,益者迁善以益己之德,故其德长进而宽裕。设者,侈张也。
有侈大不诚实之意,如是则非所以为益也。“困穷而通”,不修德者,遇穷困则陨获丧亡而已,君子遇穷困则德益进,道益通。井居其所而迁,如君子不以道徇人,故曰“居其所”。而情施济众,无有不及,故曰迁巽。“称而隐”,巽顺于理,故动称宜,其所以称宜者,非有形迹可见,故“隐”。
案 “复小而辨于物”,陆氏盖用韩氏之说,与朱子异,然朱子之义为精。
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
本义 寡怨,谓少所怨尤。辨义,谓安而能虑。
此第七章,三陈九卦,以明处忧患之道。
集说 虞氏翻曰:礼和为贵,故“以和行”也,有不善朱尝不知,故“自知”也,恒立不《易》方,故“一德”也。
欧阳氏修曰:君子者天下係焉,一身之损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损,忿欲耳,自益,迁善而改过耳,然而到其忿欲者,岂止一身之损哉,天下有被其害矣,迁善而改过,岂止一身之益哉,天下有蒙其利矣。
《朱子语类》:问:“巽以行权”,“权”是逶迤曲折以顺理否?曰:然。“巽”有人之义,巽为风,如风之人物,只为巽便能人,义理之中,无细不入,又问“巽称而隐”,隐亦是人物否。曰:“隐”便是不见处。
又云:见得道理精熟后,于物之精微委曲处,无处不入,所以说“巽以行权”。
又云:“兑见而巽伏”,“权”是隐然作底事物,若显然地作,却不成行权。
陆氏九渊曰:“履以和行”,行有不和,以不由礼故也,能由礼,则和矣。“谦以制礼”,自尊大则不能由礼,卑以自牧,乃能自节制以礼。“复以自知”,自克乃能复善, 王氏应麟曰:“复以自知”,必自知然后见天地之心,“有不善未尝不知”,自知之明也。
何氏揩曰:以,用也。履者,礼也。用礼以约之,而制作始和,此履所以为“德之基”也,所贵乎礼者以其为德之品节也,然唯让为礼之实,不让不为礼,故用“谦以制之”,此谦所以为“德之柄”也。
总论 项氏安世曰:此章亦论彖辞,凡彖辞之体,皆先释卦名,次言两卦之体,末推卦用,故此章之序亦然,以为观彖者之法也。
胡氏炳文曰;上经自《乾》至《履》九卦,下经自《恒》至《损》、《益》亦九卦,上经《履》至《谦》五卦,下经《益》至《困》、《井》亦五卦。
上经《谦》至《复》又九卦,下经《井》至《巽》又九卦,上经自《复》,而后八卦而为下经之《恒》,下经自《巽》而《未济》,亦八卦《复》为上经之《乾》,上下经对待,非偶然者。
叶氏良佩曰:此章二陈九卦,专言卦也,《易》道屡迁一章,专言爻也。
案 此上二章,申象之动乎内,而吉凶见乎外也。六十四卦之象,皆以乾坤交错而成,中涵天地变化之道,鬼神微妙之德,是所谓“动乎内者”也,及圣人命之以名,系之以辞,于是吉凶之义昭然见矣。六十四卦之名,或曰伏羲所命,或曰文王所命,盖自夫子之时而已疑也,但以其所取事类观之,知其非上古淳质时所有,则为文王命名,可以理推,“名当”,则卦爻之物可辨,因“正言”其是非,而吉凶之辞可断,向之“体天地之撰”,而有以“彰往察来”,“通神明之德”,而有以“微显阐幽”者,至是而大备矣,“名杂而不越”,故所称者小而义则大,彖所以发其蕴也,故寓意深远而辞则文,指远辞文,故言虽“曲而中”,名小类大,故事虽“肆而隐”,盖由于世衰民疑,而将以济其行,故非探赜索隐,无以尽其变也,非周事体物,无以恬其心也,夫吉凶者失得之报而已矣,故下九卦遂言圣人之所处,以示观彖之例。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本义 远,犹忘也。周流六虚:谓阴阳流行于卦之六位。
百五十四赞当昼,三百五十四赞当夜,昼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轻重,凶之中又自分轻重,《易》却不然,有阳居阳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阴居阴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有应而吉底,有有应而凶底,是“不可为典要”之书也,是有那许多变,所以如此。
蔡氏渊曰:屡迁,谓为道变通而不滞乎物,自“《易》之为书”至“屡迁”,此总言为书为道,以起下文之意也。自“变动不居”至“唯变所适”,言《易》道之屡迁也。
不居,犹不止也。六虚,六位也。位未有爻曰“虚”,卦虽六位,而刚柔爻画往来如寄,故以“虚”言。或自上而降,或由下而升,上下无常也,柔来文刚,分刚上而文柔,刚柔相《易》也。典,常也。要,约也。其屡变无常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而已。
吴氏曰慎曰:“不可为典要”,变无方也,既有典常,理有定也,故曰《易》者变:《易》也,不《易》也。
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
本义 此句未详,疑有脱误。
集说 韩氏伯曰:明出入之度,使物知外内之戒也。
潘氏梦旂曰:《易》虽“不可为典要”,而其出入往来,皆有法度,而非妄动也,故卦之外内,皆足以使人知惧。
蔡氏清曰:卦爻所说者,皆利用出入之事,其出入也,皆必以其法。法者,事理当然之则也,使人人而在内,出而在外,皆知有法而不敢妄为,是使知惧也,知惧必以度。
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
本义 虽无师保,而常若父母临之,戒惧之至。
集说 虞氏翻曰:“神以知来”,故明忧患,“知以藏往”,故知事故。
苏氏轼曰:忧患之来,苟不明其故,则人有苟免之志而怠,故易明忧患,又明其所以致之之故。
朱氏震曰:又明于己之所当忧患,与所以致忧患之故,无有师保教训而严惮之,有如父母亲临而爱敬之,见圣人之情也。
赵氏振芳曰:不特使人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所以致忧患之故,谆谆然与民同患,与民同忧,不止如师保之提命,且直如父母之俨临行,故不虚行也。
孔氏颖达曰:虽千变万化,“不可为典要”,然循其辞,度其义,原寻其初,要结其终,皆“唯变所适!”是其常典也。
邵子曰:既有典常,常也,不可为典要,变也。
总论 项氏安世曰:此章专论《易》之爻辞,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二句,一章大指,自“变动不居’至“唯变所适”,言“屡迁”也,爱之无所不至,虑之无所不周,故训之无所不切也。
案 “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朱氏赵氏之说甚善,盖上文言“出入以度”,则人知畏惧,严惮之如师保,及观其示人忧患之故,恳切周尽,使闻之者,不知严惮而但感其慈爱,此圣人之情,所以为至也。无有者,非无师保也,人之意中,“无有师保”也。
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本义 方,道也。始由辞以度其理,则见其有典常矣,然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也。
此第八章。
集说 虞氏翻曰:“其出入有度”,故“有典常”,“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谓之德自“出入以度”至“道不虚行”,言“不可远”也,唯其屡迁,故虚而无常,“不可为典要”,唯其不可远,故有度有方有典有常,而不可虚,方其率之也,则谓之辞,及其行之也,则谓之道,辞之所指,即道之所迁也,人能循其不可远之理,则屡迁之道得矣。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
本义 质谓卦体,卦必举其始终而后成体,爻则唯其时物而已。
集说 韩氏伯曰:质,体也。卦兼始终之义也。
孔氏颖达曰:物,事也。一卦之中,六爻交相杂错,唯各会其时,各主其事。
吴氏澄曰:质谓卦之体质,文王原卦义之始,要卦义之终,以为卦之体质,各名其卦而系彖辞也,爻之为言交也,周公观六位之交错,唯其六爻之时,各因其义而系爻辞也,此章言六爻,而六爻统于彖,故先言彖,乃说六爻也。
谷氏家杰曰:此章虽兼卦爻,实以卦引起爻,专重在爻上。
何氏楷曰:此章统论爻画,而归重于彖辞,说《易》之法,莫备于此,《易》之为书纲纪在卦,卦必合爻之全而后成卦,一画不似,便成他局,圣人之系卦为之推原其始,要约其终,弥纶全卦之理,如物之有体质,至于系爻,则唯相其六位之时而导之宜,因其阴阳之物而立之像,然其大指,要不过推演彖辞之意。
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
本义 此言初上二爻。
集说 干氏宝曰:初拟议之故难知,卒终成之,故易知,本来势然也。
孔氏颖达曰:“初辞拟之”者,复释“其韧难知”也,以初时拟议其始,故“难知”也,“卒成之终”者,复释“其上易知”也,言“上”是事之卒了,而成就终竞,故“易 吴氏澄曰:“初”与“终”为对,“拟之”与“卒成之”为对,两句文法,颠倒相互。
案 讲家以难知易知属学《易》者,“拟之”“卒成”属作《易》者,然圣人作易六爻之条理,挥成于心,岂有难易哉,故“初辞拟之”“卒成之终”两句,是申上两句,皆当属学《易》者说。
若夹杂物撰德,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
本义 此谓卦中四爻。
案 “杂”字“撰”字“辨”字,亦当属学《易》者。说“杂”者,参错其贵贱上下之位也。撰者,体察其则柔健颗之德也,德位分而是非判矣。辨者,剖别之于象,以考验之于辞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本义 彖统论一卦六爻之体。
集说 苏氏轼曰:彖者,常论其用事之爻,故观其彖,则其余皆彖爻之所用者也。
吴氏澄曰:章首第一句言彖,第二句总言六爻,此一节又总言六爻而归重于彖,盖为结语与章首起语相始终。
案 彖辞之系,文王盖统观六爻以立义者,如《屯》则以初为侯,《蒙》则以二为师,《师》则以二为将,《比》则以五为君,其义皆先定于彖,爻辞不过因之而随爻细别耳,其爻之合于卦义者吉,不合于卦义者凶,故彖辞为纲领,而爻其目也,彖辞为权衡,而爻其物也,总之于纲,则目之先后可知,审之于权衡,则物之轻重可见,夫子彖传,既参错六爻之义以释辞,示人卦爻之不相离矣,于此又特指其要而切言之,读《易》之法,莫先于此。
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本义 此以下论中爻,同功,谓皆阴位。异位,谓远近不同,四近君,故“多惧”,柔不利远,而“二多誉”者,以其“柔中”也。
集说 崔氏憬曰:此重释中四爻功位所宜也,二四皆阴位,阴之为道,近比承阳,故“不利远”矣,二远阳虽则不利,其要或有无咎者,以柔居中,异于四也。
苏氏轼曰:近于五也,有善之名,而近于君则惧矣,故二之善宜著,四之善宜隐。
程氏迥曰:《易》以六居五,以九居二,为卦十有六,虽为时不同,其十有五皆吉,谓人君柔中虚己,而任刚德之臣,其臣亦以刚中应之也。
吴氏澄曰:二与四同是阴位,若皆以柔居之,则六二六四,同是以柔居阴,故曰“同功”。然其位则有远近之异,五者一卦之尊位,故远近皆自五而言,二与五应为远,四与五比为近,以位之远近有异,而其善亦不同,远者意气舒展而多誉,近者势分逼迫而多惧,多者,谓不尽然而若此者众尔,“近也”二字,释“四多惧”,谓四之所以惧,不 何氏楷曰:月远日则光满,近则光微,此“多誉”、“多惧”之说也。
案 吴氏说亦详密,但以二之誉,四之惧,专为以柔居柔者,三之凶,五之功,专为以刚居刚者,则于经意犹偏,盖圣人之言举其一隅,则可以三隅反,“多誉”“多惧”,以二四之位言,不论刚柔居之,皆“多誉”“多惧”也,多凶多功,以三五之位言,亦不论刚柔居之,皆多凶多功也。下文言“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则可见二虽多誉,而九二尤善于六二,四既多惧,而九四尤甚于六四也,又言“其柔危其刚胜邪”,则可见三虽多凶,而九三犹善于六三,五虽多功,而六五犹让于九五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为六二言,而九二在其中,并六四、九四皆在其中,其柔危,为六三言,而九三在其中,并六五、九五亦在其中,此圣言之所以妙。
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
本义 三五同阳位,而贵贱不同,然以柔居之则危,唯刚则能胜之。
此第九章。
集说 侯氏行果曰:三五阳位,阴柔处之,则多凶危,则正居之,则胜其任,言“邪”者不定之辞也,或有柔居而吉者,得其时也。
崔氏憬曰:三处下卦之极,居上卦之下,而上承天子,若无含章之美,则必致凶,五既居中不偏,贵乘天位,以道济物,广被寰中,故“多功”也。
吴氏澄曰:三与五同是阳位,若皆以刚居之,则九三九五,同是以刚后阳,故曰“同功”,然其位则有贵贱之异,贱者,刚居刚为太过而多凶;贵者,刚居刚为适宜而多功。
“二多誉”“四多惧”之上,有“其善不同”一句,而“三多凶五多功”之上无之者,誉惧虽不同,而皆可谓之善,凶则不可谓善矣,故不言也。“贵贱之等也”五字,释“三多凶”,谓三之所以凶,不能如五之功者,盖贵贱有等,贱者不与贵者同故也。“其柔危”以下,释“五多功”,五为尊位,以柔居之,则不胜其任而危,惟刚居之,则能胜其任而有功也。
胡氏炳文曰:其柔危,其刚胜,专为三言也。
蔡氏清曰:或远或近,或贵或贱,此所谓“爻有等,故曰物者”,是为杂物,或柔中,或不中,或多誉,或多惧,或多凶,或多功,又或柔危而刚胜,此所谓撰德也。而“辨是与非”,举具其中矣。
案 柔危刚胜,吴氏以为指五,胡氏以为指三,侯氏兼之,须分别融会,乃得经意。
总论 何氏楷曰:章末复举中爻,所以略初上不言者,盖初上非用事之地,故所重在时位,中四爻用事之地,故唯重在德行也。若夫卦主在初上者,则不可以此例论,此章为《易》之凡例,求卦爻之义者,执此以求之而已,然仅曰要曰多曰过半,则虽圣人 案 此上二章,中爻之动乎内,而吉凶见乎外也,道屡迁者,于“周流六虚”见之,无常相易,所谓“周流”者也,“唯变所适”,所谓“屡迁”者也,此则爻之动乎内者,及系辞而吉凶见,则使人于日用出入之间,各循乎法度而知惧,盖凛乎师保之严矣,再观其开示人以忧患,与其所以至忧患之故,不啻父母之谋其子孙者,又使人无有师保之严,但如临父母之亲而已,夫是以由其辞而揆之,则不可为典要者,未尝不有典常,而欲体其道而行之,则所谓不可远者,又存乎其人之不远于道也,下文遂以辞之典常言之,大约初上虽无位,而为事之始终,自二至五,则居中而正,为用事之位,玩辞者,拟其初,竟其终,参合其物理,以辨其是非而求其备,此学《易》之法也,然彖者括始终以立体,而爻则其趋时之物而已,故知者观彖辞而爻义已大半得,此又学《易》之要也,又举中四爻而申之,以见凡当位用事,则有誉有惧,有凶有功,非初上无位而或在功过之外者比也,圣人所谓明忧患与故者,于此尤谆谆焉。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本义 三画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而以上二爻为天,中二爻为人,下二爻为地。
集说 项氏安世曰:言圣人所以兼三才而两之者,非以私意傅会三才之道,自各有两,不得而不六也。
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
本义 道有变动,谓卦之一体。等,谓远近贵贱之差。相杂,谓刚柔之位相间,不当,谓爻不当位。
此第十章。
集说 陆氏绩曰:天道有昼夜日月之变,地道有刚柔燥湿之变,人道有行止动静吉凶善恶之变,圣人设爻以效三才之变动,故谓之爻者也。
孔氏颖达曰:三才之道,既有变化移动,故重画以象之,而曰爻也。物者,物类也。
爻有阴阳贵贱等级,以象万物之类,故谓之物也。若相与聚居,间杂成文,不相妨害,则吉凶不生,由文之不当相与聚居,不当于理,故吉凶生也。
张子曰:故曰爻,爻者交杂之义。
项氏安世曰:“爻有等”者,初二三四五上也。‘物相杂”者,初三五与二四上,阴阳相同也。“文不当”者,九居阴位,六居阳位也。
李氏筒曰:一则无变无动,兼而两之,故三才之道,皆有变动,以其道有变动,故名其画口爻。爻者,效也,言六画能效天下之动也。爻有贵贱上下之等,故曰物。物有九六杂居刚柔之位,则成文,交错之际,有当不当,吉凶由是生焉。
汪氏咸池曰:文既相杂,岂能皆当,故有以刚居柔,以柔居刚,而位不当者,亦有 何氏楷曰:不当者非专指阳居阴位,阴居阳位也,卦情若淑,或以不当为吉,卦情若慝,反以当位为凶,要在随时变易得其当而已。
吴氏曰慎曰:以时义之得为当,时义之失为不当,不以位论。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本义 危惧故得平安,慢易则州顷覆,易之道也。
此第十一章。
集说 张氏拭曰:既惧其始,使人防微杜渐,又惧其终,使人持盈守成,要之以无咎而补过,乃易之道也。
高氏攀龙曰:一部《易》原始要终,只是敬惧无咎而已,故曰“惧以终始”。“无咎者,善补过也”,《易》中凡说有喜有庆吉元吉,都是及于物处,若本等只到了无咎便好。
赵氏光大曰:“危者使平”二句,即是辞危处,使之不可作《易》使之,言由危而平者,危使之也,言其理之必然,若有以使之也,《易》之道,与“其道甚大”“道”字正相应。
何氏楷曰:使者,天理之自然,若或使之也,所谓殖有礼,覆昏暴,天之道也。
案 此上二章,申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也。所谓变者,生于三才之道,以两而行,交合相济,迭用不穷也,写之于易,则以其两相交也,而名为爻。所处之位不同也。而名为物,所以处是位者,又相错也。而名为文,相错则有当有否,而吉凶于此生,大业于此起矣,故曰“功,业见乎变”。虽然,上古之圣,以是济民用焉,而辞未备也,文王当殷商之衰,忘己之忧,而唯世之患,是故其因事设戒者,无非欲人战战兢兢,免于咎而趋于平也,是所谓以身立教,反覆一编之中,千载之上心如见焉,故曰“圣人之情见乎辞”。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
本义 至健则所行无难,故易。至顺则所行不繁,故简。然其于事,皆有以知其难,而不敢易以处之,是以其有忧患,则健者如自高临下,而知其险,顺者如自下趋上,而知其阻,盖虽易而能知险,则不陷不险矣,既简而又知阻,则不困于阻矣,所以能危能惧,而无易昔之倾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乾之德行恒易略,不有艰难以此之故,能知险之所兴,若不易则为险,故行易以知险也,坤之德行恒为简静,不有繁乱以此之故,知阻之所兴,若不简则为阻难,故行简以知阻也。
苏氏轼曰:已险而能知险,已阻而能知阻者,天下未尝有也,是故处下以倾高,则 上,为上所阻,故不敢进。
项氏安世曰:“易”与“险”相反,唯中心易直者能照天下险巇之情,简与阻相反,唯行事简静者,能察天下繁壅之机。
李氏简曰:两险相疑,两阻相持,则险不能知险,知天下之至险者,至易者也,阻不能知阻,知天下之至阻者,至简者也。
胡氏炳文曰:前言乾坤之易简,此言乾坤之所以为易简,盖乾之德行,所以恒易者,何也?乾,天下之至健也,坤之德行,所以恒简者。何也?坤,天下之至顺也。
蔡氏清曰:天下之至健,天下之至顺,犹《中庸》云“天下至诚”、“天下至圣”相似,皆以人言,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此天下之至健者也,安贞之吉,“应地无疆”,此天下之至顺者也。
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本义 “侯之”二字衍,“说诸心”者,心与理会,乾之事也。“研诸虑”者,理因虑审,坤之事也。“说诸心”,故有以定吉凶;“研诸虑”,故有以成亹亹。
集说 张子曰:易简故能说诸心,知险阻故能研诸虑。
朱氏震曰:简易者我心之所固有,反而得之,能无说乎,以我所有,虑其不然,能无研乎。
《朱子语类》云:能说诸心,能研诸虑,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凡事见得通透了,自然欢说,既说诸心,是理会得了,于事上更审一审,便是研诸虑,研是吏去研磨,定天下之吉凶,是剖判得这事,成天下之亹亹,是作得这事业。
张氏拭曰:心之说也,不忤子理,虑之研也,不昧于事,则得者为吉,失者为凶,吉凶既定,则凡勉于事功者,莫不弘之不息以成其功矣。
谷氏家杰曰;能说诸心,能研诸虑,二能字应下成能之能,见此理人人具有,唯圣人能说能研耳。
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
本义 “变化云为”,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可以知来。
集说 苏氏轼曰:言易简者无不知也。
《朱子语类》:问:有许多“变化云为”,又吉事皆有休祥之应,所以象事者于此而知器,占事者于此而知来。曰:是。
何氏楷曰:凡人事之与吉逢者,其先必有祥兆,天人相感,志一之动气也,圣人作《易》,正以迪人于吉,故独以吉事言之,与吉之先见同义。
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
集说 《朱子语类》云:“天地设位”四句,说天人合处,“天地设位”,使圣人成其功能,“人谋鬼谋”,则虽百姓亦可与其能,成能与与能,虽大小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
胡氏炳文曰:圣人成天地所不能成之能,百姓得以与圣人所已成之能也。
蔡氏清曰:凡卜筮问《易》者,先须谋诸人,然后乃可问《易》,虽圣人亦然,故《洪范》曰:“谋及卿士,谋及庶人,然后曰谋及卜筮。”又曰:“联志先定,询谋佥同,然后鬼神其依,龟筮协从是也。”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
本义 象,谓卦画。爻彖,谓卦爻辞。
集说 崔氏憬曰:伏羲始画八卦,因而重之,以备万物而告于人也。爻,谓爻下辞。
象,谓卦下辞。皆是圣人之情,见乎系辞,而假爻象以言,坟曰“爻彖以情言”,六爻刚柔相推,而物杂居,得理则吉,失理刚凶,故“吉凶可见”也。
蔡氏清曰:八卦以象告,则刚柔杂居矣,爻彖以情言,则吉凶可见矣。
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
本义 不相得,谓相恶也,凶害悔吝,皆由此生。
集说 崔氏憬曰:远,谓应与不应。近,谓比与不比,或取远应而舍近比,或取近比而舍远应,由此远近相取,所以生悔吝于系辞矣。
项氏安世曰:“爱恶相攻”以下,皆言“吉凶以情迁”之事,而以六爻之情与辞明之,吉凶悔吝利害之三辞,分出于相攻相取相感之三悄,而总属于相近之一情,此四者,爻之情也。命辞之法,必各象其爻之情,故观其辞可以知其情。利害者,商略其事有利有不利也,悔吝则有迹矣,吉凶则其成也,故总而名之曰吉凶。“相感”者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则有事矣,故以悔吝言之。“相攻”则其事极矣,故以吉凶言之。
爱恶远近情伪,姑就浅深分之,若错面综之,则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远近,其行皆有情伪,其情皆有爱恶也,故总以相近一条明之。“近而不相得”,则以恶相攻而凶生矣,以伪相感而害生矣,不以近相取而悔吝生矣,是则一近之中,备此三条也。凡爻有比爻,有应爻,有一卦之主爻,皆情之当相得者也,今称近者,正据比爻言之,反以三隅,则远而为应为主者,亦必备此三条矣,但居之近者,其吉凶尤多,故圣人概以近者明之。
吴氏澄曰:害者利之反,凡占曰不利无攸利者害也,近而不相得,则凶害悔吝,其相得,则吉利悔亡无悔无咎从可知也。
胡氏一桂曰:“凡《易》之情”以下,独举近者总言之,近而相取,其情乃不相得, 蔡氏清曰:“爱恶相攻”三句平等说,下文却合言之曰:大抵凡《易》之情,近而相得者为贵,不相得而远者亦无害,唯是近而不相得者则凶,又有害而悔且吝矣。
又曰:“吉凶悔吝利害”六字,大抵吉凶重于利害,利害重于悔吝,故末句先凶次害,又次悔吝,而凡曰吉凶见乎外,吉凶以情迁则皆该利害与悔吝矣。
林氏希元曰:“近而不相得”,是解“远近相取而悔吝生”一句,并“爱恶相攻”两句亦解。盖远近相取而悔吝生,这里分情相得不相得。情相得者,远相取而悔吝。情不相得者,近相取而悔吝,但此意未明,故于此发之,只曰近不曰远者,举近则远者可以三隅反也,夫近而不相得则凶,可见恶相攻而凶生者,以其近也,伪相感而害生者,亦以其近也,故曰是并解“爱恶相攻”两句。
案 此条诸说相参,极详密矣,然尚有须补备者,诸说皆以近为相比之爻,于《易》例未尽,应爻虽远,然既谓之应,地虽远而情则近也。先儒盖因上章“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故必以相比为近,然彼就二四而言之,则有远近之别,此就六爻而统论之,则比与应皆近也,观《蒙》之六四曰“独远实也”,以其比应皆阴也,如虽无比面有应,亦不得谓之远实矣,故《易》于应爻,有曰婚媾者,有曰宗者,有曰主者,有曰类者,皆亲近之称也。“远近相取”,须分无比应者为远,有比应者为近,乃为完备。
《易》之情,其有远近者,固从爻位而生,若爱恶情伪,则从何处生来,须知《易》爻吉凶,皆在“时”、“位”、“德”三字上取,时随卦义而变,时变,则有爱恶矣,如《泰》之时则交,《否》之时则隔,《比》之时则和,《讼》之时则争,是“爱恶相攻”者,由于时也。位逐六爻而异,位异则有远近矣,如《比》之内比外比,《观》之观光者,近也;《蒙》之困蒙,《复》之迷复者,远也,是远近相取者,由于位也。德由刚柔当否而别,德别则有情伪矣,如《同人》五之号咷,《豫》二之介石,以中正也,《同人》三之伏戎,《豫》三之盱豫,以不中正也,是情伪相感者,由于德也。时有消息盈虚之变,位有贵贱上下之异,德有刚柔善恶之别,此三者皆吉凶悔吝之根,然其发动,皆因彼己之交而起。所谓彼己之交者,比也,应也,非因比应,则无所谓相攻也,无所谓相取也,无所谓相感也。所谓相攻相取相感者,皆以比应言之,放下独举近而不相得以见例,近而相得,相爱者也,相取者也,以情相感者也,善之善者也,不相得者而远,则虽恶而不能相攻也,不近而不得相取也,虽伪而不与相感也,善之次也,宜相得者而远,则虽爱而不得相亲也,不近而不能相取也,虽有惰而无以相感也,又其次也,唯近而不相得,则以恶相攻,以近相取,以伪相感,人事之险阻备矣,大者则凶,极其恶之情者也,《同人》三之敌刚是也,次者则害,防其伪之端者也,《兑》之介疾孚剥是也,轻者犹不免于悔吝,如《豫》、《萃》之三,虽以近而从四,然以非同类而曰悔曰吝者此也,《易》者教人知险知阻,故特举此条以见例,余者可以三隅反也,故观《易》者,须先知时、位、德、比、应五字,又须知时、位、德之当否,皆于比应上发动,其义莫备于此章矣。
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 本义 卦爻之辞,亦犹是也。
此第十二章集说 王氏申子曰:歉于中者必愧于外,故“将叛者其辞惭”,疑于中者必泛其说,故“中心疑者其辞枝。 ”吉德之人见理直,故其“辞寡。 ”躁竞之人急于售,故其“辞多”。
诬善类者,必深匿其迹而阴寓其忮,故其“辞游”。“失其守”者,必见义不明而内无所主,故“其辞屈”。
吴氏澄曰:此篇之道,泛言辞变象占四道,而末句归重于辞,巳以本于圣人之情,至于卒章凡二节,其中亦言四道,而首末皆言彖爻之辞,末又本于《易》之情,以终系辞之传,盖唯圣人之情,能知《易》之情而系易之辞也,是为一篇始终之脉络云。
张氏振渊曰:此节即人之辞以情迁者,验《易》之辞以情迁也。
案 此章亦总上卜一章之意而通论之,易简即上下传首章所谓乾坤之理,而圣人体之以立极者,故此即以乾坤为圣人之名称,见《易》道之本,圣心所自具也,《易》与险反,故“知险”,简与阻反,故“知阻”,以是说诸心,即以是研渚虑,凡天下所谓吉凶亹亹者,固已豫定取成于圣人之心矣,于是仰观变化俯察云为,“知以藏往”而通其象,“神以知来”而裕其占,此所以作《易》而天地之功以成,百姓之行以济也,“爻象动乎内”者以象告,“吉凶见乎外”者以情言,“功业见乎变者”以利言,“圣人之情见乎辞”者以情迁,时有顺逆而爱恶生焉,位有离合而远近判焉,德有淑慝而情伪起焉,此三者《易》之情也,吉利凶害悔吝之辞。所由兴也,在《易》则为《易》之惰,圣人从而发挥之,则吉凶之途明,而利害之几审,此即圣人之情也,故言凡人之情著于辞而不可掩者六,反切上章所谓有忧患者辞危也。
文言传本义 此篇申《彖传》、《象传》之意,以尽乾坤二卦之蕴,而余卦之说,因可以例推云。
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
本义 “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故于时为春,于人则为仁,而众善之长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于此,莫不嘉美,故于时为夏,于人则为礼,而众美之会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于时为秋,于人则为义,而得其分之和。“贞”者,生物之成,实理具备,随在各足,故于时为冬,于人则为智,而为众事之干,于,木之身,而枝叶所依以立者也。
程传 它卦,《彖》、《象》而已,独乾坤更设《文言》以发明其义,推乾之道施于人事,“元亨利贞”,乾之四德,在人则“元”者,众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会也;“利”者,和合于义也,“贞”者,干事之用也。
集说 《朱子语类》:问:“元者善之长。”曰:“元亨利贞”皆善也,而“元”乃为四者之长,是善端初发见处也。
问“亨者嘉之会”。曰:且以草木言之,发生到夏时,好处都来凑会。嘉,只是好处。会,是期会也 。
又云:“利者义之和”,“义”。疑于不和矣,然处之而各得其所,则和,“义之和”处便是利。
问程子曰:义安处便为利,只是当然便安否。曰:是。正好去解利者义之和句,义截然而不可犯,似不和,分别后万物各止其所,却是和,不和生于不义,义则无不和,和则无不利矣。
义云:“贞者事之干”,知是那默运事变底一件物事,所以为“事之干”。
又云:正字不能尽贞之义,须用连正固说,其义方全,正如孟子所谓“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斯”是正意,“弗去”是固意。干问又有所谓不可贞者是如何。曰:也是这意思,只是不可以为正而固守之。
项氏安世曰:善也嘉也义也,皆善之异名也,在事之初为善,善之众盛为嘉,众得其宜为义,义所成立为事,此一理而四名也,故分而为四,则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比而为二,则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混而为一,则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义之和,和, 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
本义 以仁为体,则无一物不在所爱之中,故“足以长人”,嘉其所会,则无不合礼,使物各得其所利,则义无不和,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谓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为事之干。
程传 体法于乾之仁,乃为君长之道,足以长人也。体仁,体元也,比而效之谓之体,得会通之嘉,乃合于礼也,不合礼则非理,岂得为嘉,非理安有亨乎,和于义乃能利物,岂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贞固所以能干事也。
集说 李氏鼎祚曰:天运四时以生成万物,君法五常以教化于人,元为善长,故能体仁,仁主春生,东方木也。通为嘉会,足以合礼,礼主夏养,南方火也。利为物宜,足以和义,义主秋成,西方金也。贞为事干,以配于智,智主冬藏,北方水也。不言信者,信主土,土居中宫,分王四季,水火金木,非土不载。
《朱子语类》云:体仁,不是将仁来为我之体,我之体便都是仁也。又曰:《本义》云,以仁为体者,犹言自家一个身体,元来都是仁。
又云:嘉,美也。会,是集齐底意思,许多嘉美,一时斗凑到此,故谓之嘉会,嘉其所会,便动容周旋无不中礼。
又云:看来义之为义,只是一个宜,其初则甚严,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直是有内外之辨,君尊于上,臣恭于下,尊卑大小,截然不可犯,似若不和之甚,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则其和也,孰大于是。
又云:干如木之干,事如木之枝叶,贞固者,正而固守之,贞固在事,是与立个骨子,所以为事之干,欲为事而非此之贞固,便植立不起,自然倒了。问“贞固”二字与体仁嘉会利物似不同。曰:属北方者,便著用两字,方能尽之。
问《文言》四德一段。曰:“元者善之长”以下四句,说天德之自然,“君子体仁足以长人”以下四句,说人事之当然,元是善之长,万物生理,皆始于此,众善百行,皆统于此,故于时为春,于人为仁,亨是嘉之会。嘉,美也。会,犹齐也。盖春方生育,至此乃无一物不畅茂,其在人则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事事物物,一齐到恰好处。所谓动容周旋皆中礼,故于时为夏,于人为礼。“利者义之和”,万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无不得宜,故于时为秋,于人为义。“贞者事之于”,万物至此收敛成实,事理至此无不的正,故于时为冬,于人为智。此天德之自然,其在君子所当从事于此者,体者,以仁为体,仁为我之骨,我以之为体,仁皆从我发出,故无物不在所爱,所以能长人,欲其所会之美,当美其所会,盖其厚薄亲疏尊卑小大相接之体,各有节文,无不中节,即所会皆美,所以能合于礼也,能使事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自无乖戾而各得其分之和,知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云,故足以为事之干。干,如版筑之有桢干。
胡氏炳文曰:体仁有以存诸中。嘉会则美见乎外,利物有以方乎外,而贞固有以守于中,礼者仁之著,智者义之藏,体仁长人,贞固干事,山理以及用,嘉会合礼,利物 董氏真卿曰:朱子谓属北方者便著用两字,方能尽之,幼时闻先君子之言曰:北方天气之终始,有分别之义,故北字篆文,两人相背,至于四端五脏四兽,属北方者皆两,东西南三方者各一,四时为冬,亦与春为交接,四德:勾贞,亦贞下起元,十二辰为亥子,六十四卦为《坤》、《复》。
林氏希元曰:君子克己复礼,使亡:充乎中而见乎外,中之所有,无一念之非仁,外之所行,无一事之非仁,则君子之身,浑是一个仁,非体其体而体夫仁也,体仁,仁之至也,故无一物不在所爱之中,而足以长人,安土敦厂故能爱,正是如此。
又曰:“利者义之和”之“利”,乃在人天然之利,“利物足以和义”之“利”,乃人所以求乎天然之利也,义之和之和,乃在人天然之和,足以和义之和,乃人所以求乎天然之和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本义 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贞”。
此第一节,申《彖传》之意,与《春秋传》所载穆姜之言不异,疑古者已有此语,穆姜称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故下文别以子曰:表孔子之辞,盖传者欲以明此章之为古语也。
程传 行此四德乃合于乾也。
集说 《朱子语类》:问:“乾元亨利贞”,犹言性仁义礼智。曰:此语甚稳当。又曰:“乾元亨利贞”,它把“乾”字当君子。
蔡氏清曰:“元亨利贞”四字,在文王只为占辞,至孔子《彖传》,乃有四德之说,然其所谓四德者,又有不同,天之四德,自其生成万物者言也,圣人之四德,自其统治一世者言也,至此所谓四德,又只就君子一身所行而言也,一身所行者其体也,统治一世者其用也,四德无乎不在也,又见乾字所该者广也。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本义 龙德,圣人之德也,在下故隐,易,谓变其所守,大抵乾卦六爻,《文言》皆以圣人明之,有隐显而无浅深也。
程传 自此以下言乾之用,用九之道也,初九阳之微,“龙德”之潜隐,乃圣贤之在侧陋也,守其道,不随世而变,晦其行,不求知于时,自信自乐,见可而动,知难而避,其守坚不可夺潜龙之德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心以为乐,己则行之,心以为忧,己则违之,身虽逐物推移,心志守道,确乎坚实其不可拔。
游氏酢曰:“龙德而隐”,故“不易乎世”,“不易乎世”者,用舍在我,故“遯世无 吴氏澄曰:“乐则行之”,释上文“无闷”二句。“忧则违之”,释上文“不易”“不成”二句。乐者,谓无闷也。行之,谓为之也。忧者,谓非其所乐也。违之,谓不为也。
不求见于世,不求知于人者,此其所乐也,则为之,易乎世成乎名者,此非其所乐也,则不为。
蒋氏悌生曰:行道而济时者,圣人之本心,故曰“乐则行之”,不用而隐遯者,非圣人所愿欲也,故曰“忧则违之”。虽然其进其退莫不求至理之所在,未尝枉道以徇人也,故曰“确乎其不可拔。”蔡氏清曰:“遯世无闷”二句,尤重于“不易乎世”二句,“乐则行之”三句,更重于“遯世无闷”二句,此三句明其无意必也,论龙德之隐,必至是而后尽。
案 吴氏蒋氏两说不同,而皆可通。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言,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本义 正中,不潜而未跃之时也,常言亦信,常行亦谨,盛德之至也,闲邪存其诚,无斁亦保之意,言君德也者,释“大人”之为九二也。
程传 以龙德而处正中者也,在卦之正中,为得正中之义,庸信庸谨,造次必于是也,既处无过之地,则唯在闲邪,邪既闲,则诚存矣,“善世而不伐”,不有其善也,“德博而化”,正已而物正也,皆大人之事,虽非君位,君之德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庸,常也,常言之信实,常行之谨慎,防闲邪恶,自存诚实,为善于世,而不自伐其功,德能广博,而变化于世俗,初爻则全隐遯避世,二爻则渐见德行以化于俗也。
《朱子语类》云:“庸言”“庸行”,盛德之至,到这里犹自闲邪存诚,便是无射亦保,虽无厌致,亦当保也,保者持守之意。
又云;“‘利见大人’,君德也”,两处说“君德”,却是要发明“大人”即是九二。
陆氏九渊曰:言行之信谨,二之所以成己者也,“善世而不伐”,二之所以成物者也,彼其所谓信谨者,乃其所以不伐者也,“闲邪存其诚地”,存诸己者也,“德博而化”,德之及乎物者也,彼其所以闲而存者,乃其所以博而化者也。
李氏舜臣曰:乾画一,实则诚,坤画一,虚则生敬,故《乾》九二言诚,《坤》六二言敬,诚敬二字始于包牺心画,而实天地自然之理也。
项氏安世曰:称“中正”者,二事也,二五为中,阴阳当位为正,称“正中”者,一事也,但取其正得中位,非以当位言也。
又曰:以在下卦,又非阳位,故不为中位而为中德,《文言》两称“君德”,明非君位也,此又称“龙德”之中,明非龙位之中也。
冯氏椅曰:《易》者理学之宗,而乾坤二卦,又《易》学之宗也,子思、孟子言诚 何氏楷曰:道止于中,中寓于庸,庸者常也,平无奇之名,言必有物,无苟高也,唯其信无择言矣,行必有则,无苟难也,唯其谨无择行矣,信谨,诚也,天德也,一实焉而已。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本义 “忠信”,主于心者,无一念之不诚也。“修辞”,见于事者无一言之不实也,虽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辞立诚,则无以居之。“知至至之”,进德之事:“知终终之”,居业之事,所以“终日乾乾”而夕犹惕若者,以此故也,可上可下,不骄不忧,所谓无咎也。
程传 三居下之上,而君德已著,将何为哉,唯进德修业而已,内积忠信,所以进德也:择言笃志,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后至之,加之在先,故可与几。所谓始条理者,知之事也。知终终之,力行也,既知所终,则力进而终之,守之在后,故可与存义。所谓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此学之始终也,君子之学如是,故知处上下之道而无骄忧,不懈而知惧,虽在危地而无咎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九三所以“终日乾乾”者,欲进益道德,修营功业,故终日乾乾匪懈也,进德则知至,将进也,修业则知终,存义也。
程子曰:“修辞立其诚”,不可不予细理会,言能修省言辞,便是要立诚,若只是修饰言辞为心,只是为伪也,修其言辞,正为立己之诚意。
吕氏大临曰:“忠信”“进德”,如有诸己又知所以充实之也,“修辞立其诚”,正名是事,行其实以称之也,所立卓尔而欲从之,“知至至之也”,于德有先见之明也,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知终终之”也,于分有当安之义也。
《朱子语类》云:“德”是就心上就,“业”是就事上说,“忠信”是自家心中诚实,“修辞立其诚”,是说处有真实底道理。
又云:“忠信”只是实,若无实,如何会进,如播种相似,须是实有种子下在泥中,方会日见发生,若把个空壳下在里面,如何会发生,道理须是实见得,若徒将耳听过将口说过,济甚事,忠信所以为实者,且如孝须实是孝,方始那孝之德日进一日,如弟须实是弟,方始那弟之德日进一日,若不实,却自无根了,如何会进,“立其诚”,诚依旧便是上面忠信,“修辞”是言语照管得到那里面亦须照管得到,“进德”是自觉得意,思日强似一日,日振作似一日,不是外面事,只是自见得意思不同。
问“立诚”不就制行上说,而特指“修辞”何也。曰:人不诚处多在言语上。又曰:人多将言语作没紧要,容易说出来,若一一要实,这工夫自是大,“忠信”、“进德”,便是见得“修辞”、“立城”底许多道理,“修辞”“立诚”,便要立得这忠信,若口不择言, 又云:伊川解“修辞”“立城”作择言笃志,说得来宽,不如明道说云:修其言辞,正为立己之诚意。
又云:“忠信”“修辞”,且大纲说所以“进德修业”之道,“知至”“知终”,则又详其始终工夫之序如此。“忠信”,心也。“修业”,事也。然蕴于心者所以见于事,修于事者所以养其心,此圣人之学,所以为内外两进,而非判然二事也。“知至”,则知其道之所止。“至之”,乃行矣而验其所知也。知终则见其道之极致。“终之”,乃力行而期至于所归宿之地也。知而行,行而知,二者交相警发,而其道日益光明,终日乾乾,又安有一息之间哉。
又云,知至至之者,言此心所知者,心真个到那所知田地,虽行未到而心已到,故其精微几密,一齐在此,故曰可与几。“知终终之”者,既知到极处,便力行到极处,此真实见于行事,故天下义理都无走失,故曰“可与存义。”又云,“进”字贴著那“几”字,“至”字又贴著那“进”字,“居”字贴著那“存”字,“终”字又贴著那“居”字,“几”是心上说,“义”是那业上底道理。
又云:“忠信”“进德”与“知至至之可与几也”,这几句都是去底字,“修辞”“立诚”与“知终终之可与存义”,都是住底字,“进德”是日日新,“居业”是日日如此。
问,修业居业之别?曰:二者只是一意,居,守也,逐日修作是修,常常如此是守。
又云;“忠信”“进德”“修辞”“立诚”,与“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分属乾坤,盖取健顺二体,忠信立诚,自有刚健主立之体,敬义便有静顺之体,进修便是个笃实:敬义便是千虚静,故曰:阳实阴虚。
俞氏琰曰:“德”与“忠信”,皆主于心者也,业与辞,皆见于事者也,事已成谓之业,“修业”者,业未成则修而成之也。居业,业已成则居而守之也。辞,言辞也。修,谓修省,非修饰也。诚,即忠信也。“立其诚”,谓立其诚意,而不为私意所汨挠也,若但以修饰言辞为心则伪矣,君子闲邪存其诚,则无一念之不正也,“修辞立其诚”,则无一言之不实也。
蒋氏悌生曰:“乾乾因其时而惕”,“时”字正解爻辞终日之义,见圣人省察之心,无少间断也。
蔡氏清曰:“忠信”所以“进德”也,每应一件事,俱著一个心为之主,唯心之所主者一于诚,则德之在内者进矣,而其于事也,又处置恰好,如其所言,则是诚有所归宿安顿处,是之谓“立诚”,而业之见于外者修矣。
又曰:诚,即“忠信”也。“忠信”,就初间存主上说,“修辞”“立诚”,就后来事到就绪上说,二者总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忠信”,直内之事;“修辞”,方外之事。
又曰:闲邪之外,再无存诚工夫,故承之曰“存其诚”,“修辞”之外,再无立诚工夫,故承之曰“立其诚”,诚即“忠信”,向也诚存于心,而今则见于事,而诚有立矣。
又曰:《中庸章句》云:反诸身不诚,谓反求诸身,而其所存所发有未实也,所存之实,即主忠信也,所发之实,即修辞立其诚也,合进德修业,总是《中庸》之诚身, 又曰:九三居下之上,是亦有位其上者,则九三为在下位矣,亦有位在下者,则九三又为居上位矣,若于初二,必不兼言居上位,若于九五,必不兼言在下位,此亦当知。
林氏希元曰:“忠信”,是此心真实,如孝则真实是孝,弟则真实是弟,实心为善,则善心日以充长,善念日以彰著,此之谓“进德”。实心为善乃诚也,若辞不修,语孝弟俱是空言无实事,则此诚终于消散,不聚集矣,何由立,又何绩业可居,故工夫又在修治言辞上,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言必有物,凡吐口言语皆是实事,无一句虚妄,乃“修辞”也。“修辞”则行成,孝成个孝,弟成个弟,吾心之诚,集聚而不消散,故曰“立其诚”,诚立则业修而可居,非立诚之外,又有居业工夫也,。
又曰:“忠信”所以“进德”,是“忠信”所以至之也,何也?凡有所进,将必有所至,“忠信”以至之,则善心日长,神智日开,道之壶奥,理之玄妙,为吾所当至者,一时虽未能遽至,固已先得之矣,故“可与几”。“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是修辞立诚,所以终之也,何也?居是居止,终是终身居止而不移,居之所以终之也,修辞立减以终之,则践履笃实,持守坚固,事理之宜,吾所当守者,可与存之而不失矣,义者,事理之宜,吾所当守者也。
郑氏维岳曰:不曰所以修业,而曰“所以居业”,盖修辞立诚,即是修矣,既修则有可居矣,犹之屋然,修者方在营构,既成则可居也。
杨氏启新曰:心之存诸中者,纯乎忠信而不妄,则心无外弛,而得于己者,日进而不已,言之见于事者,致其修省而有实,则事皆实理,而体诸身者,安安而不迁。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本义 内卦以“德”学言,外卦以“时”位言,“进德修业”,九三备矣,此则欲其及时而进也。
程传 或跃或处,“上下无常”,或进或退,去就从宜,非为邪枉,非离群类,“进德修业”,欲及时耳,时行时心,不可恒也,故云或。深渊者,龙之所安也。“在渊”,谓跃就所安,渊在深而言跃,但取进就所安之义。或,疑辞。随时而未可必也,君子之顺时,犹影之随形,可离非道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进退上下,不敢自必,相时而动,所谓“自试也”,大抵上下之交,皆危疑之地。故三厉而四犹疑之。
俞氏琰曰:上与进释“跃”宁,下与退,释在渊之义,无常无恒,释或之义,非为邪,非离群,欲及时,以申进无咎之义。
林氏希元曰:可上而不上,疑于以隐为高,可进而不进,疑于遯世离群,及时之时,上进之时也,欲及时,是应非为邪离群句,无咎,得时也。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本义 作,起也。物,犹人也。睹,释利见之意也。“本乎天”者,谓动物。“本乎地”者,谓植物,物“各从其类”。圣人,人类之首也,故兴起于上,则人皆见之。
程传 人之与圣人,类也,五以龙德升尊位,人之类莫不归仰,况同德乎,上应于下,下从于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流湿就燥,从龙从虎,皆以气类,故圣人作而万物皆睹,上既见下,下亦见上。物,人也。古语云人物物论,谓人也。《易》中“利见大人”其言则同,义则有异,如《讼》之利见大人,谓宜见大德中正之人,则其辨明,言在见前。《乾》之二五,则圣人既出,上下相见,共成其事,所利者见大人也,言在见后,“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虫兽草木,阴阳各从其类,人物莫不然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因大人与众物感应,故广陈众物相感应,以明圣人之作而万物瞻睹,以结之也。
又曰:《周礼大宗伯》“有天产地产”。《大司徒》云“动物植物,本受气于天者”是动物,天体运动,含灵之物亦运动,是亲附于上也,本受气于地者,是植物,地体凝滞,植物亦不移动,是亲附于下也。
《朱于语类》云:天下所患无君,不患无臣,有如是君,必有如是臣,虽使而今无,少间也,必有出来,“云从龙,风从虎”,只怕不是真个龙虎,若是真个龙虎,必生风致云也。
又云:“本乎天者亲上”,凡动物首向上,是亲乎上,人类是也。“本乎地者亲下”,凡植物本向下,是亲乎下,草木是也,禽兽首多横生,所以无智,此本康节说。
项氏安世曰: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故为“同声”、“同气”之义,圣人之于人亦类也,故为“各从其类”之义。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予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本义 “贤人在下位”,谓九五以下,“无辅”,以上九过高志满,不来辅助之也。
此第二节申《象传》之意。
程传 九居上而不当尊位,是以无民无辅,动则有悔也。
集说 谷氏家杰曰:以有位谓之贵,以有民谓之高,以有辅谓之贤人在下位,其贵而又五位,高而又无民,“贤人在下位”而又无辅者何,俱以亢失之也,故“动而有悔”。
潜龙勿用,下也。
程传 此以“下”言乾之时,勿用,以在下未可用也。
见龙在田,时舍也。
终日乾乾,行事也。
程传 “进德修业”也。
集说 林氏希元曰:事,所当为之事也。前章之“进德修业”是也,“终日乾乾”,日行其当为之事而不止息也。
或跃在渊,自试也。
本义 未遽有为,姑试其可。
程传 随时自用也。
集说 赵氏汝楳曰:凡飞者必先跃,所以作其飞冲之势,今鸟雏习飞,必跳跃于巢,以自试其羽翰,四之跃亦犹是也,此以试释“跃”。
俞氏琰曰:试释“跃”字,与《中庸》日省月试之试同,君子谨失时之戒,而自试其所学,盖欲自知其浅深也。
谷氏家杰曰:人见者浅,自见者真,必自家试之而后可决也。
飞龙在天,上治也。
本义 居上以治下。
程传 得位而行,上之治也。
集说 苏氏濬曰:上治,犹言盛治,五帝三王,皆治之上者也。
亢龙有悔,穷之灾也。
程传 穷极而灾至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本义 言“乾元用九”,见与它卦不同,君道刚而能柔,天下无不治矣。
此第三节,再申前意。
程传 用九之道,天与圣人同,得其用则天下治也。
集说 《朱子语类》:问:“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曰:“九”是天德,健中便自有顺,用之则天下治,如下文“乃见天则”。则,便是天德。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
程传 此以下言乾之义,方阳微潜藏之时,君子亦当晦隐,未可用也。
集说 陆氏铨曰:微阳潜藏,愈养则愈厚,轻用则发浊无余矣。
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本义 虽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
集说 苏氏轼曰:以言行化物,故曰“文明”。
终日乾乾,与时偕行。
本义 时当然也。
程传 随时而进也。
案 与时偕行,即卜“乾乾因其时”之义,言终日之间,无时不乾乾。
或跃在渊,乾道乃革。
本义 离下而上,变革之时。
程传 离下位而升上位,上下革矣。
集说 赵氏汝楳曰:三为下,至四革而为上,卦革则道亦革,此专释上下卦之交。
俞氏琰曰:革者变也,下乾以终,上乾方始,犹天道更端之时也。
林氏希元曰:此“道”字轻看,犹云阳道阴道,九四离下体而人上体,是“乾道”改革之时也,故“或跃”而未果,爻下本义改革之际,正是取此,人都不察,妄为之说。
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
本义 天德,即天位也,盖唯有是德,乃宜居是位,故以名之。
程传 正位乎上,“位当天德”矣。
集说 张氏振渊曰:虽有其位,苟无其德,可谓之位乎,天位而已,“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
程传 时既极。则处时者亦极矣。
集说 朱氏震曰:消息盈虚,“与时偕行”,则无悔,偕极则穷,故“有悔”也。
林氏栗曰:此节上下卦相应,初四为始,初“潜藏”,四乃“革”矣,革潜为“跃”也,二五为中,二“文明”,五乃“天德”矣,言德,称其位也,三上为终,三“与时偕行”,上偕极矣。
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本义 刚而能柔,天之法也。
此第四节,又申前意。
程传 用九之道,天之则也,夫之法则,谓天道也,或问乾之六爻,皆圣人之事乎,曰:尽其道者圣人也,得失则吉凶存焉,岂特乾哉,诸卦皆然也。
集说 苏氏轼曰:天以无首为则。
吴氏澄曰:刚柔适中,天之则也,则者理之有限节,而无过无不及者也。
张氏振渊曰:不曰乾爻用九,而曰“乾元用九”,统六爻而归之元也,亢而用变, 谷氏家杰曰:“则”者,有准而不过之意,“用九”者,有变而无常之意,天道不是变换,焉能使春夏秋冬,各有其限,圣人不是变换,焉能使仁义礼智,各有其节,“用九”,正天之准则不过处,故曰“乃见”。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本义 始则必亨,理势然也。
程传 又反复详说,以尽其义,既始则必亨,不亨则息矣。
利贞者,性情也。
本义 收敛归藏,乃见性情之实。
程传 乾之性情也,既始而亨,非利贞其能不息乎。
集说 《朱子语类》:问:“利贞者性情”也,曰:此“性情”如言本体,“元享”是发用处,“利贞”是收敛归本体处,如春时发生,到夏长茂条达,至秋结子,有个收敛摄聚底意思,但未坚实,至冬方成,在秋虽是已实,渐欲脱去其本之时,然受气未足,便种不生,故须到冬方成,人只到秋冬,疑若不见生意,不知都已收敛在内。
胡氏炳文曰:“性情”只是一“健”字,健者乾之性,而情其著见者也,且性情并言昉于此,释《彖》曰“性命”,此则曰“性情”,言性而不言命,非知性之本,言性而不言情,非知性之用也。
俞氏琰曰:性言其静也,情言其动也,物之动极而至于收敛而归藏,则复其本体之象,又将为来春动而发用之地,故曰“利贞者性情也”。元起于贞,“贞”下盖有“元”继焉,动生于静,静中盖有动存焉,“贞”而“元”,静而动,终而复始,则生生之道不穷,若但言性而不言情,则止乎贞纯平静而已矣,不见贞下起元静中有动之意,而非生生不穷之道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本义 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贞也。或曰:“坤利牝马”,则言所利矣。
程传 乾始之道,能使庶类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盖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赞其利之大曰“大矣哉”。
集说 程子曰:亭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贞也,《诗》曰:“维人之命。”于穆不已者,贞也。
《朱子语类》云:明道说得好,不有其功,言化育之无跡处为“贞”。
项氏安世曰:物既始则必亨,亨则必利,利之极必复于元,“贞”者“元”之复也,故四德总以一言曰“乾元”,又曰“乾始”,而四德在其中矣。以八卦言之,震其元也,故为出。巽则既出而将相见也,故为齐,离则其亨也,故为相见。坤则既相见而将利之 俞氏琰曰:“乾始”,即“乾元”也,元乃生物之始也,美即“亨”也,“亨”乃众美之会也。
林氏希元曰:上既即物之生长收藏以释四德,此则归其功于乾始而赞其大,即《彖传》“统天”之说也,谓乾虽四德之流行,要一元之所统,何也?乾既始物,由是而亨,就能以美利遍利乎天下,又收敛于内,不言其所利,是皆乾始之所为也,不其大与,盖万物归根复命之时,造化生物之功,不复可见。韩琦诗云:“须臾慰满三农望,敛却神功寂若无”,亦是此意。
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
本义 “刚”,以体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无过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纯”者,不杂于阴柔。“粹”者,不杂于邪恶,盖刚健中正之至极,而精者又纯粹之至极也,或疑乾刚无柔,不得言中正者,不然也,天地之间,本一气之流行而有动静尔,以其流行之统体而言,则但谓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动静分之,然后有阴阳刚柔之别也。
集说 乔氏中和曰:“刚”者元也,“健”者亨也,“中”者利也,“正”者贞也,“元亨利贞”,实以体之,“刚健中正”也,一爻之情,六爻之情也。
六爻发挥,旁通情也。
本义 旁通,犹言曲尽。
集说 胡氏炳文曰:曲尽其义者在六爻,而备全其德者在九五一爻,时乘六龙以下,则为九五而言也。
蔡氏清曰:六爻发挥,只是起下文时乘六龙之意,盖上文每条俱是乾字发端,一则曰“乾元”,二则曰“乾始”,三则曰“大哉乾乎”。
至此则更端曰“六爻发挥”,可见只是为“时乘六龙”设矣,即《彖传》“六位时成”也。
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本义 言圣人“时乘六龙以御天”,则如天之“云行雨施,而天下平也”。
此第五节,复申首章之意。
程传 大哉,赞乾道之大也。以“刚健中正”“纯粹”六者,形容乾道。精,谓六者之精极,以六爻发挥,旁通尽其情义,乘六爻之时,以当天运,则天之功用著矣,故见“云行雨施”,阴阳溥畅,天下和平之道也。
集说 张氏清子曰:《彖》言“云行雨施”,而以“品物流形”继之,则云雨为乾之云雨,此言“云行雨施”,而以“天下平”继之,则圣人之功即乾,而云雨乃圣人之德 案 贞元为体,亨利为用,然即体即用,不相离也,即用即体,未尝二也,故复释之曰:“乾元者始也”,然即始而亨之理已具,不待亨而后知其亨也,利贞者成也,事之成者,得其性情之正而已,而岂在外哉,盖一心之发,散为万用之施,而万理之宜归于一性之德,故其始而必亨也,是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也,及其终也,利及天下,而所性无加焉,又何利之可言,此“乾元”所以“统天”,而其德所以为大也。由此观之,乾之德,于其“元亨”也,见其动直而刚焉,不息而健焉,于其利贞也,见其裁制而中焉,确守而正焉,于其一元之妙,心普万物而无心也,见其不累于功利之杂驳而纯粹,不滞于声奥之粗而至精焉。天道如此,王道亦然,王者之道,其发之也刚,其行之也健,其裁之也中,其处之也正,要以体天地生生之心,能使仁覆天下而莫知为之者,如精金美玉而无疵,如太虚浮云而无亦,非如霸者小补之功,驩虞之效也,卦唯九五全备斯德,故六爻发挥,固所以旁通乎乾之情矣,而唯九五则兼统众爻之德以处崇高之位,其象为“飞龙在天”者,盖如乘六龙以御天也,龙而在天,有不兴云致雨,而使下土平康者乎,夫当其膏泽溥施,即乾之“美利利天下”也,及乎荡荡平平,大化无迹,又非乾之不言所利者与,夫子之发明天德王道,于是为至。
君子以成德为行,曰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本义 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见尔。
程传 德之成,其事可见者行也,德成而后可施于用,初方潜隐未见,其行未成,未成,未著也,是以君子弗用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为行,言德则行在其中矣,德者得之于心,行出来方见,这便是行。问行而未成如何?曰:只是事业未就。
吴氏澄曰:隐而未见者潜之象,行而末成,是以欲其弗用也。
蔡氏清曰:言君子之所以为行者,以成德为行也,夫既以成德为行,初九德已成矣,则日可以见之行也,夫既可以见之行矣,丽又何以曰“勿用”,盖初九时乎“潜”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隐而未见,则行犹未成,是以君子亦当如之而勿用也。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本义 盖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再言君德,以深明九二之为大人也。
程传 圣人在下,虽已显而未得位,则“进德修业”而已,学聚问辨,“进德”也;宽居仁行,“修业”也。君德已著,利见大人,而进以行之耳,进居其位者,舜禹也,进行其道者,伊傅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学以聚之,问以辨之”,既探讨得当,且放顿宽大田地,待触类自然有会合处,故曰“宽以居之”。
又曰:学聚之,以知其理,仁行之,以行其事,问辨之,以审别所当行于学聚之后,宽居之,以存贮所已知于仁行之先,宽之所居,即学之所聚者,仁之所行,即问之所辨者。
林氏希元曰:学聚问辨,是知工夫,宽居,是把义理放在胸中,详玩深味,使透彻贯串,乃居安资深时也,故亦属之行。
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天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本义 重刚,谓阳爻阳位。
程传 三“重刚”,刚之盛也,过中而居下之上,上未至于天,而下已离于田,危惧之地也,因时顺处,乾乾兢惕以防危,故虽危而不至于咎,君子顺时兢惕,所以能泰也。
集说 虞氏翻曰:以乾接乾,故“重刚”,位非二五,故“不中”也。
孔氏疑达曰:“上不在天”,谓非五位,“下不在田”,谓非二位也,居危之地,以乾乾夕惕戒惧不息,得无咎也。
吴氏澄曰:九三居下乾之终,接上乾之始,九四居上乾之始,接下乾之终,当重乾上下之际,故皆曰“重刚”。
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本义 九四非重刚,“重”字疑衍,在人谓三,或者,随时而未定也。
程传 四不在天不在田而出入之上矣,危地也。疑者,未决之辞。处非可必也,或进或退,唯所安耳,所以无咎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三之与四,俱为人道,人下近于地,上远于天,九三近二,正是人道,九四则上近于天,下远于地,非人所处,故特云中不在人。或之者疑之也,此夫子释经“或”字,经称“或”,是疑惑之辞,欲进欲退,犹豫不定,故“疑”之也。
九三位卑近下,向上为难,危惕忧深,九四则阳德渐胜,去五弥近,前进稍易,故但疑惑,忧则浅也。
李氏鼎祚曰:三居下卦之上,四居上卦之下,俱非得中,故曰“重刚而不中”也。
张氏振渊曰:“或之者”据其迹,“疑之者”指其心,疑非狐疑之疑,只是详审耳。
本义 大人,即释爻辞所“利见之大人”也,有是德而当其位,乃可当之,人与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于有我之私,是以牿于形体,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为体,曾何彼此先后之可言哉。先天不违,谓意之所为,默与道契。后天奉天,谓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回纥谓郭子仪曰:卜者言此行当见一大人而还,其占盖与此合,若子仪者,虽未及乎夫子之所论,然其至公无我,亦可谓当时之大人矣。
程传 大人与天地日月四时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圣人先于天而天同之,后于天而能顺天者,合于道而已,合于道,则人与鬼神岂能违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与天地合其德”,谓覆载也,“与日月合共明”,谓照临也,“与四时合其序”者,若赏以春夏,刑以秋冬之类也,“与鬼神合其占凶”者,若福善祸淫也,若在天时之先行事,天乃在后不违,是天合大人也,若在天时之后行事,能奉顺上天,是大人合天也,尊而远者尚不违,况小而近者可违乎。
程子曰:若不一本,则安能“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又曰:天且不违,况于鬼神乎,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
王氏宗传曰:“先天而天弗违”,时之未至,我则先乎天而为之,而天自不能违乎我。
“后人而奉天时”,时之既至,我则后乎天而奉之,而我亦不能违乎人,盖“大人”即天也,天即“大人”也。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
本义 所以动而有悔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言上九所以亢极有悔者,正由有此三事,若能三事备知,虽居上位,不至于亢也。
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本义 知其理势如是,而处之以道,则不至于有悔矣,固非计私以避害者也,再言其唯圣人乎,始若没问,而卒自应之也。
此第六节,复申第二节三节四节之意。
程传 极之甚为“亢”,至于“亢”者,不知进退存亡得丧之理也,圣人则知而处之,皆不失其正,故不至于亢也。
集说 李氏鼎祚曰:再称圣人者,叹美用九能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朱氏震曰:“亢”者处极而不知反也,万物之理,进必有退,存必有亡,得必有丧,“亢”知一而不知二,故道穷而致灾,人固有知进退存亡者矣,其道诡于圣人,则未必得其正,不得其正,则与天地不相似,“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故两 胡氏炳文曰:阳极则剥,《乾》上则“亢”,中不可过也,知其时将过乎中,而处之不失其正,“其唯圣人乎”,“贞者正也”,乾元之用所归宿也,乾之四德始于元,至此又论圣人之体乾而归于正,其意深矣。
陈氏琛曰:进极必退,存极必亡,乃理势之自然也,知其如是,则随时变通,而处以是道之当然,有收敛而无施张,有舍弃而无系吝,如此则不至于有悔矣,然此唯圣人能之,盖圣人乐天知命,达理而能权也,常人则明不足以见几,心不免于物累,故不能也。
总论 朱子答万正淳曰:大抵《易》卦之辞,本只是各著本卦本爻之象,明占凶之占当如此耳,非是就圣贤地位说道理也,故《乾》六爻,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自圣人以至于愚不肖,筮或得之,义皆有取,但纯阳之德,刚健之至,若以义类推之,则为圣人之象,而其六位之高下,又有似圣人之进退,故文言因潜见曜飞自然之文,而以圣人之迹各明其义。
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
本义 刚方,释“牝马之贞”也。“方”,谓生物有常。
集说 《朱子语类》云:“坤至柔而动也刚”,“坤”只是承天,如一气之施,坤则尽能发生承载,非刚安能如此。
问《程传》云:坤道“至柔而动则刚”,坤体至静而德则方,柔与刚相反,静与方疑相似。曰:静无形,方有体,静言其体,则不可得见,方言其德,则是其著也。
吴氏澄曰:坤体中含乾阳,如,人肺藏之藏气,故曰“至柔”。然其气机一动而辟之时,乾阳之气,直上而出,莫能御之,故曰“刚”。刚即六二爻辞所谓直也,乾运转不已,而坤体岿然不动,故曰“至静”。然其生物之德普遍四周,无处欠缺,故曰“方”。
方即六二爻辞所谓“方”也,乾之九五,不徒刚健而能中正,故为乾元之大,坤之六二,不徒柔静而能刚方,故为坤元之至。
何氏楷曰:乾刚坤柔,定体也,坤固至柔矣,然乾之施一至,坤即能翕受而发生之,气机一动,不可止遏屈挠,此又柔中之刚矣,乾动坤静,定体也,坤固至静矣,及其承乾之施,陶冶万类,各有定形,不可移易,此又静中之方矣,承静者体也,刚方者用也。
后得主而有常。
本义 《程传》曰:“主”下当有“利”字。
集说 赵氏汝楳曰:坤无乾以为始,孰开其端,“先迷”也,天先施而地后生,“后得主”也,先阳后阴,乃天地生生之常理。
余氏芑舒曰:程子以“主利”为一句,朱子因之,故以《文言》后得主力阙文,然《彖传》后顺得常,与“后得主而有常”,意正一律,似非阙文也。
俞氏琰曰:坤道之常,盖当处后,不可挠先也,挠先则失坤之常矣,唯处乾之后, 含万物而化光。
本义 复明“亨”义。
集说 王氏宗传曰:唯其动刚,故能德应乎乾,而成万物化育之功,唯其德方,故能不拂乎正,而顺万物性命之理,此坤之德所以能配天也,后得主而有常,则申后顺得常之义,含万物而化光,则申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之义。
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
本义 复明顺承天之意。
此以上申《彖传》之意程传 坤道至柔,而其动则刚,坤体至静,而其德则方,动刚故应乾不违,德方故生物有常,阴之道,不唱而和,故居后为得,而主利成万物,坤之常也,含容万类,其功化光大也,“主”字下脱“利”字,“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承天之施,行不违时,赞坤道之顺也。
集说 俞氏琰曰:“至柔而动也刚”,申“德合无疆”之义。“至静而德方”,释“贞”义。“后得主而有常”,后顺得常之谓。含万物而化光,即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之谓。“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即“乃顺承天”之谓。
案 动刚,释“元亨”也,气之发动而物生也。德方,释“利贞”也,形之完就而物成也。柔静者坤之本体,其刚其方,乃是乾为之主。而坤顺之以行止者,故继之曰“后得主而有常”,释“先迷后得主”也。含物化光,谓亨利之间,致养万物,其功盛大,释“西南得朋”也。承天时行,谓顺承于元,至贞不息,阴道终始于阳,释“东北丧朋”也。盖孔子既以《坤》之“元亨利贞”,配乾为四德,则所谓西南东北者,即四时也,故用《彖传》所谓含弘光大者,以切西南,又用所谓乃顺承天“行地无疆”者,以切东北,欲人知四方四德,初非两义,此意《彖传》未及,故于《文言》发之。
又案《乾》爻唯九五“刚健小正”,得乾道之纯,故《彖传》言“乘尼”“御天”,“首出庶物”,即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之义也,《坤》爻唯六二柔顺中止,得坤道之纯,故《文言》言动刚德方,含物承天,即六二“直方大”之义也,《象传》于乾五曰“位乎天德”,于坤二曰“地道光”也,明乎乾坤之主,在此二爻矣。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本义 古字“顺”、“慎”通用,案此当作“慎”,言当辨之于微也。
程传 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积而成,家之所积者善,则福庆及于子孙,所积不善,则灾殃流于后世,其大至于弑逆之祸,皆因积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则知渐不 集说 吕氏祖谦曰:“盖言顺也”,此一句尤可警,非心邪念,不可顺养将去,若顺将去,何所不至,惩治遏绝,正要人著力。
张氏振渊曰:天道有刚必有阴,原相为用,然阴之为道,利于从阳。而不利于抗阳。
坤道可谓至顺矣,而顺之变反为逆,故至人深著其顺之利,明臣子之大分,究极其逆之祸,立君父之大防也。
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本义 此以学言之也。止,谓本体,义,谓裁制,敬则本体之守也,“直内”“方外”,《程传》备矣,不孤,言大也,疑故习而后利,不疑则何假于习。
程传 “直”言“其正也”,“方”言“其义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内,守义以方其外,敬立而内直,义形而外方,义形于外,非在外也,敬义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为疑乎。
集说 孔氏颖达曰:君子用“敬以直内”,内谓心也,用此恭敬以直内心,“义以方外”者,用此义事以方正外物,言君子法地正直而生万物,皆得所宜。
程子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合内外之道也,释氏内外之道不备者也,敬义夹持,直上达天德自此。
问必有事焉当用敬否?曰:“敬”只是涵养一事。必有事焉,须当集义,又问,义莫是中理杏?曰:中理在事,义在心。问敬义何别?曰:敬只是持己之道,义便知有是有非,顺理而行是为义也,若只守一个敬,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又问“义”只在事上如何?曰:内外一理,岂特事上求合义也。
谢氏良佐曰:释氏所以不如吾儒,无“义以方外”一节,“义以方外”,便是穷理,释氏却以理为障碍,然不可谓释氏无见处,但见了不肯就理。
《朱子语类》云:“敬以直内”,是持守功夫;“义以方外”,是讲学功夫,“直”是直上直下,胸中无纤豪委曲,“方”是割截方正之意,是处此事皆合宜,截然不可得而移易之意。
又云:“敬义”夹持,直上达天德自此,最是下得“夹持”两字好,教主乎中,义防于外,二者夹持,要放下霎时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达天德自此,表裹夹持更无东西走作去处,上面只更有个天德。
问义形而外方,曰:“义”是心头断事底,心断于内,而外便方正,万物各得其宜。
又云:《文言》将“敬”字解“直”字,“义”字解“方”字,“敬义立而德不孤”,即解“大”字,敬而无义,则作事出来必错了,只义而无礅则无奉,何以为义,皆是孤也,须是敬义立方不孤,施之事君则忠于君,事亲则悦于亲,交朋友则信于朋友,皆不待习而无一之不利也。
王氏应麟曰:《丹书》“敬义”之训,夫子于《坤》六二《文言》发之,孟子以集义为本,程子以居敬为先,张宣公谓功夫并进,相须而相成也。
胡氏炳文曰:《乾》九三,明诚并进也,《坤》六二,敬义偕立也,主敬是为学之要,集义乃讲学之功。
薛氏瑄曰:“敬以直内”,涵养未发之中。“义以方外”,省察中节之和。
又曰:“敬以直内”,戒慎恐惧之事。“义以方外”,知言集义之事。内外夹持,用力之要,莫切于此:蔡氏清曰:“正”是无少邪曲,“义”是无少差谬。
又曰:此“正”“义”二字,皆以见成之德言,然直不自直,必由于敬,方不自方,必由于义,直即主忠信,方即徙义,直即心无私,方即事当理,故直内以动者言为当。
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
程传 为下之道,不居其功,含晦其章美以从上事,代上以终其事,而不敢有其成功也,犹地道代天终物,而成功则主于天也,妻道亦然。
集说 宋氏衷曰:臣子虽有才美,含藏以从其上,不敢有所成名也,地终天功,臣终君事,妇终夫业,故曰“而代有终”也。
程子曰:天地日月一般,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中生物者,皆大气也,唯“无成而代有终”者,地之道也。
王氏申子曰:三非有美而不发,特不敢暴其美,唯知代上以终其事,而不居其成功,犹地代天生物,而功则主于天也。
俞氏琰曰:既曰“地道无成”,而又曰“代有终”,何也?乾能始物,不能终物,坤继其终而终之,则坤之所以为有终者,终乾之所未终也。
蔡氏清曰:以从王事,以含章之道而从王事,“弗敢成也”,即是含章之道,用于从王事者也。
谷氏家杰曰:爻言“有终”,此言“代有终”,则并其终亦非坤之所敢有也。
何氏楷曰:乾能始万物而已,必赖坤以作成之,故曰“代有终”,正对乾之始而言。
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
程传 四居上近君,而无相得之义,故为隔绝之象,天地交感则变化万物,草木蕃盛,君臣相际而道亨,天地闭隔,则万物不遂,君臣道绝,贤者隐遯,四于闭隔之时, 集说 张氏浚曰:括囊盖内亢其德,待时而有为者也,汉儒乃以“括囊”为讥、岂不陋哉,阳舒阴闭,故孔子发天地闭之训,夫闭于前而舒于后,生化之功,自是出也,“括囊”之慎,庸有害乎。
君子黄中通理。
本义 黄中,言中德在内,释“黄”字之义也。
集说 蔡氏消曰:通理,即是“黄中”处通而理也,盖“黄中”非通,则无以应乎外,通而非理,则所以应乎外者,不能皆得其当,此所以言“黄中”,而必并以通理言之,通理亦在内也。
正位居体。
本义 虽在尊位,而居下体,释“裳”字之义也。
案 孟子曰:“立天下之正位。”正位,即礼也,此言“正位居体”者,犹言以礼居身尔,礼以物躬,则自卑而尊人,故为释“裳”字之义。
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本义 “美在其中”,复释“黄中”,“畅于四支”,复释“居体”。
程传 黄中,“文在中”也,君子文中而达于理,居正位而不失为下之体,五尊位,在坤则唯取中正之义,美积于中,而通畅于四体,发见于事业,德美之至盛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二在下,方是就功夫上说,如不疑其所行是也,五得尊位,则是就它成就处说,所以云“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蔡氏渊曰:“黄中通理”,释“黄”义,“正位居体”,释“裳义”。“黄中”,正德在内。“通理”,文无不通,言柔顺之德蕴于内也。“正位”,居在中之位,“居体”,居下体而不僭,言柔顺之德形于外也。“美在其中”,“黄中通理”也,“畅于四支,发于事业”,“正位居体”也,二五皆中,二居内卦之中,其发见于外者,不疑其所行而已,五外卦之中,其施于外,有事业之可观,坤道之美,至此极矣。
蔡氏清曰:“黄裳”二字,分而言之,则‘黄”为中,“裳”为顺,合而言之,则唯中故顺,存于中为中,形于外为顺,理一而已,天下无有形于外而不本乎中者,唯有黄中之德,故能以下体自居。
林氏希元曰:《文言》既分释“黄裳”了,又恐人认为二物,不知归重处,故发“美在其中”一条,见得其所谓顺,乃本于中,与《象传》“文在中也”,及“六二之动直以方也”,意思一般。
附录 胡氏炳文曰:盖直内方外之君子,即“黄中通理”之君子也。“敬以直内”,则胸中洞然表里如一,是即所以为“黄中”。“义以方外”,则凡事之来,义以处之,无不合理,是即所以为通理,五之“黄中通理”,本于直内方外,故其“正位”也,虽居乎五之尊,而其“居体”也,则不失乎二之常,二之直内方外,是内外夹持,两致其力, 案 《乾》爻之言学者二,于九二,则曰,言信行谨,闲邪存诚也;于九三,则曰忠信以进德,修辞立诚以居业世。《坤》爻之言学者二,于六二,则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也;于六五,则曰“黄中通理,正位居体”也。分而言之则有四,合而言之,则《乾》二之存诚,即乾三之忠信,皆以心之实者言也,乾二之信谨,即乾三之修辞立诚,皆以言行之实者言也。在二为大人,则以成德言之,由其言行以窥其心,见其纯亦不已如此也,在三为君子,则以进学言之,根于心而达于言行,见其交修不懈如此也。
《坤》二之“直内”,即《坤》五之“黄中”,皆以心之中直者言也,《坤》二之“方外”,即《坤》五之“正位”,皆以行之方正者言也,二言“直”而五言“中”,“直”则未有不中者,“中”乃“直”之至也。二言“方”而五言“正”,“方”则未有不正者,“正”乃方之极也,二居下位,不疑所行而已,五居尊,又有发于事业之美,此则两爻所以异也。在《乾》之两爻,诚之意多,实心以体物,是乾之德也。《坤》之两爻,敬之意多,虚心以顺理,是坤之德也。而要之未有诚而不敬,未有敬而不诚者,乾坤一德也,诚敬一心也,圣人所以分言之者。盖乾阳主实,坤阴主虚,人心之德,必兼体焉,非实则不能虚,天理为主,然后人欲退听也,非虚则不能实,人欲屏息,然后天理流行也,自其实者言之则曰诚,自其虚者言之则口“敬”,是皆一心之德,而非两人之事,但在圣人则纯乎诚矣,其敬也,自然之敬也,其次则主敬以至于诚。故程子曰:诚则无不敬,未能诚,则必敬而后诚,而以乾坤分为圣贤之学者此也。
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本义 “疑”,谓钧敌而无小大之差也,坤虽无阳,然阳未尝无也。“血”,阴属,盖气刚而血阴也,“玄黄”,天地之正色,言阴阳皆伤也。
此以上申《象传》之意。
程传 阳大阴小,阴必从阳,阴既盛极,与阳偕矣,是疑于阳也,不相从则必战,卦虽纯阴,恐疑无伤,故称龙见其与阳战也,于野,进不已而至于外也,盛极而进不已,则战矣,虽盛极不离阴类也,而与阳争,其伤可知,故称“血”,阴既盛极,至与阳争,虽阳不能无伤,故“其血玄黄”。“玄黄”,天地之色,谓皆伤也。
集说 干氏宝曰:阴在上六,十月之时也,卦成于乾,乾体纯刚,不堪阴盛,故曰“龙战”。戌亥,乾之都也,故“称龙”焉,“未离阴类”,故曰“血”。阴阳色杂,故曰“玄黄”。阴阳离则异气,合刚同功,君臣夫妻,其义一也。
蔡氏渊曰:十月为纯坤之月,六爻皆阴,然生生之理,无顷刻而息,圣人为其纯阴而或嫌于尤阳也,故“称龙”心明之,古人谓十月为阳月者,盖出于此。
俞氏琐曰:“玄”者天之色,“黄”者地之色,“血”言“幺黄”,则天地杂类,而阴刚无别矣,故曰“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阴阳相战,虽至于天地之杂乱,然而天地定位于上下,其大分终不可易,故其终又分而言之曰:“天玄而地黄”。
说卦传集说 孔氏颖达曰:孔子以伏羲画八卦后重为六十四卦,《系辞》中略明八卦小成,引而伸之。又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主情”,然引而伸之,重三成六之意,犹自末明,仰观俯察,近身远物之象,亦为未见,故于此更备说重卦之由,及八卦所为之象,谓之说卦焉。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
本义 幽赞神明,犹言赞化育。《龟荚传》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茎长丈,其丛生满百茎。
集说 孔氏颖达曰:以此圣知,深知神明之道,而生用蓍求卦之法,故曰“幽赞于神明而生蓍”。
程子曰:“幽赞于神明而生蓍”,用蓍以求卦,非谓有蓍而后画卦。
苏氏轼曰:介绍以传命谓之赞天地鬼神不能与人接也,故以蓍龟为之介绍。
项氏安世曰:“生蓍”,谓创立用蓍之法,神不能占,以蓍言之,所以赞神出命,故谓之幽赞神明,即大衍所谓佑神也。
龚氏焕曰:项氏生蓍之说与本义不同,然以下文倚数立卦生爻观之,似当以项氏之说为正。
苏氏濬曰:“生蓍”,当以生爻之例推之。
参天两地而倚数。
本义 天圆地方,圆者一而围三,三各一奇,故参天而为三,方者一而围四,四合二偶,故两地而为二,数皆倚此而起,故揲蓍三变之末,其余三奇,则三三而九,二偶,则三二而六,两二一三则为七,两二一二则为八。
集说 孔氏颖达曰:七九为奇,天数也;六八为偶,地数也。故取奇于天,取偶于地,而立七八六之数也。何以参两为目奇偶,盖占之奇偶,亦以“参两”言之一,且以两是偶数之始,三是奇数之初故也,不以一目奇者。张氏云,以“三”中含两,有一以包“两”之义,明天有包地之德,阳有包阴之道。
陆氏振奇曰:倚,依也,,倚数在生菁之后,立卦之前,盖用蓍得数,而后布以为卦,故以七八九六当之。
案 “参天两地”,以方圆径田定之,亦其大致尔,实则径一者不止围三,非密率也。以理言之,则张氏所谓以一包两者是,盖:大能兼地,故一并二以成三也,以算言 二二三为八也。以算言之,奇数起于一三,成于九七,偶数起于二四,成于八六,故以其成数纪阴阳,阳之进者为老,退者为少,阴之退者为老,进者为少也,以象言之,凡圆者以六而包一,虚其中则六也,实其中则七也,凡方者以八而包一,实其中则九也,虚其中则八也,阳圆阴方,阳实阴虚,故唯七圆而实,为盛阳,唯八方而虚,为壮阴,九虽实而积方,则阳将变而为阴矣,故为老阳,六虽虚而积圆,则阴将变而为阳矣,故为老阴也,其数皆自参两中来,故曰“倚数”。
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本义 和顺从容,无所乖逆,统言之也,理,谓随事得其条理,析言之也,穷天下之理,尽人物之性,而合于天道,此圣人作《易》之极功也。
此第一章。
集说 韩氏伯曰:卦,象也。蓍,数也。卦则“雷风相薄,山泽通气”,拟象阴阳变化之体,蓍则错综天地参两之数,蓍极数以定象,卦备象以尽数,故蓍曰“参天两地而倚数”,卦曰“观变于阴阳”。
孔氏颖达曰:《系辞》言伏羲作《易》之初,故直言仰观俯察,此则论其既重之后,端策布爻,故先言生蓍,后言立卦,非是圣人幽赞在观变之前也。
邵子曰:天使我有是之谓命,命之在我之谓性,性之在物之谓理。
《朱子语类》:问:“观变于阴阳而立卦”,是就蓍数上观否?曰:恐只是就阴阳上观,未用说到蓍数处。
问既有卦则有爻矣,先言卦而后言爻何也?曰:方其立卦,只见是卦,及细别之,则有六爻。又问阴阳刚柔一也,而别言之何也?曰:“观变于阴阳”,近于造化而言,“发挥刚柔”,近于人事而言,且如《泰》卦,以卦言之,只见得“小往大来”阴阳消长之意,爻里面使有包荒之类。
又云:和顺于道德,是默契本原处,理于义,是应变合宜处,物物皆有理,须一一推穷,性则是理之极处,故云“尽”,命则性之所自来处,故云“至”。
问“穷理尽性至于命”。曰:此本是就《易》上说,《易》上尽具许多道理,直是穷得物理,尽得人性,到得那天命,所以《通书》说《易》者性命之原。
项氏安世曰:道即命,德即性,义既理,“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反覆互言也。《易》之奇偶,在天之命,则为阴阳之道,在人之性,则为仁义之德,在地之宜,则为刚柔之理,“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自幽而言以至于显,此所谓显遒也, 陈氏淳曰:理与性对说,理乃是在物之理,性乃是在我之理,在物底,便是天地人物公共底道理,在我底,乃是此理已具得为我所有者。
徐氏几曰:如乾为天道,面《彖》之“元亨利贞”则其德,爻之“潜”、“见”“跃”、“飞”则其义,以一卦面统言之,所谓和顺也,就六爻而言之,所谓理也,善观《易》者,推爻义以穷天下之理,明卦德以尽一已之性,穷理尽性,则进退存亡得丧之大道可以知,而天命在我矣。
龚氏焕曰:上句是自源而流,于句是自末而本,盖必“和顺于道德”,而后能“理于义”,必“穷理尽性”,而后能“至于命”也。
卢氏曰:立卦生爻,在圣人作《易》上看,若作蓍数之变说,却是用《易》了,朱于谓未用说到蓍数处是也,圣人观察天地变化之道,而立乾坤等卦,故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既观象立卦,又就卦中刚柔两画,或上或下,微细阐发出来,而生变动之爻,故曰“发挥于刚柔而生爻”。
何氏楷曰:数既形矣,卦斯立焉,卦既立矣,爻斯生焉,“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从合而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从分而合,理义非二也。程子谓在物为理处物为义是也,性命与道德非二也,于思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是也。穷尽至,皆造极之意,性者理之原,理穷则逢其原,故穷理所以尽性,命者性之原,性尽则逢其原,故尽性所以至命,只是一事。
总论 孔氏颖达曰:“昔者圣人”至“以至于命”,此一节将明圣人引伸因重之意,故先叙圣人本制蓍数卦爻,备明天道人事妙极之理。
何氏楷曰:此章统论蓍卦及爻辞。圣人,谓羲文周公,《乾凿度》曰:垂皇策者羲,则自伏羲时已用蓍矣。卦爻辞至文王周公始系,此以知其总言之也。
案 此章次第最明,《易》为卜筮之书,而又为五经之原者,于此章可见矣,生蓍者,立蓍筮之法也。倚数者,起蓍筮之数也,立卦生爻,则指画卦系辞言之,是二者,蓍筮之体而言于后,明《易》为卜筮而作也,“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言卦画既立,则有以契合乎天之道,性之德,而下周乎事物之宜也,“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言爻辞既设,则有以穷尽乎事之理,人之性,而上达乎天命之本也,夫《易》以卜筮为教,而道德性命之奥存焉,然则以礻几祥之末言《易》者,迷道之原者也,以事物之迹言《易》者,失教之意者也。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本义 “兼三才而两之”,总言六画,又细分之,则阴阳之位,间杂而成文章也。
此第二章。
集说 崔氏憬曰:此明一卦六爻,有三才二体之义,故明天道既立阴阳,地道又立 朱氏震曰:“易有太极”,阴阳者;太虚聚而有气,柔刚者,气聚而有体,仁义根于太虚,见于气体,动于知觉者也,自万物一源观之谓之性,自禀赋观之谓之命,自天地人观之谓之理,三者一也,圣人“将以顺性命之理”,曰阴阳,曰柔刚,曰仁义,以立天地人之道,盖互见也,易“兼三才而两之”,六画成卦,则三才合而为一,然道有变动,故“分阴分阳,迭用柔刚”。
郭氏雍曰:“分阴分阳”,非谓立天之道阴阳也,言三才二道,皆一为阴一为阳,见于六位也。“迭用柔刚”,非谓立地之道柔刚也,言三才阴阳,分为六画,迭以九六柔刚居之也,故三才二道,不兼九六言之,则曰“六画”,兼明九六柔刚,而后谓之六位。
《朱子语类》云:阴阳刚柔仁义,看来当曰义与仁,当以仁对阳,仁若不是阳刚,如何作得许多造化,义虽刚,却主于收敛,仁却主发舒,这也是阳中之阴,阴中之阳,互藏其根之意,且如今人用赏罚,到赐与人自足无疑,便作将去,若是刑杀时,便迟疑不肯果决,这见得阳舒阴敛,仁属阳,义属阴处。
邱氏富国曰:上言“穷理尽性至命”,此言“顺性命”,则《易》中所言之理,皆“性命”也,然所谓性命之理,即阴阳柔刚仁义是也,兼三才而两之,言重卦也,方卦之小成,三画已具三才之道,至重而六,则天地人之道各两,所谓六画成卦也。“分阴分阳”,以位言,凡卦初三五位为阳,二四上位为阴,自初至上,阴阳各半,故曰“分”。“迭用柔刚”以爻言,柔谓六,刚谓九也,位之阳者,刚居之,柔亦居之,位之阴者,柔居之,刚亦居之,或柔或刚更相为用,故曰“迭。”分之以示其经,迭用以为之纬,经纬错综,粲然有文,所谓“六位”“成章”也。
吴氏澄曰:性之理,谓人之道也,命之理,谓天地之道也,天之气有阴阳,地之质有柔刚,人之德有仁义,道则主宰其气质而为是德者也。
又曰:上文以“阴阳”为天之道,下“阴阳”二字,则总言六位也,六位之中,分初三五为阳位,二四上为阴位也,上文以柔刚为地之道,下“柔刚”二字,则总言六画也,六画之中,奇画皆谓之刚,偶画皆谓之柔也,位无质,故以“阴阳”名之,画有质,故以“柔刚”名之,位之阴阳相间则分布一定,画之柔刚不同,则迭用以居,《系辞传》所谓“物相杂曰文”,即此成章之谓也。
胡氏炳文曰:上章“和顺于道德”,统言之也;“理于义”,析言之也,此章“六画而成卦”,统言之也;“分阴分阳”,“迭用柔刚”,“六位而成章”,又析言之也。
蔡氏清曰:“立天之道”,非有以立之也,谓天道之立以阴阳也,其曰“分阴分阳”者,阴阳之自分也,其曰“迭用柔刚”者,刚柔之自迭用也,非有分之用之者也。
何氏楷曰:此章言卦画“顺性命之理”,即上章所谓“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者,以一言蔽之也,性者人之理,命者天地之理,阴阳刚柔仁义,正所谓“性命之理”也,分阴阳,用柔刚,以断吉凶而成亹亹,则仁义之道,固在其中矣。
案 上章总论易道,此章以下,专明卦也,上章云“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和顺于道 又案 “兼三才而两之”,及“分阴分阳迭用柔刚”三句,先儒皆就《易》上说,细玩文义,当且就造化上说,“兼”字“分”字“用”字,皆不是著力字,言合三才之道而皆两,此易所以六画成卦也,三才之道,既以相对而分,又以更迭而用,此易所以六位成章也,如此方于故易两字语气相合,蔡氏说极贴。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
本义 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离东坎西,兑居东南,震居东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于是八卦相交而咸六十四卦,所谓先天之学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此一节就卦象明重卦之意,若使天地不交,水火异处,则庶类无生成之用,品物无变化之理,故云“天地定位”而合德,山泽异体而通气,雷风各动而相薄,水火不相入而相资,八卦之用,变化如此,故圣人重卦,令八卦相错,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莫不交互,以象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莫不交错,则《易》之爻卦与天地等,性命之理,吉凶之数,既往之事,将来之几,备在爻卦之中矣。
项氏安世曰:八卦虽八,实则“阴阳”二字而已,是故位虽定而气则通,势虽相薄而情不厌,明本一物也。
龚氏焕曰:“定位”以体言,“通气”“相薄”不“相射”以用言。天地,乾坤之定体,水火,乾坤之大用,山泽之气,即水之气,雷风之气,即火之气,而水火之气,又天地之气也。
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
本义 起震而历离兑,以至于乾,数已生之卦也,自巽而历坎艮,以至于神,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则以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为次,故皆“逆数”也。
此第三章。
集说 《朱子语类》云:先天图曲折,细详图意,若自乾一横排至坤八,此则全是自然,故说卦云“《易》逆数”也,若如圆图,则须如此方见阴阳消长次第,虽似稍涉安排,然亦莫非自然之理,自冬至至夏至为顺,盖与前逆数若相反,自夏至至冬至为逆,盖与前逆数者同,其左右与今天文家说左右不同,盖从中而分,其初若有左右之势尔。
陈氏埴曰:《易》本“逆数”也,有一便有二,有二便有四,有四便有十六,以至于六十四,皆由此可以知彼,由今可以知来,故自乾一以至于坤八,皆循序而生,一如横图之次,今欲以圆图象浑天之形,若一依此序,则乾坤相并,寒暑不分,故伏羲以乾坤定上下之位,坎离列左右之门,艮兑震巽,皆相对而立,悉以阴阳相配,自一阳始生,起冬至节历离震之间为春分,以至于乾为纯阳,是进而得其已生之卦,如今日复数昨日, 胡氏炳文曰;诸儒训释,皆谓已往而易见为顺,未来而前知为逆,《易》主于前民用,故曰“《易》逆数也”。唯《本义》依邵子,以数往者顺一段为指圆图,而言卦气之所以行,“易逆数”一段为指横图,而言卦画之所以生,非《本义》发邵子之蕴,则学者孰知此所谓先天之学哉。
案 此节顺逆之义,朱子之意如此,然与邵子本意,各成一说,盖邵子本意,以三阴三阳,追数至一阴一阳处为顺,自一阴一阳,渐推至三阴三阳处为逆,朱子则谓左方四卦数已生者为顺,右方四卦推未生者为逆,两说可并存。而邵子之说,于此两章文义,尤为贯串,“天地定位”一节,自乾坤说到震巽,是“数往”也。雷以动之一节,自震巽说到乾坤,是“知来”也,此三句,是承上节以起下节,言图象数往则顺,知来则逆,如上节所列是顺数,顺数者尊乾坤次六子也,若建图之意,则欲见阴阳之运行,功用之先后,所重在逆数,如下节所推也,诸说之详,备《启蒙》中。
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晅亘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本义 此卦位相对,与上章同。
此第四章。
集说 孔氏颖达曰:上四举象,下四举卦者,王肃云,互相备也。
张子曰:阴性凝聚,阳性发散,阴聚之,阳必散之,其势均散,阳为阴累,则相持为雨而降,阴为阳得,则飘扬为云而升,故云物班布太虚者,阴为风驱,敛聚而未散者也,凡阴气凝聚,阳在内者不得出,则奋击而为雷霆,阳在外者不得入,则周旋不舍而为风,其聚有远近虚实,故雷风有大小暴缓,和而散,则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则为戾气曀霾,阴常散缓,受交于阳,则风雨调,寒暑正。
朱氏震曰:前说乾坤以至“六子”,此说“六子”而归乾坤,终始循环,不见首尾,《易》之道也。
《朱子语类》云:“雷以动之”以下四句,取象义多,故以象言,“艮以止之”以下四句,取卦义多,故以卦言。
项氏安世曰:自“天地定位”至“八卦相错”,言先天之顺象也,自“雷以动之”至“坤以藏之”,言先天之逆象也。
胡氏炳文曰:此章卦位相对与上章同,特上章先之以乾坤,此章则终之以乾坤也。
金氏贲亨曰:上章以天地居首,序尊卑也,此章以乾坤居后,总成功也,上以体言,此以功用言也。
吴氏曰慎曰:前章始乾坤终坎离,此章始震巽终乾坤,首乾者其重在乾,首震者其重在震,二章虽皆明先天卦序,而后天始震之义,亦具其中矣。
又案 艮兑不言山泽,则是指气言也,暑气温热发生,故曰“兑以说之”。寒气严凝收敛,故曰“艮以止之”,上传于雷霆风雨之下,亦曰“一寒一暑”,而不言山泽也,若雷以动积寒之气,而“日以晅之”,风以散积暑之气,而“雨以润之”,则于卦象皆切,乾君坤藏,亦主大夏大冬而言,大夏如下章所云“万物皆相见”,“向明而治”,是君之也,大冬如下章所云“万物之所归”,是藏之也。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
本义 帝者天之主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谓后天之学也。
集说 程子曰:《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说,先儒以为乾位西北,坤位西南,乾坤任六子而自处于于为之地,此大故无义理,雷风山泽之类,便是天地之用,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岂可谓手足耳目皆用,而身无为乎。
何氏楷曰:三男震坎艮,以次纲纪于始终,三女巽离兑,以次而处纲纪之内,自东南至西皆阴,自西北至东皆阳,亦最齐整,故坤蹇彖辞,有西南东北之语。
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
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本义 上言帝,此言万物之随帝以出入也。
此第五章,所推卦位之说,多未详者。
集说 郑氏康成曰:“万物出乎”震雷发声以生之也,“齐乎巽”,风摇动以齐之也。
洁,犹新也。“万物皆相见”,日照之使光大,万物皆致养,地气含养,使秀实也,万物 程子曰:艮,止也,生也。止则便生,不止则不生,此艮终始万物。
又曰:冬至一阳生,每遇至后则倍寒何也,阴阳消长之际,无截然断绝之理,故相搀掩过,如天将晓,复至阴黑,亦是理也,大抵终始万物盛乎艮,此尽神妙,须研穷此理。
郑氏樵曰:乾居西北,父道也,父道尊严,严凝之气,盛于西北。西北者,万物成就之方也。坤居西南,母道也,母道在养育万物,万物之生,盛于西南。西南者,万物长养之方也。坎艮震方位次于乾者,乾统三男也,巽离兑方位夹乎坤者,坤统三女也。
西北盛阴用事,而阴气盛矣,非至健莫能与争,故阴阳相薄,曰“战乎乾”,而乾位焉,战胜则阳气起矣。
杨氏万里曰:于帝言“致役”者。盖坤,臣也。帝,君也。君之于臣,役之而已,于万物言致养者。盖坤,母也,万物,子也,母之于子,养之而已,至于它卦不言战而乾言战。乾,西北之卦,阴盛阳微之时,阴疑子阳也,不然,则《坤》之上六,何以言“龙战于野”。
项氏安世曰:后天之序,据太极既分之后,播五行于四时也,震巽二木主春,故震在东方,巽东南次之,离火主夏,故为南方之卦,兑乾二金主秋,故兑为正秋,乾西北次之,坎水主冬,故为北方之卦,土王四季,故坤土在夏秋之交,为西南方之卦,艮土在冬春之交,为东北方之卦,木金土各二者,以形王也,水火各一者,以气王也,坤阴土,故在阴地,艮阳土,故在阳地,震阳木,故正东,巽阴木,故近南而接乎阴,兑阴金,故正西,乾阳金,故近北而接乎阳,其序甚明。
徐氏几曰:坎离,天地之大用也,得乾坤之中气,故离火居南,坎水居北也。震,动也,物生之初也,故居东。兑,说也,物成之后也,故居西。此四者各居正位也,震属木,巽亦属木,震阳木也,巽阴木也,故巽居东南,巳之位也。兑属金,乾亦属金,兑阴金也,乾阳金也,故乾居西北,亥之方也。坤艮皆土也,坤阴土,艮阳土,坤居西南,艮居东北者,所以均王乎四时也。此四者分居四隅也,后天八卦以震巽离坤兑乾坎艮为次者,震巽属木,木生火,故离次之,离火生土,故坤次之,坤土生金,故兑乾次之,金生水,故坎次之,水非土亦不能以生木,故艮次之,水土又生木,木又生火,八卦之用,五行之生,循环无穷,此所以为造化流行之序也。
龚氏焕曰:土之于物,无时而不养,今独言致役乎坤何也?曰:土之养物,虽无时不然,然于西南夏秋之交,物将成就之时,土气正旺,致养之功,莫盛于此,故曰“致役乎坤”,非它时不养,而独养乎此也,故又曰“成言乎艮”。艮亦土也,养者成之渐,成者养之终,成而终者又将于此而始,此土无不在,其于养物之功,成始而成终者也,水火一而木金土二者,水火阴阳之正,木金土阴阳之交,正者一而交者二也。
胡氏炳文曰:离明以德言,八卦之德可推,坤地坎水以象言,八卦之象可推,兑秋 俞氏琰曰:艮,止也,不言止而言成,盖止则生意绝矣,成终而复成始,则生意周流,故曰“成言乎艮”。
陈氏琛曰:火气极热,物无由而成,水气极寒,物无由而生,唯土气最为中和,故火金之交有坤土,水木之交有艮土,而为万物之所由出入者也,养身养民治天下,皆要中和。
张氏振渊曰:成始只在成终内,无两截事。
吴氏曰慎曰:气不翕聚,则不能发散,物未坚实,则不能复种而生,未有不能成终而能成始者也,此贞下起元之理,主静立本之道,盖必体立而后用有以行,天地人物,其理一也。
案 此章明文王卦位也,震动而发散者,生机之始,雷厉而风行者,造化之初,是故阳气奋而物无不出,阴气顺而物无不齐,阳气盛,而于阴则明极矣,阴精厚,顺于阳则养至矣,阳之和足于内,阴之滋足于外,则说乎物而物成矣,虽然,天之道资阴而用之而功乃就,克阴而化之而命斯行,自始至终,莫非天也,而终始之际,见其健而不已焉者,天之所以为天也,由是役者于此休,故坎以习熟之义而司劳焉,动者于此止,故艮以动静不穷之义而司成焉,夫文之位变乎羲矣,而其体用交错之妙,动静互根之机,则必合而观之,然后造化之理尽。
孔子所以释文王之意者,如此而已,诸儒或以五行言之,说亦详密,故备载以相参考,然诸儒所言坤艮之理,亦有未尽者,盖吕令以土独王未月而为中央,则土位唯一也。
京房以土分王辰戍丑未而直四季,则土位有四也,今文王之卦,唯坤艮二土,位于丑未,视月令则多其一,视京房则少其二,何也?盖木之生火,金之生水,无所藉于土,若火非土,必不能成金,水非土,必不能生木,则土之功于是为著,又一岁之间,阴阳二气,皆互相胜,阳胜阴,则为木之温,火之热,自卯至未,阳多之卦是也,阴胜阳,则为金之凉,水之寒,自酉至丑,阴多之卦是也,唯丑接于寅,未接于申,为三明三阳之卦,则二气适均,而为中和之会,此所以独为土德之居也,其精义亦非诸术所及,尚有先天后天列象交变之妙,见《启蒙》附论中。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桡万物者莫痰乎风,燥万物者莫熯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
本义 此去乾坤而专言“六子”,以见神之所为,然其位序亦用上章之说,未详其义。
集说 韩氏伯曰:于此言“神”者,明八卦运动,变化推移,莫有使之然者,神无物,妙万物而为言,则雷疾风行,火炎水润,莫不自然相与为变化,故能万物既成也。
崔氏憬曰:此言六卦之用,而不及乾坤者,以天地无为而无不为,故能成雷风等有为之神妙也,艮不言山,独举卦名者,以动桡燥润,功是雷风水火,至于终始万物,于山义则不然,故言卦,而余皆称物,各取便而论也,。
朱氏震曰:张子云,一则神,两则化。妙万物者,一则神也,且动桡燥说润终始万物者,孰若六子,然不能以独化,故必相逮也,不相悖也,通气也,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合则化,化则神。
项氏安世曰;动桡燥说润盛,皆据后天分治之序,而相逮不相悖,通气变化,复据先天相合之位者,明五气顺布,四季分王之时,无极之真,二五之精,所以妙合而凝者,未始有戾于先天之事也。
又曰:泽不为润而为“说”者,“润”者,气之湿而在内者也;“说”者,色之光而在外者也。泽气上浮而光溢于外,故说而可爱,若润物之功,淫液而深长,则唯水足以当之。
吴氏澄曰:此承上章文王卦位之后,而言六卦之用,不言乾坤者,乾坤主宰万物之帝,行乎六子之中,所谓“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万物有迹可见,而神在其中,无迹可见,然神不离乎物也,即万物之中而妙不可测者,神也,故曰“妙万物”。雷之所以动,风之所以桡,火之所以燥,泽之所以说,水之所以润,艮之所以终始,皆乾坤之神也,动者发萌启蛰震之出也,桡者吹拂长养,巽之齐也,燥者炎赫暴炙,离之相见也,说者欣怿充实,兑之说也,润者滋液归根,坎之劳也,终始者贞下起元,艮之成也。
胡氏炳文曰:以上第三章第四章,言先天,第五章言后天,此第六章,则由后天而推先天者也,去乾坤而专言六子,以见神之所为,言神则乾坤在其中矣,雷之所以动,风之所以桡,以至艮之所以终所以始,后天之所以变化者,实由先天而来,先天水火相逮,以次阴阳之交合,后天雷动风桡,以次五行之变化,唯其交合之妙如此,然后变化之妙亦如此。
俞氏琰曰:物之方萌,“雷以动之”,萌而未舒,风以桡之,舒而尚柔,火以燥之,及其长也,泽以说其外,水以润其内,既说且润矣,于是“艮以止之”,止则终,终则复始,此“六子”各一其用,而其所以成万物者如是也,乃若能变能化,毕成万物,则又在乎两相为用,“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
粱氏寅曰:神,即帝也,帝吝神之体,神者帝之用,故主宰万物者,帝也,所以“妙万物”者,“帝”之神也。
蔡氏清曰:如雷青于动,风青于桡,则滞于一隅,不得谓之妙,天地则役使六子,以造化乎万物,而六子之伸缩变化,皆天地之为也,所以谓神当乾坤也,于此盖可以验合一不测之义,无在无不在之意,盖神如君后,“六子”则六官之分职也,六官所施行皆帝后所主宰,然后六职交举而治功成矣。
案 此章合羲文卦位而总赞之,盖变易之序,后天为著,而变易之理,先天为明,变易者化也,“动万物”、“桡万物”、“燥万物”,“说万物”、“润万物”、“终始万物”者也,变易者神也,所以变变化化,道并行而不相悖,使物并育而不相害者也,化者造物之迹也,统乎地者也,故以其可见之功而谓之成,神者生物之心也,统乎天者也,故以其不测之机而谓之妙。
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
本义 此言八卦之性情。
此第七章。
集说 孔氏颖达曰:此一节说八卦名训。乾象天,天体运转不息,故为健;坤象地,地顺承于天,故为顺;震象雷,雷奋动万物,故为动;巽象风,风行无所不入,故为入;坎象水,水处险陷,故为陷;离象火,火必著于物,故为丽;艮象山,山体静止,故为止;兑象泽,泽润万物,故为说。
邵子曰:乾,奇也,阳也,健也,故天下之健莫如天;坤,偶也,阴也,顺也,故天下之顺莫如地,所以顺天也;震,起也,一阳起也,起,动也,故天下之动莫如雷;“坎,陷也”,一阳陷于二阴,陷,下也,故天下之下莫如水:“艮,止也”,一阳于是而止也,故天下之止莫如山;“巽,入也”,一阴入二阳之下,故天下之入莫如风;“离,丽也”,一阳丽于二阳,其卦错然成文而华丽也,天下之丽莫如火,故又为附丽之丽;“兑,说也”,一阴出于外而说于物,故天下之说莫如泽。
张子曰:阳陷于阴为水,附于阴为火。
又曰:一陷溺而不得出为坎,一附丽而不能去为离。
《朱子语类》云: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尽于八卦,而震巽坎离艮兑,又总于乾坤,曰“动”曰“陷”曰“止”,皆健底意思,曰“入”曰“丽”曰“说”,皆顺底意思,圣人下此八字,极状得八卦性情尽。
项氏安世曰:健者始于动而终于止,顺者始于入而终于说,阳之动,志于得所止,阴之入,志于得所说。
蔡氏清曰:自震而艮者,刚之由动而静也,自巽而兑者,阴之由静而动也,坎离在中间,坎则自动而向于静也,离则自静而向于动也。
案 八卦以卦画定名义在先,取象于雷风山泽等在后,孔氏之说,固不如邵子之说矣,然邵子说三阳卦,则既得之,其说三阴卦,以巽为阴入于阳,离为阴附于阳,则似未合经义盖阴在内。阳必入而散之,阴在中,阳必附而散之,入与丽皆阳也,特以先有 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
本义 远取诸物如此。
此第八章。
集说 孔氏颖达曰:此一节略明远取诸物也,乾象天,天行健,故为马;坤象地,任重而顺,故为牛;震动象,龙动物故为龙;巽主号令,鸡能知时,故为鸡;坎主水渎,豕处污湿,故为豕;离为文明,雉有文章,故为雉;艮为静止,狗能善守,禁止外人,故为狗;兑说也。王廙云,羊者顺之畜,故为羊也。
项氏安世曰:健者为马,顺者为牛,善动者为龙,善伏者为鸡,质躁而外污者为豕,质野而外明者为雉,前刚而止物者为狗,内很而外说者为羊。
又曰:造化权舆云,乾阳物也,马故蹄园,坤阴物也,牛故蹄折,阳病则阴,故马疾则卧,阴病则阳,故牛疾则立,马阳物,故起无前足,卧先后足,牛阴物,故起先后足,卧先前足。
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本义 近取诸身如此。
此第九章。
集说 孔氏颖达曰:此一节略明近取诸身也,乾尊而在上,故为“首”。坤能包藏含容,故为“腹”。足能动用,故“震为足”也。股随于足,则巽顾之谓,故“巽为股”也。坎北方之卦主听,故“为耳”也。离南方之卦主视,故“为目”也。艮既为止,手亦能止持其物,故“为手”也。兑主言语,故“为口”也。
龚氏原曰:其外园,诸阳之所聚者,首也,其中宽,众阴之所藏者,腹也,足则在下而善动,股则从上而善随,耳则内阳而聪,目则外阴而明,在上而止者乎也,在外而说者口也。
余氏芑舒曰:首以君之,腹以藏之,足履于下为动,手持于上为止,股下歧而伏,口上窍而见,耳外虚,目内虚,各以反对也。
案 诸儒说股义,唯余氏得之,盖股者阴所伏也。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加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者,以其画之次序言也。
又云:一索再索之说,初间画卦时也不恁地,只是画成八卦后,便见有此象耳。
项氏安世曰:乾坤“六子”,初为气,末为形,中为精,雷风气也,山泽形也,水火精也。
吴氏澄曰:万物资始于天,犹子之气始于父也,资生于地,犹子之形生于母也,故“乾称父,坤称母”。索,求而取之也。坤交于乾,求取乾之初画中画上画,而得长中少三男,乾交于坤,求取坤之初画中画上画,而得长中少三女。“一索”,谓交初。“再索”,谓交中。“三索”,谓交上。以索之先后,为长中少之次也。
胡氏炳文曰:此章本义,乃朱子未改正之笔,当以语录说为正,若专言揲蓍求卦,则无复此卦序矣。
俞氏琰曰:“一索”、“再索”、“三索”,盖以三画自下而上之次序言。称者,尊之之辞。谓者,卑之之辞。
案 以上四章,皆言八卦之德之象,而健顺动入陷丽止说诸德,则名卦之义,易理之根也,不言雷风山泽诸象者,为前图位中已具。
乾求坤坤求乾之说,当从吴氏,《朱子语类》记录偶误。
乾为天,为环,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
本义 《荀九家》此下有为龙,为直,为衣,为言。
集说 孔氏颖达曰:此一节广明乾象。乾既为人,大动运转,故为“环”,“为君为父”,取其尊道而为万物之始也;“为玉为金”,取其刚之清明也;“为寒为冰”,取其西北寒冰之地也;“为大赤”,取其盛阳之色也;“为良马”取其行健之善也;“老马”,取其行健之久也;“瘠马”,取具行健之其;瘠马,骨多也;“驳马”有牙如锯,能食虎豹,取其至健也;“为木果”,取其果实著木,有似星之著天也。
邵子曰:木结实而种之,又成是木而结是实,木非旧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此实生生之理也。
郭氏雍曰:“果”者“木”之始也,“木”以“果”为始,犹物以乾为始也。
程氏迥曰:“为环”,天之体也;“为君”居上而覆下也;“为玉”,德粹也;“为金”,坚刚也;“为寒”,位西北也;“为冰”,寒之凝也;“为木果”,以实承实也。
《朱子语类》云;卦象指文王卦言,所以乾言为寒为冰。
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
集说 孔氏颖达曰:此一节,广明坤象。坤既为地,地受任生育,故“为毋也”;“为布”,取其广载也;“为釜”,取其化生成熟也:“为吝墙”,取其生物不转移也;“为均”,地道平均也;“为子母牛”,取其多蕃育而顺之也;“为大舆”,取其载万物也;“为文”,取其万物之色杂也;“为众”,取其载物非一也;“为柄”,取其生物之本也;“为黑”,取其极阴之色也。
崔氏憬曰:遍布万物于致养,故“坤为布”,地生万物,不择美恶,故“为均”也,万物依之为本,故“为柄”。
项氏安世曰:“吝啬”其静之翕,均其动之辟也,乾质故坤文,乾一故坤众。
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为旉,为大涂,为长子,为决躁,为苍筤竹,为萑苇,其于马也,为善鸣,为馵足,为作足,为的颡,其于稼也,为反生,其究为健,为蕃鲜。
本义 《荀九家》有为玉、为鹄、为鼓。
集说 虞氏翻曰:“天玄地黄”,震天地之杂,故为“玄黄”。
孔氏颖达曰:此一节广明震象。“为玄黄”,取其相杂而成苍色也;“为敷”,取其春时气至;草木皆吐,敷布而生也;“为大涂”,取其万物之所生也;“为长子”,震为长子也;“为决躁”,取其刚动也;“为苍筤竹”,竹初生色苍也;“为萑苇”,竹之类也;“其于马也”,为善明,取雷声之远闻也;“为馵足”,马后足自为馵,取其动而见也;“为作足”,取其动而行健也;“为的颡”,白额为的颡,亦取动而见也;“其于稼也,为反生”,取其始生戴甲而出也。“其究为健”,极于震动则为健也;“为蕃鲜”,取其春时草木蕃育而鲜明。
俞氏琰曰:阳长而不已,则其穷为乾之健,三爻俱变则为巽,故“为蕃鲜”。
蔡氏清曰:凡嫁之始生,皆为“反生”,盖以其初间生意实从种子中出,而下著地以为根,然后种中萌芽乃自举。
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为工,为白,为长,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臭,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为近利市三倍,其究为躁卦。
本义 《荀九家》有为杨为鹳。
集说 翟氏玄曰:“为绳直”,上二阳其正一阴,使不得邪僻,如绳之直也。
孔氏颖达曰:此一节广明巽象。巽为木,木可以輮曲直,巽顺之谓也;“为绳直”,取其号令齐物也;“为工”,亦取绳直之类;“为白”,取其洁也:“为长”,取其风行之远也;“为高”,取其木生而上也;“为进退”,取其风性前却;“为不果”,亦进迟之义也;“为臭”,取其风所发也;“为寡发”,风落树之华叶,则在树者稀疏,如人之少发;“为广颡”,额阔发寡少之义;“为多白眼”,取躁人之眼,其色多白也;“为近利”,取躁人 其风之势极于躁急也。
项氏安世曰:绳直其齐,白其洁也。
案 “寡发”、“广颡”、“多白眼”,皆取洁义,今人之额阔少寒毛而眸子清明者,皆洁者也。
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为矫輮,为弓轮,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为通,为月,为盗,其于木也,为坚多心。
本义 《荀九家》有为宫,为律,为可,为栋,为丛棘,为狐,为蒺藜,为桎梏。
集说 宋氏衷曰:曲者更直为矫,直者更曲为輮,水流有曲直,故为“矫輮”,“为美脊”,阳在中央,马脊之象也。
孔氏颖达曰:此一节广明坎象。“坎为水”,取其北方之行也;“为沟渎”,取其水行无所不通也;“为隐伏”,取其水藏地中也;“为輮矫,使曲者直为矫,使直者曲为輮,水流曲直,故为“矫輮”也;“为弓轮”,弓者激矢如水激射也,轮者运行如水行也;“为加忧”,取其忧险难也;“为心病”,忧险难故心病也;“为耳痛”,坎为劳卦,听劳则耳痛也;“为血卦”,人之有血,犹地有水也;“为赤”,亦取血之色;“其于马也,为美脊”,取其阳在中也;“为亟心”,亟,急也,取其中坚内动也;“为下首”,取其水流向下也;“为薄蹄”,取水流迫地而行也;“为曳”,取水磨地而行也;“其于舆也,为多眚”,取其表里有阴,力弱不能重载也;“为通”,取行有孔穴也;“为月”,月是水之精也;“为盗”,取水行潜窃也;“其于木也,为坚多心”,取刚在内也。
郑氏正夫曰: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间,故为“血卦。”蔡氏清曰:日火外影也,金水内影也,月是金水之精,何独外影,曰,月体亦内影,坎象也,得日之光以为光,故兼外影耳,凡金与水得日之光,亦光辉外射也。
案 坎以习险取“劳”义,故“加忧”、“心病”、“耳痛”者,人之劳也。“亟心”、“下首”、“薄蹄”、“曳”者,马之劳也。多眚者,车之劳也。凡马劳极,则心亟而屡下其首,蹄薄而足曳,皆历险之甚所致也。
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胄,为戈兵,其于人也,为大腹,为乾卦,为鳖,为蟹,为蠃,为蚌,为龟,其于木也,为科上搞。
本义 《荀九家》有:为牝牛。
集说 孔氏颖达曰:此一节广明离象。“离为火”,取南方之行也;“为日”,日是火精也;“为电”,火之类也;“为中女”,离为中女:“为甲胄”,取其刚在外也:“为戈兵”,取其以刚自捍也;“其于人也,为大腹”,取其怀阴气也; ”为乾卦”,取其日所烜也;“为鳖,为蟹,为蠃,为蚌,为龟”皆取刚在外也;“其于木也,为科上槁”。科,空也。阴在内为空,木既空中,上必枯槁也。
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阙,为果藤,为阍寺,为指,为狗,为鼠,为黔喙之属,其于木也,为坚多节。
本义 《荀九家》有为鼻,为虎,为狐。
集说 宋氏衷曰:阍人主门,寺人主巷,艮为止,此职皆掌禁止者也。
虞氏翻曰:“为山”,故为径路也。艮手,故“为指”。阳刚在上,故“坚多节”。
孔氏颖达曰:此一节广明艮象。“艮为山”,取阴在下为止,阳在上为高,故艮象山也;“为径路”,取其山路有涧道也;“为小石”,取其艮为山,义为阳卦之小者也;“为门阙”,取其崇高也;“为果蓏”,木实为果,草实为蓏,取其出于山谷之中也,“为阍寺”,取其禁止人也;“为指”,取其执止物也;“为狗”,“为鼠”,取其皆止人家也;“为黔喙之属”,取其山居之兽也;“其于木也,为坚多节”,取其坚凝故多节也。
项氏安世曰:“震为敷为蕃鲜”,草木之始也,“艮为果蓏”、草木之终也,果蓏能终而又能始,故于艮之象为切。
俞氏琐曰:《周官阍人》掌王宫中门之禁,止物之不应入者。寺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官之戒令,止物之不得出者,坎之刚在内,故为木之“坚多心”,艮之刚在外,故为木之“坚多节”。
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为毁折,为附决。其于地也,为刚卤,为妾,为羊。
本义 《荀九家》有为常,为辅颊。
此第十一章。广八卦之象,其间多不可晓者,求之于经,亦不尽合也。
集说 孔氏颖达曰:此一节广明兑象。“兑为泽”,取其阴卦之小,地类卑也:”为少女”,兑为少女也;“为巫”,取其口舌之官也;“为门舌”,取西方于五事而言也;“为毁折”,“为附决”,兑西方之卦,取秋物成熟,稿秆之属,则“毁折”也;果砧之属,则“附决”也;“其于地也,为刚卤”,取水泽所停,刚咸卤也;“为妾”,取少女从姊为娣也。
总论 项氏安世曰:此章推广象类,使之明备,以资占者之决也。
胡氏炳文曰:此章广八卦之象,几百十有二,其中有相对取象者,如乾为天坤为地之类是也,上文“乾为马”;此则“为良马”、“老马”、“瘠马”、“驳马”,上文“坤为牛”,此则“为子母牛”,“乾为木果”,结于上而园,“坤为大舆”,载于下而方,“震为决躁”,“巽为进退为不果”,刚柔之性也,震巽独以其究言,刚柔之始也,坎内阳外阴,水与月刚内明外暗,离内阴外阳,火与日则内暗外明,坎中实,故于人“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离中虚,故于人为“大腹”,艮为“阍寺”“为指”,艮之止也,“兑为巫”“为口舌”,阴之说也;有相反取象者,“震为大涂”,反而艮则“为径路”,“巽为长为高”,反而兑则“为毁折”;有相因取象者,“乾为马”,震得乾初之阳,故于马“为善鸣”、“馵 案 此章虽广八卦之象,然有前文所取,而此反不备者,则非广也,意前为历代相传,而此则《周易》义例与。
序卦传集说 孔氏颖达曰:韩康伯云,《序卦》之所明,非《易》之蕴也,盖因卦之次,托象以明义,今验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即变。覆者,表里视之,遂成两卦,《屯》、《蒙》、《需》、《讼》、《师》、《比》之类是也。变者反覆惟成一卦,则变以对之,《乾》、《坤》、《坎》、《离》、《大过》、《颐》、《中孚》、《小过》之类是也,且圣人本定先后,若元用孔子序卦之意,则不应非覆即变,然则康伯所云,因卦之次,托象以明义,盖不虚矣。
张子曰:《序卦》相受,圣人作《易》,须有次序。
《朱子语类》:问:《序卦》或以为非圣人之书,信乎?曰:此沙随程氏之说也,先儒以为非圣人之蕴,某以为非圣人之精则可,谓非《易》之蕴则不可,周子分“精”与“蕴”字甚分明,《序卦》却正足《易》之蕴,事事夹杂,都有在里面。问如何谓《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极,足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是《易》之精。
问如《序卦》中亦见消长进退之义,唤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夹杂有在里面,正是蕴,须是自一个生出来以至于无穷,便是精。、问《易》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多寡不均,何也?曰:卦有正对,有反对,《乾》、《坤》、《坎》、《离》、《颐》、《大过》、《中孚》、《小过》八卦,正对也,正对不变,故反覆观之,止成八卦,其余五十六卦,反对也,反对者皆变,故反覆观之,共二十八卦,以正对卦合反对卦观之,总而为三十六卦,其在上经,不变卦凡六,《乾》、《坤》、《坎》、《离》、《颐》、《大过》是也,自《屯》、《蒙》而下二十四卦,反之则为卜二,以十二而加六,则十八也。其在下经,不变卦凡二,《中孚》、《小过》是也, 缄》、《恒》而下三十二卦,反之则为十六,以十六加二,亦十八也,其多寡之数,则未尝不均也。
问《序卦》中有一,二不可晓处,如六十四卦,独不占《咸》卦,何也?曰:夫妇之道即咸也。问恐亦如上经不言乾坤,但言天地则乾坤可见否。曰:然。
项氏安世曰:《易》之称上下经者,未有考也,以《序卦》观之,二篇之分,断可知矣。
案 卦之所以序者,必自有故,而孔予以义次之,就其所次,亦足以见天道之盈虚消长,人事之得失存亡,国家之兴衰理乱,如孔氏朱子之言皆是也,然须知若别为之序,则其理亦未尝不相贯,如蓍筮之法,一卦可变为六十四卦,随其所遇而其贞与悔皆可以相生,然后有以周义理而极事变,故曰天下之能事毕也,孔子盖因《序卦》之次以明例,所谓举其一隅焉尔,神而明之,则知《易》道之周流而趋时无定,且知筮法之变通而触类可长,此义盖《易》之旁通至极处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屯”不训盈也,当屯之时,刚柔始交,天地絪緼,雷雨动盪,见其气之充塞也,是以谓之盈尔,故谓之盈者其气也,谓之物之始生者其时也,谓之难者其事也,若屯之训,纷纭盘错之义云尔。
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
集说 孔氏颖达曰:上言“屯者盈也”,释《屯》次乾坤,其言已毕,更言“屯者物之始生者”,开说下“物生必蒙”,直取始生之意,非重释《屯》之名也。
朱氏震曰:蒙,冥昧也,物生者必始于冥昧,勾萌胎卵是也,故次之以《蒙》。蒙,童蒙也,物如此稚也。
又曰:“饮食必有讼”,乾糇以愆,豕酒生祸,有血气者,必有争心,故次之以《讼》。
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比者,比也。
集说 韩氏伯曰:众起而不比,则争无由息,必相亲比,而后得宁。
项氏安世曰:《师》、《比》二卦相反,师取伍两卒旅师军之名,比取比闾族党州乡之名,师以众正为义,比以相亲为主。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
本义 晁氏云,郑无“而泰”二字。
集说 姚氏信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有礼然后泰,泰然后安也。
项氏安世曰:“履”不训礼,人所履,未有外于礼者,外于礼,则非所当履,故以履为有礼也,上天下泽,亦有礼之名分焉。
胡氏一桂曰:《乾》、《坤》至《履》十变,阴阳之气一周矣。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
本义 郭氏雍曰;以谦有大,则绝盈满之累,故优游不迫而暇豫也。
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
事者,其肯随乎。
项氏安世曰:“蛊”不训事,物坏则万事生矣,事因坏而起,故以蛊为事之先。
又曰:“临”不训大,大者以上临下,以大临小。凡称“临”者,皆大者之事,故以“大”释之,若丰者大也,则真训大矣。
吴氏澄曰:因蛊之有事,而后有临之盛大也。
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
集说 崔氏憬曰:言德业大者,可以观于人也。
苏氏轼曰: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际,所谓合也,直情而行谓之苟,礼以饰情谓之贲,苟则易合,易则相渎,相渎则易以离,贲则难合,难合则相敬,相敬则能久,饰极则文胜而实衰,故《剥》。
张氏栻曰:贲饰则贵于文,文之太过,则又灭其质而有所不通,故致饰则亨有所尽。
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集说 崔氏憬曰:物复其本,则为诚实,故言《复》则《无妄》矣。
周子曰:不善之动,妄也。妄复则无妄矣,无妄则诚矣,故《无妄》次《复》。
郭氏忠孝曰:健为天德,大畜止健,畜天德也,故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不能畜天德,则见于有为者,不能无妄,故天德止于大畜,而动于无妄也。
阎氏彦升曰:“无妄然后可畜”,所畜者在德,故曰大。
余氏芑舒曰:自有事而大。大而可观,可观而合,合而饰,所谓忠信之薄而伪之始也,故一变而为剥,《剥》而《复》,则真实独存而不妄矣。
何氏楷曰:不妄与无妄当辨,由不以妄然后能无妄也。
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
集说 苏氏轼曰:养而不用,其极必动,动而不已,其极必过。
阎氏彦升曰:养者君子所以成已,动者君子所以应物,然君子处则中立,动则中立,岂求胜物哉,及其应变,则有时或过,故受之以《大过》。
林氏希元曰:不专一则不能直遂,不翕聚则不能发散,故必有养然后能动,不养则不可以动。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即此理也,或受之以《大过》,大过 姜氏宝曰:无所养则其体不立,不可举动以应大事,惟养充而动,动必有大过人者矣。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
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集说 干氏宝曰:此详言人道三纲六纪有自来也,人有男女阴阳之性,则自然有夫妇配合之道,阴阳化生,血体相传,则自然有父子之亲,以父立君,以子资臣,则必有君臣之位,有君臣之位,故有上下之序,有上下之位,则必礼以定其体,义以制其宜,明先王制作,盖取之于情者也。上经始于《乾》、《坤》,有生之本也;下经始于《咸》、《恒》,人道之首也。《易》之兴也,当殷之末世,有妲己之祸,当周之盛德,有三母之功,以言天不地不生,夫不妇不成,相须之至,王教之端,故《诗》以关睢为国风之始,而《易》于《咸》、《恒》,备论礼义所由生也。
《朱子语类》:问:“礼义有所错”,“错”字陆氏两音,如何?曰:只是作“措”字,谓礼义有所设施耳。
吴氏澄曰:此言《咸》所以为下经之首也,夫妇谓《咸》卦,先言天地万物男女者,有夫妇之所由也,后言父子君臣上下者,有夫妇之所致也,有夫妇,则其所生为父子,由家而国,虽非父子也,而君尊臣卑之分,如父子也,由国而天下,虽非君臣,而上贵下贱之分,如君臣也,礼义所以分别尊卑贵贱之等。错,犹置也。《乾》、《坤》、《咸》不出卦名者,以其为上下经之首卦,特别言之。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终遯,故受之以《大壮》。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伤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集说 郭氏忠孝曰:“伤乎外者必反其家”,盖行有不得于人,则反求诸己。
阎氏彦升曰:知进而已,不知消息盈虚,与时偕行,则伤之者至矣,故受之以《明夷》,以利合者,迫穷祸患害相弃也,以天属者,迫穷祸患害相收也,《明夷》之伤,岂得不反于家人乎。
何氏楷曰:《晋》与《渐》皆进,进必有归者,先以艮,进必有伤者,先以壮也。
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
蹇者,难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
集说 周子曰:家人离必起于妇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项氏安世曰:凡言《屯》者,皆以为难,而《蹇》又称难者,卦皆有《坎》也,然《屯》“动乎险中”,行乎患难者也,《蹇》见险而止,但为所阻难,而不得前耳,非患难之难也,故居《屯》者,必以经纶济之,遇《蹇》者,待其解缓而后前。
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决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
姤者,遇也。
集说 朱氏震曰:益久必盈,盈则必决,堤防是已,故次之以《夬》。
胡氏一桂曰:《咸》、《恒》十变为《损》、《益》,亦犹《乾》、《坤》十变为《否》、《泰》也。
俞氏琰曰:损益盛衰,若循环然,损而不已,天道复还,故必益,益而不已,则所积满盈,故必决,此乃理之常也。《损》之后继以《益》,深谷为陵之意也,《益》之后继以《夬》,高岸为谷之意也。
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集说 崔氏憬曰:冥升在上则穷,故言“升而不已必困”也。
张氏栻曰:天下之物,散之则小,合而聚之,则积小以成其高大,故“聚而上者”为“升”也。
项氏安世曰:物相遇而聚者,彼此之情交相会也,以众言之也,比而有所畜者,系而止之也,自我言之也,畜有止而聚之义,聚者不必止也。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集说 朱氏震曰:井在下者也,井久则秽浊不食,治井之道,革去其古井者而已。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
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敌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
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
集说 阎氏彦升曰: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渐者进也,进必有归,何也?曰:晋所谓进者,有进而已,此进必有伤也,渐之所谓进者,渐进而已,乌有不得所归者乎。
朱氏震曰:前曰“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 ”,此曰“得其所归者必大”,《大有》次《同人》者,处大之道也,《丰》次《归妹》者,致大之道也。
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集说 郭氏雍曰:动极而止,止极复进,进极必伤,进以渐则有归,归得其所则大,穷其大则必失,盖非有大以谦故也。
张氏械曰:旅者“亲寡”之时,“无所容”也,唯巽然后得所入,故受之以《巽》,而巽者入也。
俞氏琰曰;大而能谦则豫,大而至于穷极,则必失其所安,故《丰》后继以《旅》。
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
涣者,离也。
集说 张氏栻曰:入于道故有见而说,故巽,而受之以《兑》。唯说于道,故推而及人,说而后散,故受之以《涣》。
项氏安世曰:人之情,相拒则怒,相人则说,故人而后说之。
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
集说 韩氏伯曰:孚,信也。既已有节,则宜信以守之,守其信者,则失贞而不谅之道,而以信为过,故曰《小过》也。
项氏安世曰:有其信,犹《书》所谓有其善,言以此自负而居有之也,自恃其信者,其行必果而过于中。
吴氏澄曰:过者行动而踰越之也,故《大过》云动,《小过》云行,凡行动未至其所为未及,既至其所为至,既至而又动又行,则为踰越其所至之地而过也。
蔡氏清曰:节而信之,必立为节制于此,上之人当信而守之,下之人当信而行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若果于自信,则于事不加详审,而在所必行矣,能免于过乎。
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
终焉。
集说 韩氏伯曰:行过乎恭,用过乎俭,可以矫世励俗,有所济也。
项氏安世曰:《大过》则踰越常理,故必至于陷。《小过》或可济事,故有济而无陷也。坎离之交,谓之《既济》,此生生不穷之所从出也,而圣人犹以为有穷也,又分之以为《未济》,此即咸感之后,继之以恒久之义也。盖情之交者,不可以久而无弊,故 总论 王氏通中说赞《易》至《序卦》曰:大哉时之相生也,达者可与几矣,至《杂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与存义矣。
邵子曰:《乾》、《坤》天地之本,《坎》、《离》天地之用,是以《易》始于《乾》、《坤》,中于《坎》、《离》,终于既《未济》,而《泰》、《否》为上经之中,《咸》、《恒》为下经之首,皆言乎其用也。
又曰:《乾》、《坤》、《坎》、《离》为上篇之用,《兑》、《艮》、《震》、《巽》为下篇之用也,《颐》、《中孚》、《大过》、《小过》为二篇之正也。
又曰:自《乾》、《坤》至《坎》、《离》,以天道也,自《咸》、《恒》至《既济》、《未济》,以人事也。
程子上下篇又曰:《乾》、《坤》天地之道,阴阳之本,故为上篇之首。《坎》、《离》阴阳之成质,故为上篇之终。《咸》、《恒》夫妇之道,生育之本,故为下篇之首。《未济》坎离之合,《既济》坎离之交,合而交则生物,阴阳之成功也,故为下篇之终。二篇之卦既分,而后推其义以为之次,《序卦》是也。卦之分则以阴阳,阳盛去居上,阴盛者居下。所谓盛者,或以卦,或以爻,卦与爻取义有不同,如《剥》以卦言,则阴长阳剥也。以爻言,则阳极于上,又一阳为众阴主也。如《大壮》以卦言,则阳长而壮,以爻言则阴盛于上,用各于其所,不相害也。乾父也,莫亢焉,坤母也,非乾无与为敌也,故卦有《乾》者居上篇,有《坤》者居下篇。而《复》阳生,《临》阳长,《观》阳盛,《剥》阳极,则虽有《坤》而居上,《姤》阴生,《遯》阴长,《大壮》阴盛,《遯》阴极,则虽有《乾》而居下,其余有乾者皆在上篇,《泰》、《否》、《需》、《讼》、《小畜》、《履》、《同人》、《大有》、《无妄》、《大畜》也。有坤而在上篇,皆一阳之卦也,卦五阴而一阳,则一阳为之主,故一阳之卦皆在上篇,《师》、《谦》、《豫》、《比》、《复》、《剥》也,其余有坤者,皆在下篇,《晋》、《明夷》、《萃》、《升》也。卦一阴五阳者,皆有乾也,又阳众而盛也,虽众阳说于一阴,说之而已,非如一阳为众阴主也。王弼云,一阴为之主,非也,故一阴之卦,皆在上篇,《小畜》、《履》、《同人》、《大有》也。卦二阳者,有坤则居下篇,《小过》虽无坤,阴过之卦也,亦在下篇,其余二阳之卦,皆一阳生于下而达于上,又二体皆阳,阳之盛也,皆在上篇,《屯》、《蒙》、《颐》、《习坎》也。阳生于下,谓震坎在下,震生于下也,坎始于中也,达于上,谓一阳至上,或得正位,生于下而上达,阳畅之盛也,阳生于下而不达于上,又阴众而阳寡复失正位,阳之弱也,《震》也《解》也,上有阳而下无阳,无本也,《艮》也,《蹇》也,《震》、《坎》、《艮》以卦言,则阳也,以爻言,则皆始变微也,而震之上艮之下无阳,坎则阳陷,皆非盛也,唯习坎则阳上达矣,故为盛。卦二阴者,有乾则阳盛可知,《需》、《讼》、《大畜》、《无妄》也,无乾而为盛者,《大过》也,《离》也,《大过》阳盛于中,上下之阴弱矣。阳居上下,则纲纪于阴,《颐》是也。阴居上下,不能主制于阳而反弱也,必上下各二阴,中唯两阳,然后为胜,《小过》是也,《大过》、《小过》之名可见也,离则二体上下皆阳,阴实丽焉,阳之盛也,其余二阳之卦,二体俱阴,阴盛也,皆在下篇,《家人》、《睽》、 项氏安世曰:上经言天地生万物,以气而流形,故始于《乾》、《坤》,终于《坎》、《离》,言气化之本也,下经言万物之相生,以形而传气,故始于《咸》、《恒》,终于《既济》、《未济》,言夫妇之道也。
蔡氏清曰:《序卦》之义,有相反者,有相因者,相反者,极而变者也,相因者,其未至于极者也,总不出此二例。
杂卦传集说 孔氏颖达曰:《序卦》依文王上下而次序之,此《杂卦》,孔子更以意错杂而对,辨其次第,不与《序卦》同。
《朱子语类》云:卦有反有对,《乾》、《坤》、《坎》、《离》是反,《艮》、《兑》、《震》、《巽》是对,《乾》、《坤》、《坎》、《离》,倒转也只是四卦,《艮》、《兑》、《震》、《巽》倒转则为《中孚》、《颐》、《小过》、《大过》,其余皆是对卦。
又云:八卦便只是六卦,《乾》、《坤》、《坎》、《离》是四正卦,《兑》便是翻转底《巽》,《震》便是翻转的《艮》,六十四卦,只八卦是正卦,余便只二十四卦,翻转为五十六卦,《中孚》是个双夹底离,《小过》是个双夹的《坎》,《大过》是个厚画底《坎》,《颐》是个厚画底《离》。
又云:三画之卦,只是六卦,即六画之卦,以正卦八,加反卦二十有八,为三十有六,六六三十六也,邵子谓之暗卦,小成之卦八,即大成之卦六十四,八八六十四也,三十六与六十四同。
乾刚坤柔,比乐师忧。
集说 苏氏轼曰:有亲刚乐,动众则忧。
朱氏震曰:此得位而众从之,故乐,师犯难而众比之,故忧,忧乐以天下也。
临观之义,或与或求。
本义 以我临物曰“与”,物来观我曰“求”,或曰:二卦耳有与求之义。
集说 郭氏雍曰:《临》与所临,《观》与所观,二卦皆有与求之义,或有与无求,或有求无与,皆非《临》、《观》之道。
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
本义 《屯》震遇坎,震动故“见”,坎险不行也,《蒙》坎遇艮,坎幽昧,艮光明也。或曰,《屯》以初言,《蒙》以二言。
集说 苏氏轼曰:“君子以经纶”,故曰“见”。“盘桓利居贞”,故曰“不失其居”。
蒙以养正,蒙正未分,故曰“杂”。童明,故曰“著”。
龚氏原曰:不见则不足以济众,不居则不足以为主。
柴氏中行曰:在蒙昧之中,虽未有识别,而善理昭著。
震,起也。艮,止也。损益,盛衰之始也。
集说 虞氏翻曰:《震》阳动行,故起。《艮》阳终止,故止。
朱氏震曰:阳起于《坤》而出《震》,则静者动,阳止于《艮》而入《坤》,则动者静。
郭氏雍曰:损已必盛,故为盛之始,益已必衰,故为衰之始,消长相循,在道常如是也。
俞氏琰曰:《损》、《益》盖未至于盛衰,而盛衰自此始也。
钱氏志立曰《损》、《益》、《否》、《泰》,为盛衰反复之介,《易》所最重者也,《杂卦》于它卦分举,而《损》、《益》、《否》、《泰》则合举之,以明盛衰之无常,反复之甚速也。《周易》自《乾》、《坤》至《否》、《泰》十二卦,自《咸》、《恒》至《损》、《益》十二卦,此除《乾》、《坤》外,自《比》、《师》至《损》、《益》十卦,自《成》、《恒》至《泰》、《否》十卦。
大畜,时也。无妄,灾也。
本义 止健者,时有适然,无妄而灾自外至。
集说 郭氏雍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然则“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亦以待时也,《无妄》之谓灾,其余自作孽而已,故《无妄》“匪正有眚”。
萃聚而升不来也,谦轻而豫怠也。
集说 郭氏雍曰:谦轻己,豫怠己也,以乐豫,故心怠,是以君子贵知几。
《朱子语类》云:“轻”是不自尊重,卑少之义,“豫”是悦之极,便放倒了,如上六“冥豫”是也。
项氏安世曰:自以为少,故“谦”。自以为多,故“豫”,小故“轻”,多故“怠”。
柴氏中行曰:谦者视己若甚轻,豫则有满盈之志而怠矣。
张氏振渊曰:《萃》有聚而尚往之义,《升》有庄而不反之义。
噬嗑,食也。贲,无色也。
本义 白受采。
集说 郭氏雍曰:《贲》以白贲无咎,故无色则质全,有天下之至贲存焉。
项氏安世曰:物消曰“食”,噬者合,则强物消矣。
案 此二语之义,即所谓“食”取其充腹,衣取其蔽体者也,若饫于膏梁,则噬之不能合,而失饮食之正,若竞于华美,则目迷五色,而非自然之文。
兑见而巽伏也。
本义 《兑》阴外见,《巽》阴内伏。
集说 何氏楷曰:《巽》本以阴在下为能巽也,《彖传》乃为“刚异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兑》本以阴在上为能说也。《彖传》乃谓“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盖终主阳也云尔。
随,无故也。蛊,则饬也。
本义 《随》前无故,《蛊》后当饬。
集说 俞氏琰曰:故,谓故旧,与革去故之故同,随人则忘旧,《蛊》则饬而新也。
案 无故,犹庄子言去故,人心有旧见,则不能随人,故尧舜舍己从人者无故也。
剥,烂也。复,反也。
集说 项氏安世曰:剥,烂尽。复,反生也。凡果烂而仁生,物烂而蛊生,木叶烂而根生,粪壤烂而苗生,皆《剥》、《复》之理也。
徐氏几曰:剥烂则阳穷于上,复反则阳生于下,犹果之烂坠于下,则可种而生矣。
晋,昼也。明夷,诛也。
本义 诛,伤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本义 刚柔相遇而刚见掩也。
集说 张子曰:泽无水,理势适然,故曰“相遇。”朱氏震曰:往来不穷,故曰“井通”,遇阴则见掩而困,唯其时也。
郭氏雍曰:“往来井井”,则其道通,田遇刚掩,所以为《困》。
项氏安世曰:自《乾》、《坤》至此三十卦,正与上经之数相当,而下经亦以《咸》、《恒》为始,以此见卦虽以杂名,而《乾》、《坤》、《咸》、《恒》上下经之首,则未尝杂也。
咸,速也。恒,久也。
本义 咸速,恒久。
集说 蔡氏渊曰:有感则应故速,常故能久。
蔡氏清曰:“咸”非训速也,天下之事,无速于感通者,故曰“咸速”。
涣,离也。节,止也。解,缓也。蹇,难也。睽,外也。家人,内也。
否泰,反其类也。
集说 虞氏翻曰:涣散故“离”,节制度数故“止”。
张子曰:天下之难既解,故安于佚乐,每失于缓。《蹇》者“见险而止”,故为“难”。
项氏安世曰;《涣》、《节》正与《井》、《困》相反,《井》以木出水,故居塞而能通,《涣》则以水浮木,故通之极而至于散也。《节》以泽上之水,故居通而能塞,《困》为泽下之水,故塞之极而至于困也。
徐氏几曰:《睽》者疏而外也,《家人》者亲而内也。
俞氏琰曰:《涣》、《节》皆有坎水,风以散之则离,泽以潴之则止。
徐氏在汉曰:外,犹言外之也,非内外之外,以情之亲疏为内外也。
大壮则止,遯则退也。
本义 止,谓不进。
集说郭氏雍曰:壮不知止,小人之壮也。君子之壮,则有止。《遯》之退,《大壮》之止,则克己之道。
赵氏玉泉曰:《大壮》以“壮趾”为“凶”,“用壮”为“厉”,欲阳之知所止也,《遯》以“嘉遯”为“吉”,“肥遯”为“利”,欲阳之知所处也。
何氏楷曰:壮不可用,宜止不宜躁,遯与时行,应退不应进,止者难进,退者,易退也。
本义 既明且动,其故多矣。
集说 朱氏震曰:《大有》六五,柔得尊位而有其众,有其众则众亦归之,故曰大有众也。《同人》六二,得中得位而同乎人,同乎人则人亦亲之,故曰“同人亲也”。
潘氏梦旂曰:物盛则多故,旅寓则少亲。
离上而坎下也。
本义 火炎上,水润下。
小畜,寡也。履,不处也。
本义 不处行进之义。
集说 龚氏原曰:柔为君,故《大有》则众,柔为臣,故《小畜》则寡。
案 寡者,一阴虽得位而畜众阳,其力寡也,不处者,一阴不得位而行乎众阳之中,不敢宁处也。
需,不进也。讼,不亲也。
集说 李氏舜臣曰:乾上离下为《同人》,火性炎上而趋乾,故曰“同人亲也”。乾上坎下为《讼》,水性就下,与乾违行,故“不亲也”。
大过,颠也。姤,遇也,柔遇刚也。渐,女归待男行也。颐,养正也。
既济,定也。归妹,女之终也。未济,男之穷也。夬,决也。刚决柔也。
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
本义 自《大过》以下,卦不反对,或疑其错简,今以韵协之,又似非误,未详何义。
集说 韩氏伯曰:刚柔失位,其道未济,故曰”穷也”。
《朱子语类》云:女待男而行,所以为渐。
又云:《杂卦》以《乾》为首,不终之以它卦,而必终之以夬者,盖《夬》以五阳决一阴,决去一阴,则《复》为纯《乾》矣。
项氏安世曰:《大过》之象,本未俱弱,而在杂卦之终,圣人作《易》,示天下以无终穷之理,教人以拨乱反正之法,是故原其乱之始生于《姤》,而极其势之上穷于《夬》,以示微之当防,盛之不足畏。自《夬》而《乾》,有终而《复》始之义也。
又曰:自《大过》以下,特皆以“男女”为言,至《夬》而明言之曰:“君子”“小人”,然则圣人之意,断可识矣。
胡氏炳文曰:本义谓自《大过》以下,或疑其错简,以韵协之,又似非误。愚窃以为“杂物撰德,非其中爻不备”,此盖指中四爻互体而言也。先天图之左,互《复》、《颐》、 易学启蒙圣人现象以画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后世之人,皆有以决嫌疑,定犹豫,而为迷于吉凶悔吝之途,其功可谓盛矣。然其为卦也,自本而干,自干而枝,其势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为蓍也,分合进退,从横逆顺,亦无往而不相值焉,是岂圣人心思智虑之所得为也哉。特气数之自然,形于法象,见于图书者,有以启于其心而假手焉尔。近世学者,类喜谈《易》而不察乎此,其专于文义者,既支离散漫,而无所根著,其涉于象数者,又皆牵合傅会,而或以为出于圣人心思智虑之所为也,若是者予窃病焉,因与同志,颇辑旧文,为书四篇,以示初学,使毋疑于其说云。
淳熙丙午暮春既望魏氏了翁曰:朱文公《易》,得于邵子为多。盖不读邵《易》,则茫不知《启蒙》、《本义》之所以作。
本图书第一《易大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孔安国云:“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列于背,有数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
集说 朱子答袁枢曰:以《河图》、《洛书》为不足信,自欧阳公以来,已有此说,然终无奈《顾命》、《系辞》、《论语》皆有是言,而诸儒所传二图之数,虽有交互而无乖戾,顺数逆推,纵横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图》与《易》之天一至 刘歆云: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锡《洛书》法而陈之,九畴是也。《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
关子明云:《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洛书》之文,九前一后,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后左,六后右。
集说 朱子书《河图》、《洛书》曰:读《大戴礼》书,又得一证甚明。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语,而郑氏注云:“法龟文也”,然则汉人固以九数者为《洛书》也。
又偶读《漫记》曰:子华子论《河图》之二与四抱九而上跻,六与八蹈一而下沈,五居其中,据三持七,巧亦甚矣,唯其甚巧,所以知其非古书也。
案 郑注《大戴礼》是确证,至子华子,则位置虽明,但错以《洛书》为《河图》,故朱子疑其非古书。
邵子曰:圆者星也,历纪之数,其肇于此乎。历法合二始以定刚柔,二中以定律历,二终以纪闰余,足所谓历纪也。方者土也,画州井地之法,其仿于此乎。州有九,井九百亩,是所谓画州井地也。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蔡元定曰:古今传记,自孔安国刘向父子、班固皆以为《河图》授羲,《洛书》锡禹。关子明、邵康节,皆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盖《大传》既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洪范》又明言“天乃锡禹洪范九畴”,而九宫之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正龟背之象也。唯刘牧臆见,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托言出于希夷,既与诸儒旧说不合,又引《大传》以为二者皆出于伏羲之世,其《易》置图书,并无明验,但谓伏羲兼取图书,则《易》、《范》之数诚相表里,为可疑耳。其实天地之理,一而已矣,虽时有古今先后之不同,而其理则不容于有二也。故伏羲但据《河图》以作《易》,则不必豫见《洛书》,而已逆与之合矣。大禹但据《洛书》以作《范》,则亦不必追考《河图》,而已暗与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战?诚以此理之外,无复它理故也。然不特此尔,律吕有五声十二律,而其相乘之数,究于六十,日名有十干十二支,而其相乘之数,亦究于六十,二者皆出于《易》之后,其起数又各不同,然与《易》之阴阳策数多少自相配合,皆为六十者无不合若符契也。下至运气参同太乙之属虽不足道,然亦无不相通,盖自然之理也。假令今世复有图书者出,其数亦必相符,可谓伏羲有取于今日而作《易》乎?《大传》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者,亦汛言圣人作《易》作《范》,其原皆出于天之意,如言“以卜筮者尚其占”,与“莫大乎蓍龟”之类,《易》之书岂有龟与卜之法子?亦言其理无二而已尔。
此一节,夫子所以发明《河图》之数也。天地之间,一气而已,分而为二,则为阴阳,而五行造化,万物始终,无不管于是焉。故《河图》之位,一与六共宗而居乎北,二与七为朋而居乎南,三与八同道而居乎东,四与九为友而居乎西,五与十相守而居乎中。盖其所以为数者,不过一阴一阳,以两其五行而已。所谓天者,阳之轻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谓地者,阴之重浊而位乎下者也,阳数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属乎天,所谓“天数五”也。阴数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属乎地,所谓“地数五”也,天数地数,各以类而相求,所谓“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其所谓“各有合”焉者也。积五奇而为二十五,积五偶而为三十,合是二者而为五十有五,此《河图》之全数,皆夫子之意,而诺儒之说也。至于《洛书》,则虽夫子之所未言,然其象其说,已具于前,有以通之,则刘歆所谓经纬,表里者可见矣。
案 中间述《大传》处,是夫子之意,天一生水之类,则是诸儒之说,盖诸儒旧说,皆以五行说图书,故朱子于《启蒙》、《本义》,因而仍之,它日又曰:《河图》、《洛书》于八卦九章不相著,未知如何也。然则朱子之意,盖疑图书之精蕴,不尽于诸儒之所云者尔。
或曰:《河图》、《洛书》之位与数其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图》以五生数统五成数而同处其方,盖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数之体也。《洛书》以五奇数统四偶数而各居其所,盖主于阳以统阴而肇其变,数之用也。
集说 赵氏汝楳曰:一对二,三对四,而五居中,六七合一二,八九合三四,而十合五,奇偶数对,阴阳有合,而数之体以立。圣人所谓“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者,此其类也。体立矣不变则数不行,故阳以三左行,阴以二右行,三其一为三,而居东,三其三为九,而居南,三其九为二十七,而七居西,三其二十七为八十一,而一复居北,等而上之,至于亿兆,其余数之位皆然。二其二为四而居东南,二其四为八而居东北,二其八为十六,而六居西北,二其十六为三十二,而二复居西南,上而亿兆亦然。八位既列,五仍居中,而数之用以通,圣人所谓“参伍以变,错综其数”者,此其类也。
鲍氏云龙曰:以《洛书》变数推之,阳以三左行,天圆径一围三。三,天数也。一在北:一而三之,三在东;三其三为九,而居南;九而三之,三九二十七而居西;三其二十七为八十一,而一复居于北。北而东,东而由,南而西,西而复北,循环不穷,有以符;天道左旋之义。地方径一围四,两其二也,盖以地上之数起于二,而阴资以为始,位在西南而右行,二而二之为四,而居东南,二而四之为八,而居东北:二其八为十六,而居西北,二其十六为三十二,而二复居西南本位。西南而东南,东南而东北,东北而 案 朱子此条,己尽图书之大义。盖以生数统成数而同处其方者,自五以前为方生之数,自五以后为既成之数。阴生则阳成,阳生则阴成,阴阳二气,相为终始,而未尝相离也。以奇数统偶数而各居其所者,四正之位,奇数居之;四维之位,偶数居之。阴统于阳,地统于天,天地同流,而定分不易也。揭其至以示人,而道其常者数至十而始全,缺一则不全矣。故曰数之体主于阳以统阴,而肇其变者,始于一,终于九,所以起因乘归除之法,故曰数之用。然生成之理则明矣,而正维之位所自定者,唯赵氏鲍氏之说,为能推明其义,诸家皆不及也。
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数之始,一阴一阳而已矣。阳之象圆,圆者径一而围三,阴之象方,方者径一而围四,围三者以一为一,故参其一阳而为三。围四者以二为一,故两其一阴而为二,是所谓“参天两地”者也。二二之合,则为五矣,此《河图》、《洛书》之数,所以皆以五为中也。
案 三二之合,五也,一四之合,亦五也,一一二二之积,又五也,三二四四之积,又五之积也,此五所以为数之会而位之中与。
然《河图》以生数为主,故其中之所以为五者,亦具五生数之象焉。其下一点,天一之象也,其卜一点,地二之象也,其左一点,天三之象也,其右一点,地四之象也,其中一点,天五之象也。《洛书》以奇数为主,故其中之所以为五者,亦具五奇数之象焉。其下一点,亦天一之象也,其左一点,亦天三之象也,其中一点,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点,则天七之象也,其上一点,则天九之象也,其数与位,皆三同而二异,盖阳不可易,而阴可易,成数虽阳,固亦生之阴也。曰:中央之五,既为五数之象矣,然其为数也,奈何?曰:以数言之通乎一图,由内及外,固各有积实可纪之数矣,然《河图》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数,以附于其生数之外。《洛书》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类以附于奇数之侧,盖中者为主,而外者为客,正者为君,而侧者为臣,亦各有条而不紊也。
集说 翁氏泳曰:《河图》东北阳方,则主之以奇,而与合者偶,西南阴方,则主之以偶,而与合者奇。
吴氏曰慎曰:阳始北而终西,一三阳尚微,故居内。七九阳盛而著于外也,必实其中而后能著乎外,故五居中。阴始南而终东,二四阴尚微,故居内。六八阴盛而凝于外也,必坚乎外而后能实其内,故十居中。自中而外,阳之生长,自外而中,阴之收藏,观于草木之枝叶果实,亦可见矣。
五,生数之终,十,成数之终,而藏于中,此“太和”之所以“保合”深固,而生机之所以充实于内也。
案 此段即与上生数统成数奇数,统偶数一段相发明。以生数统成数者,生数常居内而为主,成数常居外而为客。如一岁之寒暑往来,一月之阴魄死生,一日之昼夜进退, 曰: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图》主全,故极于十,而奇偶之位均,论其积实,然后见其偶赢而奇乏也。洛书主变,故极于九,而具位与实,皆奇赢而偶乏也。必皆虚其中也,然后阴阳之数,均于二十而无偏耳。
案 此段亦与上段数之体、数之用相发明。
曰:其序之不同何也?曰《河图》以生出之次言之,则始下次上次左次右以复于中,而又始下也。以运行之次言之,则始东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于东也。其生数之在内者,则阳居下左而阴居上右也,共成数之在外者,则阴居下左,而阳居上右也。《洛书》之次,其阳数,则首北次东次中次西次南,其阴数,则首西南次东南次西北次东北也。合而言之,则首北次西南次东次东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东北而究于南也。
其运行,则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复克水也,是亦各有说矣。曰:其七八九六之数不同何也?曰《河图》六七八九,既附于生数之外矣,此阴阳老少进退饶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数一三五之积也,故自北而东,自东而西,以成于四之外。其六者,生数二四之积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于一之外。七则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则六之自北而东者也,此又阴阳老少、互藏其宅之变也。《洛书》之纵横十五而七八九六,迭为消长,虚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则参伍错综,无适而不遇其合焉,此变化无穷之所以为妙也。曰:然则圣人之则之也,奈何?曰:则《河图》者虚其中,则《洛书》者总其实也。《河图》之虚五与十者,太极也,奇数二十偶数二十者,两仪也。以一二三四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为乾坤离坎,补四隅之空,以为兑震巽艮者,八卦也。《洛书》之实,其一为五行,其二为五事,其三为八政,其四为五纪,其五为皇极,其六为三德,其七为稽疑,其八为庶徽,其九为福极,其位与数尤晓然矣。
集说 《朱于语类》云:《洛书》本文,只四十五点。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古字画少,恐或有模样,但今无所考。汉儒此说未是,恐只是以义起之,不是数如此,盖皆以天道人事参互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事又参之,故第二;身既修,可推之于政,故八政次之;政既成,又验之于天道,故五纪次之;又继之以皇极居五,盖能推五行,正五事,用八政,修五纪,乃可以建极也,六三德,乃是权衡此皇极者也,德既修矣,稽疑庶征继之者,著其验也,又继之以福极,则善恶之效,至是不可加矣,皇极非大中也,皇乃天子,极乃极至,言皇建此极也。
吴氏曰慎曰:《河图》虚中宫以象太极,故周子曰“无极而太极”,《洛书》主中五以为皇极,故曰皇建其有极。
阴阳皆自内始生,穷外而尽,观四时之寒暑相推,万物之荣枯生死可见。《河图》 《洛书》上三数象天,中三数象人,下三数象地,人能参天地,赞化育,建中和,故归重于五皇极焉。
案 吴氏三条,于图书卦畴,深有发明。所谓无极有极云者,则《易》、《范》之第一义也,其以先天图合《河图》,语尤真切。圣人所谓则之者,为其理之符契耳,岂必规规于点画方位而求密合哉!《洛书》以四正之参数象天,四隅之两数象地,中宫之合数象人,吴氏分三重者,似亦本于《大戴礼》子华子之说,然今以《洪范》考之,盖始于一二三,中于四五六,终于七八九,而各以相天道,建主极,协民居,为之先后次第,自日用饮食修己治人之近,层累增高,至于上下同流而后已焉,皆所谓得其理而不规规于点画方位以求密合者。大抵《易》卦以八为节,其根起于两仪也,《范畴》以九为节,其根起于三才也,知《易》、《范》所起之根,则知“图书”所蕴之妙矣。
曰:《洛书》而虚其中,则亦太极也,奇偶各居二十,则亦两仪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纵横十五而互为七八九六,则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为乾坤离坎,四隅之偏,以为兑震巽艮,则亦八卦也。《河图》之一六为水,二七为火,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五十为土,则固《洪范》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畴之子目也,是则《洛书》固可以为《易》,而《河图》亦可以为《范》矣。且又安知“图”之不为书,“书”之不为“图”也邪!曰:是其时虽有先后,数虽有多寡,然其为理则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图”,而初无所待于“书”,《范》则大禹之所独得乎“书”,而未必追考于“图”耳。且以《河图》而虚十,则《洛书》四十有五之数也,虚五则大衍五十之数也,积五与十,则《洛书》纵横十五之数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则又皆大衍之数也。
《洛书》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而通为大衍之数矣,积五与十,则得十五,而通为《河图》之数矣,苟明乎此,则横斜曲直,无所不通,而《河图》、《洛书》,又岂有先后彼此之间哉!
原卦画第二朱子答袁枢曰: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而天地万物之理,阴阳始终之变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为作《传》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传》,则其所论,固当专以文王之《易》为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画卦之所由,则学者只从中半说起,不识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极两仪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泽雷风水火之类,皆本伏羲画卦之意。今新书原卦画一篇,亦分两义,伏羲在前,文王在后。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大传》又言包羲画卦所取如此,则《易》非独以《河图》而作也,盖盈天地之间,莫非太极阴阳之妙,圣人于此,仰观俯察,远求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默契于其心矣。故自两仪之末分也,浑然太极,而两仪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粲然于其中。自太极而分两仪,则太极固太极也,两仪固两仪也,自两仪而分四象,则两仪又为太极,而四象又为两仪矣,自是而推之,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于百千万亿之无穷。虽其见于摹画者,若有先后而出于人为,然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势,则固已具于浑然之中,而不容毫发思虑作为于其间也。程子所谓加一倍法者,可谓一言以蔽之,而邵子所谓画前有《易》者,又可见其真不妄矣,世儒于此,或不之察,往往以为圣人作《易》,盖极其心思探索之巧而得之,甚者至谓凡卦之画,必由蓍而后得,其误益以甚矣。
集说 谢氏良佐曰:尧夫《易》数甚精,明道闻说甚熟,一日因监试无事,以其说推算之皆合,出谓尧夫曰:尧夫之数,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济事。
朱子答虞大中曰:太极两仪四象八卦,此乃《易》学纲领,开卷第一义,孔子发明伏羲画卦自然之形体,孔子而后;千载不传,唯康节明道二先生知之,盖康节始传先天之学而得其说,且以此为伏羲之《易》也。《说卦》天地定位一章,“先天图”乾一至坤八之序皆本于此,然康节犹不肯大段说破《易》之心髓全在此处。不敢容易轻说,其意非偶然也。明道以为加一倍法,其发明孔子之言,又可谓最切要矣。
《易》有太极太极者,象数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称,形器已具,而其理无联之目,在《河图》、《洛书》,皆虚中之象也。周子曰:“无极而太极。”邵子曰:“道为太极。”又曰:“心为太极。”此之谓也。
案 太极之在《易》书者虽无形,然乾即太极也,偏言之,则可以与坤对,亦可以与“六子”并列,专言之,则地一天也,“六子”亦一天也。故程子曰:夫天,专言之则道也,以形体言谓之天,以主宰言谓之帝,以妙用言谓之神,以性情言谓之乾,其言可谓至矣。虽然画卦之初亦未有乾之名,其始于一画者即是也,摹作圆形者,始自周子,朱子盖借之以发《易》理之宗,学者不可误谓伏羲画卦,真有是象也。
太极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为一画者二,是为两仪,其数则阳一而阴二,在《河图》、《洛书》则奇偶是也。周子所谓“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邵子所谓“一分为二”者,皆谓此也。
集说 朱子答袁枢曰:如所论两仪,有曰乾之画奇,坤之画偶,只此乾坤字便未稳当,盖仪,匹也,如俗语所谓一双一对云耳,自此再变至第三画,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当其为一画之时,方有一奇一偶,只可谓之阴阳,未得谓之乾坤也。
两仪生四象“两仪”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二画者四,是谓“四象”,其位则太阳一;少阴二;少阳三;太阴四。其数则太阳九;少阴八;少阳七;太阴六。以《河图》言之,则六者一而得于五者也,七者二而得于五者也,八者三而得于五者也,九者四而得于五者也。以《洛书》言之,则九者十分一之余也,八者十分二之余也,七者十分三之余也,六者十分四之余也。周子所谓“水火木金”,邵子所谓“二分为四”者,皆谓此也。
集说 朱子答程迥曰:所谓“两仪”为乾坤初爻,“四象”为乾坤初二,相错而成,则恐立言有未莹者,盖方其为“两仪”,则未有“四象”也,方其为“四象”,则未有八卦也,安得先有乾坤之名,初二之辨哉?“两仪”只可谓之阴阳,“四象”方有太少之别,其序以太阳少阴少阳太阴为次,此序既定,递升而倍之,适得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也。
又答袁枢曰:“四象”之名,所包甚广,大抵须以两画相重四位成列者为正,而一二三四者其位之次也,七八九六者,其数之实也。其以阴阳刚柔分之者,合天地而言也,其以阴阳太少分之者,专以天道而言也,若专以地道言之,则刚柔又自有太少矣,推而广之,纵横错综,凡是一物,无不各有四者之象,不但此数者而已矣。
《语类》云:《易》中七八九六之数,向来只从揲蓍处推起,虽亦吻合,然终觉曲折太多,疑非所以得数之原。因看“四象”次第,偶得其说,极为捷径,盖因一二三四, 四象生八卦“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三画者八,于是三才略具,而有八卦之名矣,其位则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在《河图》,则乾坤离坎分居四实,兑震巽艮分居四虚。在《洛书》,则乾坤离坎分居四方,兑震巽艮分居四隅。《周礼》所谓三《易》“经卦皆八”,《大传》所谓“八卦成列”,邵子所谓“四分为八”者,皆指此而言也。
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四画者十六,于经无见,邵子所谓“八分为十六者”是也,又为‘两仪”之上,各加八卦,又为八卦之上,各加“两仪”也。
案 四画十六者,为八卦之上,各加“两仪”,又为“四象”之上,各加四象也。
于经虽无见,然及六十四卦既成之后,以其自二至五,四爻互之,或自初至四,或自三至上,或自四而又至初,或自五而又至二,或自上而又至三,错综颠倒互之,皆得《乾》、《坤》、《既济》、《末济》、《剥》、《复》、《垢》、《夬》。《渐》,《归妹》、《大过》、《颐》、《解》、《蹇》、《睽》、《家人》诸卦适合十六之数,孔子于杂卦发其端矣。汉儒互卦之说,盖本诸此也。邵子诗云: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即以此四画者,为四象相交者尔,学者误以上文天地否泰十六卦当之,失其指矣。
四画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五画者三十二,邵子所谓“十六分为三十二者”是也,又为“四象”之上,各加八卦,又为八卦之上,各加四象也。
案 五画三十二者,自初至三,可互一卦,自三至五,又可互一卦,六十四卦既成之后,依此法错综,颠倒互之,则得《复》、《垢》、《颐》、《大过》、《屯》、《鼎》、《恒》、《益》、《丰》、《涣》、《坎》、《离》、《蒙》、《革》、《同人》、《师》、引临》,《遯》、《成》、《损》、《节》、《旅》、《中孚》、《小过》、《大壮》、《观》、(大有》、《比》、《夹》、《剥》、(乾》、《坤》诸卦亦适合三十二之数,先儒亦有以是说互卦者,如《损》、《益》皆互《颐》,《颐》象离为龟,故《损》、《益》二五言“十朋之龟”之类。
五画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六画者六十四,则“兼三才而两之”,而八卦之乘八卦亦周,于是六十四卦之名立而《易》道大成矣。《周礼》所谓三《易》之别,皆六十有四,《大传》所谓“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邵子所谓“三十二分为六十四者”是也。若于其上各卦,又各生一奇一偶,则为七画者百二十八矣;七画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则为八画者二百五十六矣;八画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则为九画者五百十二矣;九画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则为十画者干二十四矣;十画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则为十一画者二干四十八矣;十一画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则为十二画者四千九十六矣。
此焦赣《易林》变卦之数,盖亦六十四乘六十四也,今不复为图于此,而略见第四篇中。
若自十二画上,又各生一奇一偶,累至二十四画,则成千六百七十七万七千二百一十六变,以四千九十六自相乘,其数亦与此合,引而伸之,盖未知其所终极也,虽未见其用处,然亦足以见《易》道之无穷矣。
案 《易林》之数,盖古占筮之法,《洪范》占法,“曰贞曰悔”,夫以八卦变为六十四言之,则八卦贞也,重卦悔也,《春秋传》“贞风悔山”是也。以六十四卦变为四千九十六言之,则六十四卦贞也,变卦悔也,《春秋传》“贞屯悔豫”是也,因卦画之生生无尽,故占筮之变化无穷,焦赣能知其法,而至各缀之以辞则凿矣,邵朱二子,所为传心之要者在此。
集说 朱子答林栗曰: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生出次第,位置行列,不待安排,而粲然有序,以至于第四分而为十六,第五分而为三十二,第六分而为六十四,则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推捧,而与前之三分焉者,未尝不吻合也。比之并累三阳以为乾,连叠三阴以为坤,然后以意交错而成“六子”,又先画八卦于内,复画八卦于外+以旋相加而 又答袁枢曰:若要见得圣人作《易》根原直截分明,不如且看卷首横图,自始初只有两画时,渐次看起,以至生满六画之后,其先后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费辞说,于此看得,方见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挨排出来,圣人只是见得分明,便只依本画出,元不曾用一豪智力添助。盖本不繁智力之助,亦不容智力得以助于其间也。及至卦成之后,逆顾纵横,都成义理,千般万种,其妙无穷,却在人看得如何,而各因所见为说,虽若各不相资,而实未尝相悖也。盖自初未有画时,说到六画满处者,邵子所谓“后天之学”也,卦成之后,各因一义推说,邵子所谓“先天之学”也。先天后天既各自为一义,而后天说中,取义又多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执一而废百也。
《浯类》问自一阴一阳,见一阴一阳又各生一阴一阳之象,以图言之,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节节推去,固容《易》见,就天地间著实处,如何骏得?曰:一物上又自各有阴阳,如人之男女阴阳也,逐人身上,又各有这血气,血阴而气阳也,如昼夜之间,昼阳而夜阴也,而昼阳自午后又属阴,夜阴自子后又属阳,便是阴阳各生阴阳之象。
又云:先天图直是精微,不起子康节,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秘而不传,次第是方士辈所相传授,《参同契》中,亦有些意思相似,扬雄《太玄》,全模仿《易》,他底用三数,《易》却用四数,他本是模《易》,故就他模底句上看《易》,也可略见得《易》意思。
又云:自有《易》以来,只有邵子说得此图如此齐整,如扬雄(太玄》,便零星补凑得可笑。若不补,又却欠四分之一,补得来,又却多四分之三,如《潜虚》之数用五,只似如今算位一般,其直一画则五也,下横一画则为六,模二画则为七,盖亦补凑之书也。
黄氏瑞节曰:先天图与太极图同时而出,周邵二子不相闻,则二图亦不相通,此勿论也。陈莹中云:司马文正与康节同时友善,而未尝有一言及先天之学,邵伯温云,伊川在康节时,于先天之学非不问,不语之也。即二先生之论,则先天图在当时,岂犹未甚著邪,陈莹中云,先天之学,以心为本,其在《经世书》者,康节之余事耳。又曰:阐先圣之幽,微先天之显,不在康节之书乎,然则朱子以前表章尊敬此图者,了翁为有见也。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邵子曰:此一节,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错者,明交相错而成六十四也,“数往者顺,若顺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数往”也。“知来者谨”,若逆天而 自震之初为冬至,离兑之中为春分,以至于乾之末而交夏至焉,皆进而得其已生之卦,犹自今日而追数昨日也,故曰“数往者顺”。其右方,自巽之初为夏至,坎艮之中为秋分,以至于坤之末而交冬至焉,皆进而得其未生之卦,犹自今日面逆计来日也,故曰“知来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则其先后始终,如横图及圆图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数也。
”集说 《朱子语类》云:若自乾一横排至坤八,此则全是自然,故《说卦》云: “《易》逆数也。”皆自己生以得末生之卦,若如圆图,则须如此,方见阴阳消长次第,震一阳,离兑二阳,乾三阳,巽一阴,坎艮二阴,坤三阴,虽似稍涉安排,然亦莫非自然之理。
附录 项氏安世曰:“数往者顺”,以指上文,“知来者逆”,以指下文,“是故《易》逆数也”,此一句以起下文八句也。上文据八卦已成之后,对面数之,其序顺而理明,故曰“数往者顺”。下文据八卦始画之初,左右对画,而上下逆生,故曰“知来者逆”。
非圣人于顺之外别为逆象也,此之逆象,即上文之顺象。
章氏潢曰:自乾纯阳,历兑离以至一阳之震,自坤纯阴,历艮坎以至一阴之巽,非数往之顺乎?自震一阳,历离兑以至乾之纯阳,自巽一阴,历坎艮以至坤之纯阴,非知来之逆乎?左旋则总为“知来”,有旋则总为“数往”,但《易》以“知来”为主,生生不穷,是以逆而数之。
案 邵子所谓左旋者,犹言向左而旋耳。所谓右行者,犹言向右而行耳,与历家所谓左旋右转,义正相反,各为一说也。其所谓“已生一未生”,正指阴阳生生而言,如章氏之说,而项氏说尤得前后联贯语气。盖其顺数者,既如上文所列矣,而图之作,主于逆数,故其终始生成,又如下文之所叙也。朱子之解似又自为一说,学者分别观之。
又曰:太极既分,两仪立矣,阳上交于阴,阴下交于阳,而四象生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八卦相错,而后万物生焉,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犹根之有干,干之有枝,愈大则愈小,愈细则愈繁。
集说 《朱子语类》:问:程《易》乾辞下解云,圣人始画八卦,三才之道备矣,因而重之,以尽天下之变,故六画而成卦。或疑此说却是圣人始画八卦,每卦便是三画,圣人因而重之为六画,似与邵子一分为二,而至六十四为六画,其说不同。曰:程子之意,只云三画上叠成六画,八卦上叠成六十四耳,与耶子说诚异,盖康节此意,不曾说与程子,程于亦不曾问之,故一向只随他所见去。但程子说圣人始画八卦,不知圣人画八卦时,先画甚卦,此处便晓不得。
是故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长之,巽以消之。长则分,分则消,消则翕也,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兑离坎艮再交也,故震阳少而阴尚多也,巽阴少而阳尚多也,兑离阳浸多也,坎艮阴浸多也。
又曰:无极之前,阴含阳也,有象之后,阳分阴也。阴为阳之母,阳为阴之父,故母孕长男而为《复》,父生长女而为《姤》,是以阳起于《复》,阴起于《垢》也。
案 周子所谓“无极而太极”者,以阴阳之奉体言之,《中庸》所谓“天命之性”也。邵子所谓“无极”者,以动静之枢纽言之,<中庸》所谓“未发之中”也。天命之性,固周流而无不在,然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则冲漠无暇之时,乃本体之真之所以具,故周子亦言主静,程子言其本也,真而静,三子之说,实相发明而不相悖也。
又曰:震始交阴而阳生,巽始消阳而阴生。兑,阳长也,艮,阴长也,震兑,在天之阴也,巽艮,在地之阳也,故震兑上阴而下阳,巽艮上阳而下阴。天以始生言之,故阴上而阳下,交泰之义也。地以既成言之,故阳上而阴下,尊卑之位也。乾坤定上下之位,坎离列左右之门,天地之所阖辟,日月之所出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昼夜长短,行度盈缩,莫不由乎此矣。震始交阴而阳生,是说圆图震与坤挂而一阳生也,巽始消阳而阴生,是说圆图巽与乾接而二阴生也。
集说 邵子曰:阳爻,昼数也;阴爻,夜数也。天地相衔,阴阳相交,故昼夜相离,刚柔相错。春夏,阳也,故昼数多,夜数少。秋冬,阴也,故昼数少,夜数多。
胡氏方平曰:此一节先论震巽艮兑四维之卦,而后及于乾坤坎离四正之位。震始交阴而阳生,以震接坤言也,至兑二阳,则为阳之长。巽始消阳而阴生,以巽接乾言也,至艮二阴则为阴之长。震兑在天之阴者,邵子以震为天之少阴,兑为天之太阴,唯其为阴,故阴爻皆在上,而阳爻皆在下。天以生物为主,始生之初,非交泰不能,故阴上阳下,而取交泰之义。巽艮在地之阳者,邵子以巽为地之少刚,艮为地之太刚,唯其为刚,故阳爻皆在上,而阴爻皆在下。地以成物为主,既成之后,则尊卑定,故阴下阳上,而取尊卑之位。乾坤定上下之位,天地之所阖辟也,坎离列左右之门,日月之所出入也。
岁而春夏秋冬,月而晦朔弦望,日而昼夜行度,莫不胥此焉出,岂拘拘爻画阴阳之间哉。
又曰:乾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为阴所克也,坤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为所克之阳也,故乾得三十六,而坤得十二也。兑离以下更思之。
今按,兑离二十八阳二十阴,震二十阳二十八阴,艮坎二十八阴二十阳,巽二十阴二十八。
又曰:乾坤纵而六子横,《易》之本也。
又曰:阳在阴中,阳逆行,阴在阳中,阴逆行,阳在阳中,阴在阴中,则皆顺行,此真至之理,按图可见之矣。
又曰:《复》至《乾》凡百一十有二阳,《垢》至《坤》凡八十阳,《垢》至《坤》凡百一十有二阴,《复》至《乾》凡八十阴。
又曰:坎离者,阴阳之限也,故离当寅,坎当申,而数常逾之者,阴阳之溢也。然用数不过乎中也。此更宜思。离当卯,坎当酉,但以坤为子半可见矣。
又曰:先天学,心法也,故图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生于心也。
又曰:图虽无文,吾终日言而未尝离乎是,盖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矣。
案自孔子既没,易道失传,义理既巳差讹,图象尤极茫渺,唯《大传》“帝出乎震”一条,所载八卦方位,显然明白,故学者有述焉。其余如“卦气”“月候”之属,皆汉儒傅会,非圣人本法也,至宋康节邵子,乃有所谓“先天图”者,其说有六十四卦生出之序,则今之横图,自一画至六画,一每分二者是已,有八卦方位,则今之小囤图,乾南坤北离东坎西者是已,有六十四卦方位,则今之大圆图,始《复》、《姤》、终《乾》、《坤》者是巳,大圆图中自方图,又所以象天地之相函也。诸图之义,广大高深,信非圣人不能造作,然当邵子之时,伊川程子则未之见,龟山杨氏见而未之信,唯明道程子,稍见其书,而括以加倍之一言,然则当时知邵子者,明道一人而已。南渡之后,如林栗袁枢之徒,攻邵者尤众,虽象山陆氏,亦以为先天图非圣人作《易》本指。独朱子与蔡氏,阐发表章,而邵学始显明于世,五百年来虽复有为异论者,而不能夺也。顾朱子之意,以为孔于之后诸儒不能传授,而使方外得之,故其流为丹灶小术,至康节然后返之于易道。今以《参同契》诸书观之,其六卦月候,盖即“纳甲”之法,其十二辟卦主岁,盖即“卦气”之流,所为始于震复者,与先天偶同尔,似未足为先天传受之据。唯扬雄作《太玄》,其法始于三方,重于九洲,又重于二十七部,又重于八十一家,则与先天极仪象卦加倍之法相似也。流行之序,始于中羡从,中于更晬廓,终于减沈成,则与先天始《复》终《乾》,始《姤》终《坤》之序相似也。首用九九,策闲六六,则与先天卦用八八,策用七七之数相似也。意者康节读扬雄之书而心悟作《易》之本与,然非扬雄之时,《易》传未泯,则雄亦无自而依仿之,故康节深服《太玄》,以为见天地之心,盖其学所启发得力处也。然白邵书既出,则《太玄》为僭经,为汨阴阳之叙,与邵书迥乎如苍素之不相侔矣。观明道程子之意,盖以为康节能自得师,故于希夷之传,扬雄之书,皆有取焉,而其纯一不杂,汪洋浩大,则非扬陈之所能及也,故曰尧夫之数,似玄而不同。又曰:穆李皆得之希夷者,而其言与行事,概可见矣,尧夫特因其门户而入者尔,程子之言至当,后之学者,欲考先天之传,不可以不知。
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
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挠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熯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
邵子曰:此一节明文王八卦也。
又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为《泰》,坎离交而为《既济》也。乾生于子,坤生于午,坎终于寅,离终于申,以应天之时也。置乾于西北,退坤于西南,长子用事,而长女代母,坎离得位,而兑艮为偶,以应地之方也。王者之法,文王也其尽于是矣。此言文王改《易》伏羲卦图之意也。盖自乾南坤北而交,则乾北坤南面为《泰》矣。自离东坎西而交,则离西坎东而为《既济》矣。乾坤之交者,自其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也。故再变则乾退乎西北,坤退乎西南也。坎离之变者,东自上而西,西自下而东也。
故乾坤既退,则离得乾位,而坎得坤位也。震用事者,发生于东方,巽代母者,长养于东南也。
案 邵子言乾坤交而为“泰”者,释“先天”变为“后天”之指也。先天之位,乾南坤北,今变为乾北坤南,故曰“交”。然邵子盲乾生于子,坤生于午,今按图考之,则乾在西方,乃亥而非子,坤在西南,乃未而非午,其故何也?曰:阳自静以之动,故气肇于子。然自亥月而已联兆胚胎,故古人以亥为阳月,言天道于是始也。阴自动以之静,故功著于午。然至未而后育养蕃庶,故古人以未为中央,言土德于是,王也。亥字从草为蓑,从木为核,皆联兆胚胎之意。未从日为昧,言日于是始向昧谷,而万物将西成也。乐律黄钟子为天统,然自应钟亥而阳气已应于内,故曰应钟。林钟未为地统,故班固引“西南得朋”释之,下至纳甲星命浅术,亦以亥为天门,未为坤始,疑皆本于后天以为说也。若乃火虽始于东而盛于南,水虽始于西而盛子北,雷霆之气,虽动于寅, 又曰:《易》者,一阴一阳之谓也。震兑始交者也,故当朝夕之位,坎离交之极者也,故当子午之位,巽艮不交而阴阳犹杂也,故当用中之偏,乾坤纯阳纯阴也,故当不用之位也。
又曰:兑离巽,得阳之多者也,艮坎震,得阴之多者也,是以为天地用也。乾极阳,坤极阴,是以不用也,、又曰:震兑横而六卦纵,《易》之用也。尝考此图而史为之说曰:震东兑西者,阳主进,故以长为先而位子左,阴主退,故以少为贵而位乎右也。坎北者,进之中也,离卤者,退之中也,男北而女南者,互藏其宅也。四者皆当四方之止位,而为用事之卦,然震兑妨而坎离终,震兑轻而坎离重也。乾西北坤西南者,父母既老而迟居不用之地也,然母亲顺父尊,故砷犹半用页乾全下用也。艮东北巽东南者,少男进之后而长女退之先,故亦皆不用也,然男未就傅,女将在行,故巽稍向用,而艮全未用也。四者皆居四隅不正之位,然居东者耒用而居西者不复用也。故下文历举“六子”而不数乾坤,至其水火雷风山泽之相偶,则又用伏羲卦云。
集说 邵子曰:乾统三男于东北,坤统三女于西南。
案 邵子之言,可蔽图之全义,《周易》、《坤》,《蹇》、《解》诸卦彖辞,皆出于此也,大抵先天则以东南为阳方,西北为阴方,故自阳仪而生之卦,皆居东南,自阴仪而生之卦,皆居西北也。后天则以北东为阳方,南西为阴方,故凡届阳之卦,皆居东北,属阴之卦,皆居西南也。然先天阳卦虽起于东,而其重之以叙卦气,则所谓“复见天地心”者。仍以北方为始,后天阳卦虽起于北,而其播之以合岁序,则所谓“帝出乎震”者,仍以东方为先。盖两义原不可以偏废,必也参而互之,则造化之妙,《易》理之精,可得而识矣。岁始于东,终于北,而西南在其间,后天图意主乎阳以统阴,故自震而坎而艮者,以阳终始岁功也,自巽而离而兑者,以阴佐阳于中也。震阳生,故直春生之令,以始为始也,乾则以终为始,而莫得其端,乃《传》所谓“大始”者也,所谓“不可为首者”也,兑阴成,故毕西成之事,阴功之终也,坤则致役以终事,而不居其成,乃《传》所谓“作成”者也。所谓“无成而代有终”者也,是故阳居终始,而阴在中间,乃天地万物之至理。如草木之种实,阳也;华叶,阴也。人类之父子,阳也;妻妾,阴也。始于植种,终于成实,而其间华叶盛焉,始于有父,终于有子,而其间嫡媵繁焉,实生于华,子生于母,此阴佐阳之验,然而实成、则为来岁之种矣,子生则为它日之父矣,此又所谓以终为始者,而元阳之生生不已,其首尾端倪,真不可得而窥矣。谢氏良佐论一起于震,发生也。又曰:一起于乾,探本也,其有得于后天之精意者与。
程子曰:凡阳在下者动之象,在中者陷之象,在上止之象,阴在下者入之象,在中者丽之象,在上说之象。
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
此远取诸物之象。
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此近取者身之象。
集说 《朱子语类》云:伏羲画八卦,只此数画该尽天下万物之理,学者于言上会得者浅,于象一亡会得者深,王辅嗣伊川皆不信象,伊川说象只似譬喻样说,郭子和云,不独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谓之象,只是卦画便是象,亦说得好。郑东卿专取象,如以鼎为鼎,革为炉,小过为飞鸟,亦有义理,但尽欲如此牵合傅会便疏脱,学者须先理会得正当道理,然后于此等另碎处收拾以相资益,不为无补。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今按坤求于乾,得其初九而为震,故曰“一索而得男”,乾求于坤,得其初六而为巽,故曰“一索而得女”。坤再求而得乾之九二以为坎,故曰“再索而得男”。乾再求而得坤之六二以为离,故曰“再索而得女”。坤三求而得乾之九三以为艮,故曰“三索而得男”。乾三求而得坤之六三以为兑,故口“三索而得女”。
凡此数节,皆文王观于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以为说,邵子所谓后天之学,人用之位者也。
案 邵子既以“天地定位”一章为先天之《易》,因以“帝出乎震”以下为后天之《易》,先羲后文,其序既可信,而先天图易简浑涵,得画卦自然之妙,后天图精深切至,于《周易》义例合者为多,其理尤可信也:,然后天所以改置先天之意,朱子之说颇略,其见于答袁枢书者,可以得先贤慎重之盛心矣。诸家以五行为说者,亦有条理,然今即八卦之象求之,则唯坎水离火巽木坤土,合于本象耳。金者乾之一象,而不足以尽乾也。苍筤竹者震之一象,而不足以尽震也。艮山之为土,犹可假借,兑则绝无为金之义也,况《易》之为书,不言五行,而《说卦》解释图体,亦与五行生克,邈不相涉,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二十启蒙下明蓍策第三大衍之数五十。
《河图》、《洛书》之中数皆五,衍之而各极其数以至于十,则合为“五十”矣。《河图》积数五十五,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后得,独五为“五十”所因,而自无所因,故虚之则但为“五十”。又五十五之中,其四十者,分为阴阳老少之数,而其五与十者无所为,则又以五乘十,以十乘五,而亦皆为“五十”矣。《洛书》积数四十五,而其四十者,散布于外,而分阴阳老少之数,唯五居中而无所为,则亦自含五数,而并为“五十”矣。
案 《洪范》曰:“卜五占用二衍忒。”衍者,推衍也。忒者,过差也。卜筮所以推衍人事之过差,故揲蓍之法,谓之“大衍”。大音太,如太卜太筮之比,乃尊之之称,非如先儒小衍大衍之说也。五十之数,说者不一,唯推本于图书者得之,《河图》之数则赢五,数之体也。《洛书》之数则虚五,数之用也。大衍者,其酌河洛之数之中,而兼体用之理之备者与。
大衍之数五十,而菁一根百茎,可当大衍之数者二,故揲菁之法,取五十茎为一握,置其一不用,以象太极,而其当用之策,凡四十有九,盖两仪体具而未分之象也。
集说 崔氏憬曰:“其用四十有九”者,法长阳七七之数也,六十四卦,既法长阴八八之数,故四十九蓍,则法长阳七七之数,蓍圆而神象天,卦方而智象地,阴阳之别也,舍一不用者,以象太极虚而不用也。
邵子曰:蓍之用数,“挂一以象三”,其余四十八,则一卦之策也。四其十二为四十八也,十二去三而用九,四三十二,所去之策也,四九三十六,所用之策也;十二去五而用七,四五二十,所去之策也,四七二十八,所用之策也;十二去六而用六,四六二十四,所去之策也,四六二十四,所用之策也;十二去四而用八,四四十六,所去之策也,四八三十二,所用之策也。是故七九为阳,六八为阴,九者阳之极数,六者阴之极数,数极则反,故为卦之变也。
又曰:奇数极于四而五不用,策数板于九而十不用,故去五十而用四十九也。
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
挂者,悬于小指之间。揲者,以大指食指间而别之。奇,谓余数,扐者,抽于中三指之两间也,蓍凡四十有九,信手中分,各置一手,“以象两仪”;而挂右手一策于左手小指之间,以象三才,遂以四揲左手之策,“以象四时”;而归其:余数于左手第四指间,“以象闰”;又以四揲右手之策,而再归其余数于左手第三指间,“以象再闰”;五岁之象,挂一一也,揲左二也,扐左三也,揲右四也,扐右五也,是谓一变。其挂扐之数,不五即九。
案 《河图》之中宫,太极也。《洛书》之中宫,人极也。故大衍之数,其虚一者,既以象太极之无为,其挂一者,又以象人极之参赞,虚一之后,继以分二者,明乎分阴分阳,造化之本也。挂一之后,继以揲四归奇者,明平定时成岁,人事之纲也。分二挂一,则天地设位,而人立焉,而二才之体具欠。揲四归奇,则四气交运,五行参差,百物生焉,万事起焉,而三才之用行矣,大衍之数,所以为酌河洛之中,而兼体用之备者如此。
得五者三,所谓奇也。五除挂一即四,以四约之为一,故为奇,即两仪之阳数也。
一变之后,除前余数,复合其见存之策,或四十,或四十四,分挂揲归如前法,足凋再变,其挂仂者不四则八。
得四者二,所谓奇也。不去挂一,余同前义。
得八者二,所谓偶也。不去挂一,余同前义。
再变之后,除前两次余数,复合其见存之策,或四十,或三十六,或三十二,分挂揲归如前法,是谓三变,其挂扐者如再变例。
三变既毕,乃合三变,视其挂肋之奇偶,以分所遇阴阳之老少,是凋一爻。
右(即左图)三奇为老阳者凡十有二,挂扐之数十有三,除初挂之一为十有二,以四约而三分之,为一者三,一奇象圆而围三,故三一之中各复有三。而积三三之数则为九,过揲之数三十有六,以四约之,亦得九焉。挂扐除一,四分四十有八而得其一也,一其十二而三其四也,九之母也。过揲之数四分四十八而得其三也,三其十二而九其四也,九之子也。皆径一而围三也,即四象太阳居一含九之数也。
右(即下左图)两奇一偶,以偶为主,为少阴者凡二十有八,挂扐之数十有七,除初挂之一为十有六,以四约而三分之,为一者二,为二者一,一奇象圆而用其全,故二一之中各复有三。二偶象方而用其半,故一二之中复有二焉。而积二三一二之数则为八,过揲之数三十有二,以四约之亦得八焉,挂扐除一,四其四也,自一其十二者而进四也,八之母也,过揲之数,八其四也,自三其十二者而退四也,八之子也,即四象少阴居二含八之数也。
右(即前右图)两偶一奇,以奇为主,为少阳者凡二十,挂扐之数二十有一,除初挂之一为二十,以四约而三分之,为二者二,为一者一,二偶象方而用其半,故二二之中各复有二。一奇象圆而用其全,故一三之中,复有三焉。而积二二一三之数则为七,过揲之数二十有八,以四约之亦得七焉。挂抽除一,五其四也,自两其十二者而退四也,七之母也,过揲之数,七其四也,自两其十二者而进四也,七之子也,即四象少阳居三含七之数也。
右(即左图)三偶为老阴者四,挂扐之数二个有五,除初挂之一为二十有四,以四约而三分之,为二者三,二偶象方而用其半,故三二之中各复有二,面积三二之数则为六,过揲之数亦二十有四,有四约之亦得六焉,挂扐除一,六之母也,过揲之数,六之子也,四分四十有八而各得其二也,两其十二而六其四也,皆围四而用半也,即四象太阴居四含六之数也。
集说 蔡氏元定曰:蓍之奇数,老阳十二,老阴四,少阳二十,少阴二十八,合六十有四。三十二为阳,老阳十二,少阳二十;三十二为阴,老阴四,少阴二:十八;其十六则老阳老阴也,老阳十二,老阴四;其四十八则少阳少阴也,少阳二十,少阴二十八。老阳老阴,乾坤之象也,二八也,少阳少阴,“六子”之象也,六八也。
凡此四者,皆以三变皆挂之法得之,盖经曰“再抽而后挂”,又曰“四营而成易”,其指甚明,注疏虽不详说,然刘禹锅所记僧一行、毕中和、顾彖之说,亦已备矣。近世诸儒,乃有前一变独挂,后二变不挂之说,考之于经,乃为六仂而后挂,不应“五岁再闰”之义,且后两变又止三营,盖已误矣。
且用旧法,则三变之中,又以前一变为奇,后二变为偶,奇故其余五九,偶故其余四八。余五九者,五三而九一,亦围三经一之义也。余四八者,四八皆二,亦围四用半之义也。三变之后,老者阳饶而阴乏,少者阳少而阴多,亦皆有自然之法象焉。蔡元定 集说 苏氏轼曰:唐一行之学,以为三变皆少,则乾之象也,乾所以为老阳,而四数其揲得九,故以九名之;三变皆多,则坤之象也,坤所以为老阴,而四数其揲得六,故以六名之;三变面少者一,则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为少阳,而四数其揲得七,故以七名之;三变而多者一,则巽离兑之象也,巽离兑所以为少阴,而四数其揲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揲数以名阴阳,而阴阳之所以为老少者,不在乎是,而在乎三变之间,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学也。
《朱子文集》曰:初一变得五者三,得九者一,故曰余五九者,五三而九一。后二变得四者二,得八者二,故曰余四八者,四八皆二。三变之后,为老阳者十有二,老阴四,故臼阳饶而阴乏,少阳二十,少阴二十八,故曰阳少而阴多。沈氏《笔谈》云,《易》象九为老阳,七为少阳,八为少阴,六为老阴,其九七八六之数,皆有所从来,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归余之数,有多有少,多为阴,如爻之偶,少为阳,如爻之奇。
三少,乾也,故曰老阳,,九揲而得之,故其数九,其策三十六;两多一少,则一少为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谓之少阳,少在初为震,中为坎,末为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数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阴,六揲而得之,故其数六,其策二十有四;两少一多,则一多为之主,巽离兑也,故皆谓之少阴,多在初谓之巽,中为离,未为兑,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数八,其策三十有二。诸家揲蓍说,唯《笔谈》简而尽。孔颖达非不晓揲法者,但为之不熟,故其言之易差,然其子大数亦不差也。毕中和视疏义为详,柳子厚诋刘梦得以为肤末于学者,误矣!毕论三揲皆挂一,正合“四营”之义,唯以三揲之挂仂分措于三指间为小误,然于其大数亦不差也。其言余一益三之属,乃梦得立文太简之误,使读者疑其不出于自然,而出于人意耳。此与孔氏之说,不可不正,然恐亦不可不原其情也。蔡氏所谓以四十九蓍虚一分二挂一揲四者,盖谓虚一外,止用四十八。
分挂揲之余,为奇偶各二,老阳老阴变数各八,少阴少阳变数各二十四,合为六十四,八卦各得八焉,然此乃奇偶对待加倍而得者,体数也,着天三地二衍而为五十者,用数也,盖体数常均,用数则阳饶面阴乏也,此正造化之妙,若阴阳同科,老少一例,是体数,非用数也。
若用近世之法,则三变之余,皆为围三径一之义,而无复奇偶之分。三变之后,为老阳少阴者皆二十七,为少阳者九,为老阴者一,又皆参差不齐,而无复自然之法象,此足以见其说之误矣。至于阴阳老少之所以然者,则请复得而通论之。盖四十九策,除 集说 归氏有光曰:九具于揲,则三奇见于余;六具于揲,则三偶见于余;七具于揲,则二偶一奇见于余;八具于揲,则二奇一偶见于余。不必反观其在揲之数,而已举其要矣!其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何也?挂扐虽举其要,而七八九六之数,仍以在揲之策为正,七八九六者,自揲之以四而取也,若挂仂之策,因过揲而见者也。故曰“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又曰“当期之日”,而归奇以象闰。
何氏楷曰:案翼言“揲四以象四时,归奇以象闰”。四时,正也,闰余也。下文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皆以七八九六起数,明乎用正数而不用余数矣。
案 归氏何氏之说,亦可与朱子相参酌。
邵子曰:五与四四,去挂一之数,则四三十二也,九与八八,去挂一之数,则四六二十四也,五与八八,九与四八,去挂一之数,则四五二十也,九与四四,五与四八,去挂一之数,则四四十六也,故去其三四五六之数,以成九八七六之策,此之谓也。一爻已成,再合四十九策,复分挂揲归以成一变,每三变而成一爻,并如前法。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
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二篇”者,上下经六十四卦也,其阳爻百九十二,每爻各三十六策,积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阴爻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策,积之得四千六百八,又合二者,为力‘有一于五百二十也。若为少阳,则每爻二十八策,凡五千三百七十六,少阴则每爻三十二策,凡六千一百四十四,合之亦为万一千五百二十也。
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四营”者,四次经营也。“分二”者,第一营也;“挂一”者,第二营也;“揲四’’者,第三营也;“归奇”者,第四营也,《易》变易也,谓揲之一变也,四营成变,三变成爻。一变而得两仪之象,再变而得四象之象,二变而得八卦之象。一爻而得两仪之画,二爻而得四象之画,三爻而得八卦之画,四爻成而得其”卜六者之一,五爻成而得其三十二者之一,至于积七十二二营而成十有八变,则六爻见,而得乎六十四卦之一矣。然方其三十六而九变也已得三画,而八卦之名可见,则内卦之为贞者立矣,此所谓“八卦而小成”者也,自是而往,“引而伸之”,又三十六营九变以成三画,而再得小成之封者也,则外卦之为悔者亦备矣。六爻成,内外卦备,六十四卦之别可见,然后视其爻之变与不变,而触类以长焉,则天下之事,其吉凶悔吝,皆不越乎此矣。
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祐神矣。
道因辞显,行以数神,“酬酢”者,言幽明之相应,如宾主之相交也。“佑神”者,言有以佑助神化之功也。
卷内蔡氏说,为奇者三,为偶者二,盖凡初揲,左手余一余二余三皆为奇,余四为偶。至再揲三揲,则余三者亦为偶,故曰奇二而偶二也。
考变占第四《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象》曰:“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坤》卦用六“利永贞”。《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其所占者名爻,不谓六爻皆九六也。及其筮也,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有无九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释也。六十四斟皆然,特于《乾》、《坤》见之,则余可知耳。
愚案此说发明先儒所未到,最为有功。其论七八多而九六少,又见当时占法,三变皆卦,如一行说。
凡卦六爻皆不变,则占本卦彖辞,而以内卦为贞,外卦为悔。彖辞为卦下之辞,孔成子筮立卫公子元,遇《屯》,曰“利建侯”。秦伯伐晋筮之遇《蛊》,曰贞风也,其悔山也。
一爻变,则以本卦变爻辞占。沙氏程氏曰,毕万遇《屯》之《比》,初九变了也;蔡墨遇《乾》之《同人》,九二变也;晋文公遇《大有》之《睽》,九三变也;陈敬仲遇《观》之《否》,六四变也;南蒯遇《坤》之《比》六五变也;晋献公遇《归妹》之《睽》,上六变也。
集说 胡氏一佳曰:《启蒙》谓一爻变,则以本卦变爻辞占,其下引毕万所筮,以今观之,未尝不取之卦,且不特论一爻,兼取贞悔卦体,似可为占者法也,观陈宣公筮公子完之生,尤可见矣。
二爻变,则以本卦二变爻辞占,仍以上爻为主。经传无文,今以例推之当如此。
集说 胡氏一桂曰:案陈抟为宋太祖占,亦旁及诸爻与卦体。
三爻变,则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辞,而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前十卦主贞,后十卦主悔。凡三爻变者。通二十卦有图在后。
沙氏程氏曰,晋公子重耳筮得国,遇《屯》悔《豫》皆八,盖初与四五凡三爻变也,初与五用九变,四用六变。其不变者二二上,在两卦皆为八,故云皆八,而司空季子占之曰“皆利建侯。”集说 胡氏一桂曰:案《启蒙》但云占本卦之卦彖辞,然以晋侯《屯》、《豫》之占,则并占卦体可见。
熊氏朋来曰:七八皆不变爻,何以罕言七而专言八。曰:七七,蓍数也,八八,卦数也。
四爻变,则以之卦二不变爻占,仍以下爻为主。经传亦无文,今以例推之当如此。
五爻变,则以之卦不变爻占。穆姜往东宫,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盖五爻皆变,唯二得八,故不变也,法宜以“系小子失丈夫”为占,而史妄引《随》之彖辞以对,则非也。
六爻变,则《乾》、《坤》占二用,余卦占之卦彖辞。蔡墨曰,《乾》之《坤》曰,“见群龙无首吉”是也,然“群龙无首”,即《坤》之“牝马”“先迷”也,《坤》之“利永贞”,即《乾》之“不言所利”也。
于是一卦可变六十四卦,而四千九十六卦在其中矣,所谓“引而仲之,触类而长之,大下之能事毕矣”,岂不信哉。今以六十四卦之变,列为三十二图,最初卦者,自初而终,自一亡而下,得末卦者,自终而初,自下而卜,变在第三十二卦以前者,占本卦爻之辞,变在第三十二卦以后者,占变卦爻之辞。凡言初终上下者,据图而言,言第几卦前后以上三十二图,反复之则为六十四图,图以一卦为主,而各具六十四卦,凡四千九十六卦,与焦赣《易林》合,然其条理精密,则有先儒所未发者,览者详之。
集说 胡氏一桂曰;焦延寿卦变法,以一卦变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通变四千九十六卦,而卦变之次,本之文王序卦,且如以《乾》为本卦,其变首《坤》,次《屯》、《蒙》,以至《未济》,又如以末一卦《未济》为本卦,其变亦首《乾》,次《坤》、《屯》,以至《既济》,每一卦变六个三卦,通本卦成六十四卦,紫阳夫子以爻变多寡,顺而列之,以定一卦所变之序,又以《乾》、《卦》所变之次,引而伸之,为六十四卦所变相承之序, 案 朱子三十二图,其次第最为详密,而后学之疑义有二:一曰筮法用“九”、“六”不用“七”、“八”,今四爻五爻变者,用之卦之不变爻占,则是兼用“七”、“八”也;二曰周公未系爻之先,则彖辞之用,有所不周也。三代筮法,既不尽传,今唯以经传为据而推之,则“用九”“用六”,经文甚明,而用“七”、“八”者,诸书皆无明文,唯杜预以为夏商用之,先儒已摘其非矣。考之《春秋》内外传,盖无论变与不变,及变之多寡,皆论卦之体象与其彖辞。即一爻变者,虽占爻辞,而亦必先以卦之体象与其彖辞为主,则知古人占法,未有爻辞之先,即彖辞而已周于用,既有爻辞之后,则但以专动考占,而初亦不离乎彖辞以为断也,唯其一卦可变为六十四,则两卦相参,而可以尽事物之理。故卦之有变者,意主于生卦,不主于成爻。爻之有变者,专动则有占,杂动则无占,如是则传记之文皆合,而学者之疑可释矣。至内外传言得八者三:一曰《泰》之八,则不变者也;一曰贞《屯》悔《豫》皆八,则三爻变者也;一曰《艮》之八为《艮》之《随》,则五爻变者也。诸儒以八为不动之爻,考之文意,似未符协。盖三占者,虽变数不同,然皆无专动之爻,则其为用卦一也,卦以八成,故以八识卦,犹之爻以“九”“六”成,则以“九”“六”识爻云尔,观朱子之图者,更须以《左传》、《国语》诸书互相参考。
《启蒙》附论朱子之作《启蒙》,盖因以象数言《易》者,多穿穴而不根,支离而无据。然《易》之为书,实以象数而作,又不可略焉而不讲也,且在当日言图书卦画蓍数者,皆创为异论以毁成法,师其独智而訾先贤,故朱子述此篇以授学者,以为欲知《易》之所以作者,于此可得其门户矣。今摭图书卦画蓍数之所包蕴,其错综变化之妙,足以发朱子未尽之意者凡数端,各为图表而系之以说,盖所以见图书为天地之文章,立卦生蓍为圣神之制作,万理于是乎根本,万法于是乎权舆,断非人力私智之所能参,而世之纷纷撰拟,屑屑疑辨,皆可以熄矣。
《大传》言《河图》,曰一二,曰三四,曰五六,曰七八,曰九十,则是以两相从也。《大戴礼》言《洛书》,曰二九四,曰七五三,曰六一八,则是以三相从也。是故原《河图》之初,则有一便有二,有三便有四,至五而居中;有六便有七,有八便有九,至十而又居中,顺而布之,以成五位者也。原《洛书》之初,则有一二三,便有四五六,有四五六,便有七八九,层而列之,以成四方者也。若以阳动阴静而论,则数起于上,故《河图》之一二本在上也,三四本在右也,六七本在下也,八九本在左也,《洛书》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本自上而下也,于是阳数动而变易,阴数静而不迁,则成《河图》、《洛书》之位矣。如以阳静阴动而论,则数起于下,故《河图》之一二本在下也,三四本在左也,六七本在上也,八九本在右也。《洛书》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本自下而上也,于是阳数静而不迁,阴数动而交易,则又成《河图》、《洛书》之位 自《洛书》以三三积数,为数之原,而自四以下,皆以为法焉,何则?三者天数也,故其象圆,如前图,居四方与居四偶者,或动或静,居中者一定不易而各成纵横皆十五之数矣。四者地数也,故其象方,如后图,居中居四偶与居四方者,或动或静,亦各成纵横皆三十四之数矣。自五五以下,皆以三三图为根,自六六以下,皆以四四图为根,而四四图,又实以三三图为根,赦《洛书》为数之原,不易之论也!今附四四图如左(即后二图),以相证明,其余具数学中,不悉载。
此以十六数自左而右自上而下列之第一图,其居中与居四偶者不易,而居四方者变易,则成纵横皆三十四之数第二图。
若居四方者不易,而居中与居四偶者变易,亦成纵横皆三十四之数第三图。
此以十六数自右而左,自下而上列之第一图,用前法变为两图第二图第三图。
并得纵横皆三十四之数,但其不易者,即前之变易者,而其变易者,即前之不易者此第二图同前第三图,此第三图同前第二图,盖亦阴阳互为动静之理云。
一 三 九 七用中两率,三九相乘为二十七,以一除之得二十七,以二十七除之得一。
若用一与二十七相乘,以三除之得九。以九除之得三。
二 四 八 六用中两率,四八相乘为三十二,以二除之得十六,以十六除之得二。
若用二与十六相乘,以四除之得八,以八除之得四。
《大传》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地之数,皆自少而多,多而复还于少,此加减之原也。又曰:“参天两地而倚数。”天数以三行,地数以二行,此乘除之原也,是故《河图》以一二为数之体之始,《洛书》以三二为数之用之始。然《洛书》之用,始于参两者,以叁两为根也,实则诸数循环互为其根,莫不寓乘除之法焉,而又皆以加减之法为之本。今推得洛书加减之法四,乘除之法十六,积方之法五,勾股之法四,各为图表以明之如左(即如下)。
洛书加减四法一用奇数左旋相加,得相连之偶数。
一加三为四,三加九为十二。
九加七为十六,七加一为八。
若用奇数减左旋相连之偶数,得右旋相连之奇数。
七域十六为九,一减八为七。
一用偶数左旋相加,得相连之偶数。
二加六为八,六加八为十四。
八加四为 I一二,四加二为六。
若用偶数减左旋相连之偶数,得右旋相连之偶数。
六减八为二,八减[一四为六。
四减十二为八,二减六为四。
一用奇数右旋加偶数,得相连之奇数。
一加六为七,七加二为九。
九加四为十三,三加八为十一。
若用奇数减相连之奇数,得相连之偶数。
一减七为六,七减九为二。
九减十三为四,三减十一为八。
一用偶数右旋加奇数,得相对之奇数。
二加九为十一,四加三为七。
八加一为九,六加七为十三。
若用奇数减相对之奇数,得相连之偶数。
九减十一为二,三减七为四。
一减九为八,七减十三为六。
洛书乘除十六法一用三左旋乘奇数,得相连之奇数。
三二如九,寻九二十七。
三七二十一,三一如三。
一用八左旋乘偶数,得相连之偶数。
八八六十四,八四三一卜二。
八二一十六,八六四十八。
一用三左旋乘偶数,得相连之偶数。
三四一十二,三二如六。
三六一十八,三八二十四。
一用八左旋乘奇数,得相连之偶数。
八三二十四,八九七十二。
八七五十六,八一如八。
一用二右旋乘偶数,得相连之偶数。
二二如四,二四如八。
一用七右旋乘奇数,得相连之奇数。
七七四十九,七九六十二。
七三二十一,七一如七。
一用二右旋乘奇数,得隔二位之偶数。
二九一十八,二三如六。
二一如二,二七一十四。
一用七右旋乘偶数,得相连之偶数。
七二一十四,七四二十八。
七八五十六,七六四十二。
一用一乘奇数,得本位之奇数。
一一如一,一三如三。
一九如九,一七如七。
一用六乘偶数,得本位之偶数。
六六三十六,六八四十八。
六四二十四,六二一十二。
一用一乘偶数,得本位之偶数。
一二如二,一四如四。
一八如八,一六如六。
一用六乘奇数,得相连之偶数。
六七四十二,六九五卜四。
六三一十八,六一如六。
一用四乘偶数,得相对之偶数。
四四一十六,四六二十四。
四二如八,四/\二寸’二。
一用九乘奇数,得相对之奇数。
九九八十一,九一如九。
九三二十七,几七六十三。
一用四乘奇数,得隔二位之偶数。
四九三十六,四七二十八。
四一如四,四三十二。
一用九乘偶数,得相对之偶数。
九二一十八,九八七十二。
九四三十六,九六五十四。
凡除法,除其所得之数,得其所乘之数。
《洛书》乘除十六法,可约为八法,何则?五者河洛之中数,自此以上,由五以生, 数有合数,有对数,合数生于五,对数成于十,一六二七三八四九,此合数也,皆相减而为五者也。一九二八三七四六,此对数也,皆相并而为十者也。在《河图》,则合数同方,而对数相连。在《洛书》,则合数相连,而对数相对。相合之相从者,六从一也,七从二也,八从三也,九从四也,如前乘除十六法。相对之相从者,九从一也,八从二也,七从三也,六从四也,女垢积方五法。凡以合数共乘一数,所得之数必同。乘偶既同数,乘奇则同报。若各自乘焉,则又必合矣,如三三得九,八八六十四。以对数共乘一数,所得之数必对,如三三得九,七三二十一。若各自乘焉,则又必同矣,如一一得一,九九亦八十一,二二得四,八八亦六十四。是以自乘之数,相合之相从者,此得自数,则彼亦得自数也,如一得一,六得六。此得对数则彼亦得对数也,如四得六,九得一。此得连数,则彼亦得连数也。如三得九,八亦得四,二锝四,七亦得九。相对之相从者,此得自数,则彼得对数也。如一得一,九亦得一,六得六,四亦锝六。此得连数,则彼亦得连数也,如三得九,七亦撂九,二得四,八亦得四。要皆会于一六四九而齐焉。故开平方之自乘数,止于一六四九而《洛书》之位。一六四九居上下以为经,二七三八、居左右以为纬者,此也。
《洛书》对位成十互乘成百图一与九对成十,十自乘其积一百。九自乘八十一;一自乘一;一乘九、九乘一,俱为九,共十八;合之一百,与十自乘积同。
二与八对成十。八自乘六十四;二自乘四;二乘八、八乘二,俱十六,共三十二;合之一百。
三与七对成十。七自乘四十九;三自乘九;三乘七、七乘三,俱二十一,共四十二;合之一百。
四与六对成十。六自乘三十六;四自乘十六;四乘六、六乘四,俱二十四,共四十八;合之一百。
中五含五成十。五自乘二十五;又五自乘二十五;又五互乘各二十五,共五十。合之一百。
勾三,股四,弦五。
勾九,股十二,弦十五。
勾二十七,股三十六,弦四十五。
勾八十一,股一百零八,弦一百三十五。
此《洛书》四隅合中方,而寓四勾股之法者,推之至于无穷法皆视此。
河洛未分未变方图《河图》之数,五十有五,《洛书》之数,四十有五,合为一百,此天地之全数也,以一百之全数,为斜界而中分之,则自一至十者,积数五十有五,自一至九者,积数四十有五,二者相交,而成河洛数之两三角形矣。凡积数自少而多,必以三角,而破百数之全方,以为三角,其形不离乎此二者,下诸图之根,实出于此。
河洛未分未变三角图《河图》之数,自一至十;《洛书》之数,自一至九。象之已分者也。图则生数居内,成数居外,书则奇数居正,偶数居偏,位之已变者也。如前图破全方之百数,以为河洛二数,又就点数十位,中涵幂形之九层,以为河洛合一之数,则虽其象未分,其位未变,而阴阳相包之理,三极互根之道,已粲然默寓于其中矣。故为分析以明之,如后 点数应《河图)十位周围三角,分三重,中一重九,次内一重二九一十八,外一重三九二十七,除中心,凡五十四。
若自上而下作三层,亦如之。
中含六角,亦分三重,中一重六,次内一重二六一十二,外一重三六一一十八,除中心,凡三十六。
若自十而下作三层,亦如之。
幂形应《洛书》九位周围三角分三重,中一重九,次内一重三九二十七,外一重五九四十五,凡八十一。
若自上而下作三层,亦如之。
中含六角,亦分三重,中一重六,次内一重三六一十八,外一重五六三十,凡五十 以上诸图,本同一根,虽积数若异,而其为九六之变则一也。九六可分为内外中之三重,亦可分为上下中之三层,就每重每层论之,则九为天而包地,六为地而涵于天,心为人而主乎天地。统三重而论之,则外为天,内为地,而中为人也。统三层而论之,则上为天,下为地,面中为人也。又合而论之,则九六者,在天为阴阳,在地为刚柔,在人为阴阳刚柔之会,而其心则天地人之极也,以上下分者,其心有三,所谓三极之道,三才各具一太极也;以内外分者,其心惟一,所谓人者天地之心,三才经体一太极也。
此图之中,浑具理象数之妙者如此,故分而为图,则应乎阴阳刚柔之义,根于极而迭运不穷,“圣人则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阳九阴六,命爻衍策者此也。分而为书,则应乎三才之义,主于人而成位其中,“圣人则之”,皇极既建,彝伦攸叙,参天贰地,垂范作畴者此也。或曰:《河图》、《洛书》,出于两时,分为两象,今以一图括之可乎?曰:十中涵九,故数终于十,而位止于九,此天地自然之纪,而图书所以相经纬而未尝相离也。非有十者以为之经,则九之体无以立,非有九者以为之纬,则十之用无以行,不知图书之本为一者,则亦不知其所以二矣。或曰:《河图》、《洛书》,有定位矣,今以为有末变者何与?曰:《易大传》之言《河图》也,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顺而数之,此其未变者也。又曰:“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分而置之,此其定位者也,如《易》卦一每生二,以至六十有四,则其未变者也,乾南坤北,离东坎西,则其定位者也,不知未变之根,则亦不足以识定位之妙矣。
幂形为算法之原此图左方注者,本数也,自一至九而用数全矣。中列注者,加数也,一加二为三,二加三为五,至于八加九而为十七,皆以本数递加,而每层之幂积如之。右方注者,乘数也,一自乘一,其幂积一,二自乘四,其幂积合一三两层而为四,至于九自乘八十一, 图形合《洛书》为象法之原人为天地心图凡有数则有象,象不离乎数也,万象起于方圆,而测方圆者以三角,此勾股所以为算之宗也。圆者天象,方者地象,三角形者人象,何则?天之道如环无端,故其象圆也。
地之道奠定有常,故其象方也。人受性于天,受形于地,犹三角之形,其心则圆之心,其边则方之边也。今就九数而三分之?则一者圆之根也,而十数之内,唯六角八角,为有法之圆形,其自十以后,角愈多以至于无角者视此矣,此一六八所以为圆象之数也。
先后天阴阳卦图先天之阳卦,曰震离兑乾;其阴卦,曰巽坎艮坤。后天之阳卦,曰乾震坎艮,其阴卦,曰坤巽离兑,不同何也?盖先天分阴阳卦,自两仪而分之,由阳仪以生者,皆阳卦也;由阴仪以生者,皆阴卦也。后天分阴阳卦,自爻画以定之,其以阳为主者,皆阳卦也;其以阴为主者,皆阴卦也。先天则因乎画卦之序而中分之,后天则卦之已成,观其爻画之多寡而命之也,其理如何?曰:阳仪上有阴卦,此所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也。
阴仪上有阳卦,此所谓“立地之道曰柔与刚”也。其法象之自然者如何?曰:火之炎热光明,其为阳也,明矣。泽者水之积湿,为阳气所驱,以滋润万物者也,是亦阳也,水之幽暗寒肃,其为阴也,明矣。山者土之隆起,与地为一体者也,是亦朋也。是放先天之卦,阴阳之象之正也,其变而后天,则火与泽从风而俱为阴,水与山从雷而俱为阳,盖有由矣。凡阴阳之气,未有不合而成者也,然有感应先后之别焉,先有阳而遇阴者属阳,先有阴而遇阳者属阴,有阳气在下将发而遇阴压之,则奋而为雷矣,有阳气在中将散而遇阴包之,则郁而为雨矣,有阳气直腾而上而遇阴承之,则止而为山矣,此皆主于阳而遇阴,所以皆为阳卦也。有阴在内,阳气必入而散之,观之阴霾尽而后风息可见也,有阴在中,阳气必附而散之,观之薪刍尽而后火灭可见也;有阴在外,阳气必敷而散之,观之湿润尽而后泽竭可见也。此皆主于阴而遇阳,所以皆为阴卦也。总而沦之,唯乾纯阳,坤纯阴,不可变也。雷阳动之始,凡阴生之始,亦不可变也,火温暖,泽发散,故以用言之则阳,然火根于阴之燥,泽根于阴之湿,故以体言之则阴;水寒凉,山凝固,故以用言之则阴,然水根于阳之嘘而流,山根于阳之矗而起,故以体言之则阳。先天之象,著其用也,后天之象,探其根也,正如仁之发生为阳,而其柔和亦可以为阴,义之 后天卦以天地水火为体用图造化所以为造化者,天地水火而已矣,《易》卦虽有八而实唯四,何则?风即天气之吹嘘而下交于地者也,山即地形之隆起而上交于天者也,雷即火之郁于地中而搏击奋发者也,泽即水之聚于地上而布散滋润者也。道家言天地日月,释氏言地水火风,西人言水火土气,可见造化之不离乎四物也。故先天以南北为经,而天地居之体也,以东西为纬,而水火居之用也。后天则以天地为体,而居四维,以水火为用,而居四正。雷者火之方发,故动于春;及火播其气,则王于夏矣;泽者水之未收,故散于秋;及水归其根,则王于冬矣。水火为天地之用,故居四正以司时令也。天气联兆于西北,至东南而下交于地,《易》所谓’天下有风”《娠》也。故乾巽相对而为天纲,地功致役于西南,至东北而上交于天,《易》所谓“天在山中”《大畜》也,故坤艮相对而为地纪。天地为水火之体,故居四维以运枢轴也,天地水火,体用瓦根,以生成万物,此先后天之妙也。
若以卦画论之,则震即离也,一“阴闭之于上则为震,兑即坎也,一阳敷之于下则为兑,巽即乾也,一阴行于下则为巽,艮即坤也,一阳亘于上则为艮,是以六十四卦始《乾》、《坤》,中《坎》、《离》,而终于《既济》、《末济》,,则知造化之道,天地水火尽之矣。
先天卦变后天卦图此图先天凡四变而为后火也,盖火之体阴也,其用则阳,而天用之,故乾中画与坤 先天卦配河图之象图图之左方,阳内阴外,即先天之震离兑乾,阳长而阴消也;其右方,阴内阳外,即先天之巽坎艮坤,阴长而阳消也,盖所以象二气之交运也。
后天卦配《河图》之象图先天卦配《洛书》之数图直列《洛书》九数,而虚其中五以配八卦。
阳上阴下,故九数为乾,一数为坤,因自九而逆数之,震八坎七艮六。乾生二阳也,又自一而顺数之,巽二离三兑四,坤生三阴也,以八数与八卦相配,而先天之位合矣。
后天卦配《洛书》之数图火上水下,故九数为离;一一数为坎,火生燥土,故八次九而为艮;燥土生金,故七六次八而为兑为乾;水生湿土,故二次一而为坤;湿土生木,故三四次二而为震为巽:以八数与八卦相配,而后天之位合矣。
《洛书》之左边,本一二三四也;其右边,本九八七六也。然阴阳之道,丑未之位必交,《洛书》之二与八,正东北西南之维,丑未之位,此其所以互《易》也。以此类之,则先天图之左方,坤巽离兑;其右方,乾震坎艮,以震巽互而成先天也。后天图之左方,坎坤震巽;具才;方。离艮兑乾,以艮坤互而成后天也。
据先儒说,图书出有先后,又或谓并出于伏羲之世,然皆不必深辨,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况天地之理,虽更万年,岂不合契哉,《洛书》晚出,而其理不妨已具于《河图》之中,是故以《易》象推配,亦无往而不合也。
先后天卦生序卦杂卦图说先天图者,序卦之根也。
序卦之法,以两卦相对为义,有相对面翻覆不可变者,《乾》、《坤》、《坎》、《离》、《颐》、《大过》、《中孚》、《小过》是也 c有相对而翻覆可变者,《屯》、《蒙》以后,《既济》、《未济》以前,五十六卦皆是也。就五一卜六卦之中,则翻覆而二体不《易》者十二卦,《需》,,,《讼》、《师》、《比》、《泰》、《否》、《同人》、《大有》、《晋》、《朋夷》、《既济》、《未济》也。翻覆而二体皆易者十二卦,《随》、《蛊》、《咸》、《恒》、《损》、《益》、《震》、《艮》、《渐》、《归妹》、《巽》、《兑》也。其翻覆而止于一体易者三十二卦,则自《屯》、《蒙》至《涣》、《节》皆是也。盖翻覆而不可变者,法八卦之乾坤坎离也。翻覆而可变者,法八卦之震艮巽兑也。就翻覆可变之中,其二体不《易》者,又皆乾坤坎离相交者也。其一体不易者,亦皆交于乾坤坎离者也。唯震艮巽兑相交之卦,则二体皆易焉,《颐》、《中孚》、《大过》、《小过》,虽为震艮巽兑相交之卦,而翻覆不可变者,《颐》、《中孚》具离之象,《大过》、《小过》具坎之象也,故《序卦》以之附于《坎》、《离》、《既济》、《未济》,为其具离坎之象焉尔。
先天图八卦,两两相对,《序卦》之根也,乾与坤对,坎与离对,震与巽对,艮与兑对。相对而不相交,所以定《序卦》之体也,然既相对,则必相交,四正之卦相交,则虽翻覆而其体不易,四维之卦相交,则翻覆而其体遂易矣。若四正之卦、与四维之卦杂交,则易者生,不易者半,所以极《序卦》之用也,足故“天地定位,上经所以始于《乾》、《坤》,中于《否》、《泰》也,“山泽通气,雷风相薄”,下经所以始于《咸》、《恒》,中于《损》、《益》也,“水火不相射”,上下经所以终于《坎》、《离》、《既济》、《未济》也。
后天图者,杂卦之根也。
杂卦,即互卦也,互卦之法,或上去一画而下生一画,或下去一画而上生一画,则其体遂变矣。互体所成,凡十六卦,其阳卦从阳卦,阴卦从阴卦者八,《乾》、《坤》,《颐》,《大过》、《蹇》、《解》、《家人》、《睽》也。其阳卦交阴卦,阴卦交阳卦者亦八,《剥》、《复》、《夬》、《姤》、《渐》、《归妹》、《既济》、《未济》也,以交互之法求之,乾而上去一阳,下生一阳,或下去一阳,上生一阳,仍是乾矣。坤而上去一阴,下生一阴,或下去一阴,上生一阴,仍是坤矣。唯震而上去一阴,下生一阴,则变为坎;下去一阳,上生一阳,则变为艮。巽而上去一阳,下生一阳,则变为离;下去一阴,上生一阴,则变为兑。坎而上去一阴,下生一阴,则变为艮;下去一阴,上生一阴,则变为震。离而上去一阳,下生一阳,则变为兑:下去一阳,上生一阳,则变为巽。艮而上去一阳,下生一阳,则变为震;下去一阴,上生一阴,则变为坎。兑而上去一阴,下生一阴,则变为 后天图八卦,阴阳上下画互变,杂卦之根也,何则?后天之卦,有各从其类以相变者焉,有各得其对以相变者焉,乾居西北,而三阳从之,坤居西南,而三阴从之,此各从其类者也。乾与巽对,坎与离对,艮与坤对,震与兑对,此各得其对者也,相从者除乾坤纯阳纯阴不变外,坎而上去一阴,下生一阴,则为艮;艮而上去一阳,下生一阳,则为震;震而上去一阴,下生一阴,则复为坎,此三阳相次之序也。巽而上去一一阳,下生一阳,则为离;离而上去一阳,下生一阳,则为兑;兑而上去一阴,下生一阴,则复为巽;此三阴相次之序也。相对者,乾而上去一阳,下生一阴,则为巽;坎而上去一阴,下生一阳,则为离;艮而上去一阳,丁生一阴,则为坤;震而上去一阴,下生一阳,则为兑;此四阳卦变为对位四阴卦之序也。巽而下去一阴,上生一阳,则为乾;离而下去一阳,上生一阴,则为坎;坤而下去一阴,上生一阳,则为艮;兑而下去一阳,上生一阴,则为震;此四阴卦变为对位四阳卦之序也。然寻其对位相变之根,则又自父母男女长少而来,盖四阴卦,兑为最少,离为中,巽为长,坤为老。四阳卦,艮为最少,坎为中,震为长,乾为老。凡变者自少而老。故兑而卜去一阴,下生一阳,则变为乾矣。
离而上去一阳,下生一阴,则变为坎矣。巽而上去一阳,下生一阴,则变为艮矣。坤而上去一阴,下生一阳,则变为震矣。四阳卦之变,自阴而来,故又变而为对位之四阴也。
艮而下去一阴,上生一阳,则变为巽矣。坎而下去一阴,上生一阳,则变为离矣。震而下去一阳,上生一阴,则变为坤矣。乾而丁去一阳,上生一阴,则变为兑矣。四阴卦之变,自阳而来,故又变而为对位之四阳也。
合而观之,凡阳卦相变者,震变坎艮也,坎变震艮也,艮又变震坎也。凡阴卦相变 大衍圆方之原凡方圆可为比例,唯径七者,方周二十八,圆周二十二,即两积相比例之率也,用其半,故若十四与十一。合二十八与二十二,共五十,是大衍之数,函方圆同径两周数。